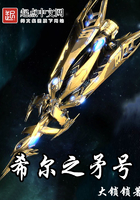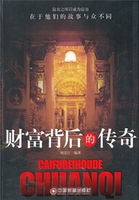蓝说,你知道吗?我姐姐死时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天堂。她总想把天堂搬到人间,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堂只有一个,所以她一难过就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张烟榻,一对依偎的身影,空气中弥散着腥甜的鸦片清香,他们一起吸食鸦片,陶醉在升腾的云雾间,”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
他终于为她家财荡尽,妻离子散。为了爱情,他亦曾用尽了一辈子的勇气死过一次,却被鸦片榨干了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活着不如死了。
她只是冷笑,其实她一直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她却措手不及,她吃空了他。
他跪地行乞,他不想失去她。
他已被毒魔死死地缠住,可是他再没有钱去买她下过毒的鸦片。当毒瘾发作时,他周身冷疼,就如万蚁啃咬般,全身的关节像是被人用一根根钢针不停地狠扎一样疼痛。炼狱般的折磨,令他痛不欲生,他用力拉扯着自己的头发,撕扯着自己的衣服,不停地在地上翻滚、嚎叫,直至声嘶力竭、不能动弹为止。
她站在苏州河旁的那棵榕树下,用冰凉的手指触碰树上刻的字,仿佛在触摸树的伤口。内心的疼痛,像蓝玫瑰一样绽放。她说,时间是什么,是不是一条寂寞的会淹没我的河流。
我是一条无法呼吸的鱼,困囚在时间的河流中,身体停留在现实,灵魂却在隔世观望。河底的荒漠还开着花朵,幻化成姐姐的影子。我躺在河底,眼看着潺潺流水,粼粼波光,落叶,浮木,空琉璃瓶,一样一样从身上流过去。
那么永远呢,是不是这棵树上寂寞空洞的伤口。
《花样年华》的结束,是一个埋葬了过往的洞口: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到。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杜拉斯说,当你开始回忆的时候,就意味着苍老。
蓝给他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
那时我很小,还不食人间烟火。我有一个姐姐,名叫安。她喜欢穿素雅的绸袍,喜欢蝴蝶,烟火,摩天轮和蒲公英,她写一手好字。可是她很小的时候,因为一场大病,眼睛瞎了。她再也看不到那些美丽的蝴蝶在天上飞舞。
我们都是私生子,母亲走的时候,说她是随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而去,说她往生是一只鸟,要飞回去,然后她就跳下了楼。你相信有往生吗?可是,这便是她的一生了,只为贪恋那一点依赖,一点儿爱,她就敢纵身一跳。到死,还记挂着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暖。也许那一刻她心里有害怕,有依恋,所以她想抓住一些什么,她从未得到过的东西。那些蝴蝶,终究没有飞回到原来的地方,就坠落了。然后是简单的丧事,眼泪就在那一天流成了回忆。
后来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男人,自称是我们的父亲,接走了我们。他家里还住着一个娇惯霸道的大女儿,常常鞭打我们,把我们锁在漆黑冰冷的储藏室。姐姐是一个压抑和隐忍的人,什么都埋在心底。她的生活原本就是黑暗的,可是她还是怕黑,她总感觉一个影子跟随着她,她便用冰凉的手指去触碰那无尽的虚无。
人的命好像都是定数,就像姐姐遇见他一样,冥冥中的安排,逃不掉。她因为他,倾尽所有,毅然决绝地和家里人断绝了关系。
他牵着她,她踩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海角天涯。苏州河旁的榕树下,他回头,她踮起脚亲吻他。
我爱姐姐,胜过爱我自己,我很怕姐姐被他抢走,我要和姐姐在一起,一辈子不分开。
那棵榕树下,他要她等他五年。五年以后,他会回来娶她做新娘。她怕会记不起他的样子,她便用冰凉的手指轻抚他英俊的脸庞,纤细的十指,从上到下,头发、眼睛、脸颊、下颚,那是张轮廓分明的脸。她的手指从此铭刻在他的心底。她用手盖住他的眼睛,不忍让他看到自己流泪,放开手时,她的手心里一片温暖的潮湿。
一个人站在一棵树下,用双臂紧紧拥抱自己,依然会觉得冷。
我们都是游走在世间的躯壳,来覆盖那张流血的伤疤。只是伤口太深,已经无法愈合。原来伤口到伤疤,已经经历了一个沧海桑田。
五年,她埋葬了她的青春。五年以后,他没有回来。父亲去世了,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那个娇贵的大女儿,惟独把眼角膜捐给了姐姐。
她终于重获光明,可是大夫说她患了极度严重的抑郁症和臆想症,她开始无休止的头痛,眼前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幻觉。
她仿佛回到小时侯,一个人赤脚走在阴暗的洞穴里,脚下是冰冷的清水,在挣扎的流动,发出很好听的声音。可是她看到一扇一扇紧闭的门,她找不到洞口。
她沉入海底,找不到灵魂的出口,她变成了一条无法呼吸的鱼,疼痛和窒息。
她的心很痛很痛,轻轻触碰便会流下泪水。她常常会看到死去的父母,她亦会看到他,他说过会回来娶她。她愿意等他,一生一世。
她泡在浴缸的冷水里,一点一点地剪自己的长发,浴缸里满是一缕一缕漆黑的发丝。她看着自己的手,用一块锋利的刀片将它割开,看里边浓黑的血液浸满寂寞的皮肤,然后滴到地上,她听到寂寞冰冷的声音,像洞穴里流水的声音,她看到那些血液开出美丽的花儿,绽放出寂寞空洞的灵魂。
有时,我会听到浴室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声音,然后是无助的抽泣。每当那时,我的心就会很痛很痛,可是我无能为力。她的心里潜伏着一个深渊,扔下巨石也发不出声音。
她会喝很多酒,麻醉自己,直到自己流着泪沉入睡梦。
十年,那个男人终于回来,可却没有带给她想要的答案。他也许有苦衷,亦不能带她一走了之。当美丽面对枯萎的一瞬,恐惧像酒里的毒,诱惑又可怕。他无法犹疑。像掉进一个明晃晃的窟窿,四外都是疼痛的。鸦片的前身是罂粟,是最魔幻毒辣的花,化身为烟,满足人生的快乐;化身为药,满足人死的凄美。你怎能说他爱的不深切,他连死的准备都有。
血自他嘴角流下,他们相拥着,看着对方濒死的样子。她手执素绢,擦去他嘴角的血迹。直到他没有知觉,直到他熄灭了苦痛的表情。因为了解,她比他从容,她拂合他的眼,才肯安心离去。终于她做到了,她带走了她的一切。
可是他并没有死,亦没有勇气再死一次。他离开,并娶了父亲家那个的娇贵的大女儿,从此享尽荣华。惟独姐姐,一个人葬在冰冷黑暗的地下,姐姐生前最怕黑的。
她其实很想问他,当初他接近她,是不是因为她父亲的家产,可是她到死,都没有开口。
蓝说,这就是爱情吗。有些人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没有开始,所以也没有结束。曾听人说,人的寂寞,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表达,就像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
她轻轻地把手盖在他的眼睛上。她潸然泪下,转身离开,她感到手心温暖的潮湿。他睁开眼,望见她远去的背影。她要去远方。
她终究没有告诉他,她怀了他的孩子,可是她因为吸食过多带毒的鸦片,孩子流掉了。她终究没有告诉他,这么多年她如何沦落风尘。她也终究没有告诉他,她是要去找姐姐,她说过办完了事,她会和姐姐在一起,一生一世不分开。
她缓缓沉入海底,她无法呼吸,她想,姐姐一定变成了海底深处的一条鱼。她越沉越深,永远都没有上来。
她是滚滚红尘里一朵寂寞的烟花,她的背后是一座座尘烟飞起,繁华落尽的城郭。她不属于这个喧嚣的世界,所以她们都走了。
他从此疯了,流落市井的乞人,时不时会有生不如死的毒瘾发作。那不过是一场湿透的雨,下在某个夏日的屋檐下,滴答声都是旧的。那一抹绯红的胭脂,也留在夜里老去了……
他终于倒在地上,他看到火焰在灰烬上径自舞蹈,洒出一滴滴寂寞的血红。
指间疼痛,划过天际,再也无力举起。他仿佛看到那棵榕树下一身素衣的少女,他对她说,永远。他不会骗她。
昨日情了人未了,梦回苦寻空楼台。
自怨前世情缘定,两生花开两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