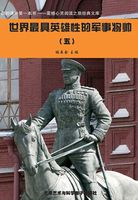实际上,他的听力并不佳,缺乏迅速判断乐声的准确能力,自称“没有绝对辨音力”。他认为身为音乐家,而又没有“绝对辨音力”,是对事业的玷污,是上帝和命运安排他不能从事音乐事业。
不久,鲍里斯果断地下了决心,与音乐一刀两断,砸碎当音乐家的美梦。他想从此再不创作乐曲,再不接触钢琴,再不参加音乐会,甚至不与音乐家们来往。这仅仅是他一时的主观的愿望。事实证明他不但没能摆脱音乐,而且生活本身使他和音乐紧紧地卷在一起。
鲍里斯青年时代创作的乐曲,大部分都失散了,只保留下来两首序曲,是他1906年之作。80年后,他的两首序曲在俄罗斯和欧洲都演奏过,还灌成了唱片,得到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至于他为音乐付出的心血,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浓厚的感情与酷爱,后来全部注入他写的诗、小说和评论文章中了。
别了,哲学
鲍里斯是非常爱动脑筋的少年。早在莫斯科男子第五学校六年级读书时他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那次革命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使他后来写成不朽的诗篇《1905年》。
1906年鲍里斯随父母在德国住了几个月。他第一次出国,对一切都感觉到不寻常,好像是在梦中。
那一年,鲍里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过音乐史课。课程讲得枯燥乏味。他想转到哲学系去听课。他认为在临近哲学的地方将出现他未来事业的胚胎。帕斯捷尔纳克成熟时期的诗作中常常透露哲理观念并非偶然。
帕斯捷尔纳克攻读哲学十分专注。家人发现他的性格有些变化,变得孤僻了。同学们也发现他喜欢独来独往,低着头冥思苦想。只有讨论哲学问题时,他才会变得滔滔不绝,引得周围人注意。
有一天,他和朋友们谈起哲学趋势,认为当今的哲学中心在德国马尔堡,最重要的哲学家是柯亭。要想研究哲学,必须去德国,必须投师柯亭教授。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这种看法,但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到那里去的条件。
过了不久,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母亲给了他一笔钱,共200卢布,说这是她弹钢琴挣的和全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父母建议鲍里斯到国外走一走,开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埋在帕斯捷尔纳克心底的愿望立即浮上心头。他早已在幻想去马尔堡了。妈妈和爸爸最理解也最体贴自己的儿子。
1912年4月21日,帕斯捷尔纳克乘坐火车的三等硬座,穿着父亲的灰色旧西装,经过4天的行程,抵达马尔堡。一座神话般的城市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有想到这个中世纪的古老大学城竟是如此之小,如此之美。人口不到3万,半数是学生。马尔堡像颗翡翠镶嵌在山脊上。哥特式的尖顶建筑,层层叠叠撒满山坡。狭窄而清洁的街道几乎见不到行人。绿色的小城异常寂静,只有几朵白云在钟楼上空飘浮。到处是花草绿茵,芬芳醉人。
帕斯捷尔纳克深知自己手中的钱是妈妈和全家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不敢滥用一分。他在城边,公路最后一排楼的三层,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房东太太是位寡妇,她丈夫原是一位兽医。隔窗可以看到农村风景,弯弯的蓝河流淌,一棵棵栗子树随风摇曳。
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在马尔堡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如果能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首领柯亭教授的垂青——让他出席自己的家庭午餐会,那就标志着自己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权威的首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事哲学的前途就展现在眼前了。
柯亨是最高的权威。为了和柯亨教授谈话,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主动登门拜访。一次,两次,都没有见到本人。第三次,柯亨接见了他。
柯亨教授白发披肩,胡子遮住半张脸。帕斯捷尔纳克立刻觉得老教授很可爱,便坦诚地说,他不想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只想攻读柯亨的理论哲学。柯亨教授脸上立刻露出愠色,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收的学生应当具备渊博而踏实的知识。谈话就那么结束了。
柯亨教授为人严肃,脾气古怪。他已年近70,右耳失聪,准备第二年退休。他每周二与周五授课:要求学生回答问题简洁明确,只能用几个字,不许拖泥带水。
有一天,上课时,帕斯捷尔纳克站起来分析自己选自康德学说中的一个命题。帕斯捷尔纳克陈述过程中,柯亨冷不防地问道?什么意思?
帕斯捷尔纳克的思路一下子受堵,但还是做了正确的回答。
柯亨没有听清楚,皱起眉头,把手往旁边一挥。帕斯捷尔纳克心中有些发怵,修改了一下答案。柯亨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懦怯的答案露出悻悻不悦的神色。柯亨问其他学生,谁能正确解答。同学们都在发愣。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本来是正确的,老教授一追问,反而成了疑点。柯亨有些气恼。大家一看老教授那副鄙夷的表情,谁也不敢再重复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了。最后,柯亨自己作了解答。他的解答实际上又恢复了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说法。
全场一阵骚动,窃窃私语。等到老教授明白过来事情的原委时,打量了帕斯捷尔纳克几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俄国学生引起了他的好感。
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一封信:柯亨教授邀请他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参加他的午餐会。帕斯捷尔纳克望着来信,沉思了良久,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日子。
偏偏那一天,他需要到基青根去看望他爱过的一位女友。
当他从基青根回到马尔堡时,柯亨邀请他出席午餐会的星期天已经过去。他不敢去见柯亨教授,尽量回避与他见面。可是事情就是那么巧。中午,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二人意外地相遇。
帕斯捷尔纳克已无处可躲,只好老老实实地迎上前去,向老教授表示歉意,一再解释他未能出席午餐会的原因,越说越不清楚。
柯亨教授默默地听着,未作任何表示。等到他把话讲完时,老教授才关切地问他今后有何打算?回国?当律师?老教授奇怪的是这位俄罗斯青年人有那么好的哲学基础,为什么不留在德国当博士研究生?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从事哲学事业前途会异常光明。
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心中对自己说:“哲学也不得不认可任何一种爱都是向新的信仰的转变。”
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尔堡大学度过3个月。这期间,他的恋人、他的堂妹、他的弟弟、他的父亲都来看过他,占用了他不少时间。凭借自己异乎寻常的勤奋和专心,他弄通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与精华,下一步是进行有关思维法则作为动学范畴来研究。他说,“这是一种富有魔力的逻辑学主题之一”,然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人无害的麻醉剂。”但是,他对这种无害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从事哲学的料。康德对于他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8月初,拂晓,他乘上火车,穿过清晨的雾霭,越过铁路道口和公路,跨过缓缓流淌的蓝河和绿油油的山坡,向一层层尖顶的石屋,还有他住过的地方,瞥了一眼。火车急剧地拐了弯。在隆隆震动的车厢里,帕斯捷尔纳克什么也看不见了。
别了,哲学!别了,青春!别了,德国!
11年后,1923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妻子叶夫根尼娅·卢里耶又一次来到这里,住了短短两天。
从此以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脚再也没有踏上这座中世纪小城的石板台阶,再也没有呼吸到这座小城的特有的空气,再也没有亲眼看到这里新一代的莘莘学子。可是在他住过的这个异国小城里,有一条街却以他的名字命了名,在他居住过的小楼的墙上出现了一块纪念板,古铜色的板面上镶嵌着几行德文字: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
195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1912年曾是马尔堡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别了,哲学!”
——引自《安全保护证》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思念着马尔堡。在关于马尔堡的诗中记录了他的深情、他的爱。马尔堡市也永远纪念着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为了哲学而来,却怀着写诗的激情离去。
寻找自我
帕斯捷尔纳克少年时代,根本没有想成为诗人。
1908年,他在莫斯科第八中学毕业了。11门功课考试成绩全部是“优”,成为金质奖章获得者。18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德文、法文与英文。
中学毕业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下意识地梳理自己迷乱的思绪。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感到不满意。没有一个行业能够让他沉醉。他在寻找自我。
当他考进莫斯科大学以后,亚历山大发现大哥变得沉闷了。
弟弟不知道鲍里斯大哥精神苦闷。文学创作悄悄地叩击他的心扉。他试探自己的写作能力,但不肯让人知道。
鲍里斯接触作家很早,他见过文学泰斗,像列夫托尔斯泰。
10岁时,他在火车站上见过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时,是里尔克外貌而不是他的创作使鲍里斯不能忘怀。
文学究竟何时代替绘画、音乐与哲学主宰了他的心,很难说清。
鲍里斯少年时,有过一位很好的家庭教师,她叫叶卡捷琳娜·博拉滕斯卡娅。博拉滕斯卡娅在教学上受过专门训练,循循善诱,她把自己对文学的爱好灌输给鲍里斯。博拉滕斯卡娅通晓法语与英语,翻译过一些小说。严格地说,那不能称为翻译,而是复述。她的翻译方法与我国翻译家林纾十分相似,用自己的语言把一部名著重写一遍。她发表这类作品时,署名“叶·鲍”并注明是“编写”而不是“翻译”。她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建议编译了阿里斯·斯托黑默的《生命的创造力》,于1894年问世。她本人也写一些伤感情调很浓的小说,一些刊物很欢迎她的作品。
博拉滕斯卡娅是俄国大科学家季米里亚捷夫的侄女,原是莫斯科省副省长的夫人,夫妻二人不睦,离了婚,她独自住在一栋宽敞的寓所里。那时,鲍里斯每天到她家上课。她对鲍里斯既严厉又体贴。
鲍里斯对这位家庭老师终身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博拉滕斯卡娅老师教我识字、算算数,学法文,从字母开始,还教我如何以正确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如何手握钢笔写字”,等等。
鲍里斯成年以后,他的字体规范、飘逸,有人说像鸟儿在飞翔,是与这位家庭女教师的良好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的。博拉滕斯卡娅把文学的种子撒在鲍里斯的心田里,只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而种子的发芽、开花、结果已是后来的事了。
博拉滕斯卡娅活到1921年,69岁逝世。她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著名的诗人。
20世纪初,俄国艺苑异彩纷呈,爱好文艺的青年人百般鼓吹自己的先锋主张,组成各种流派的文学团体、美术团体,出版社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还在中学读书的鲍里斯结识了青年诗人与画家尤里昂阿尼希莫夫。阿尼希莫夫住在一座老木屋的顶楼里,经常邀请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人聚会,朗诵诗歌,演奏乐曲,展览绘画等。他们给自己的团体起了一个谁也不知其意的名字——“谢尔达尔达”。鲍里斯很喜欢阿尼希莫夫,经常到他家里去,不是以文学爱好者而是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每当众人聚会时,鲍里斯便即兴弹奏一些曲调,用音乐的语言描绘每一位出席聚会的人进屋时的特征。他的即兴表演很受大家的欢迎。
他在阿尼希莫夫家中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年长的诗人:安年斯基、勃洛克、别雷……同辈中有洛克斯、杜雷林……正是阿尼希莫夫使鲍里斯对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并翻译了他的几首诗,成为里尔克诗歌的最早的俄译者。
后来,他对这位奥地利诗人的感情日益加深,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
正是杜雷林的慧眼发现了鲍里斯的文学才能,并推荐他将试笔之作发表出来。
正是洛克斯第一个把伊诺肯吉安年斯基的诗拿给鲍里斯阅读,使他开阔了眼界。
鲍里斯对别雷和勃洛克的诗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作品使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1910年夏天,鲍里斯和双亲在莫洛吉别墅住了一段时间。他每天爬到一棵半倒在水面上的老桦树权上,一边吟咏老一辈抒情诗人丘特切夫的作品,一边创作自己的诗。他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同从事绘画或作曲的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创作。写了改,改了再写,反反复复涂涂抹抹,然后再把删掉的部分恢复起来。他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写诗使他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写到触及灵魂时,他甚至会动情地流下眼泪。他尽力回避浪漫主义的造作和琐碎的文字趣味,他不想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这些诗,他没有追求明确的节奏。他梦寐以求的是让诗本身具有含意——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让它们自己的全部特点镂刻在书心中,并以其全部无声的语言和全部黑色的(即没有色彩的印刷)从书页中发出声响来。”多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当时的创作过程时,这样写到。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在诗的领域里找到了自己,他作为诗人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