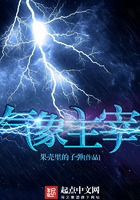“了了,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说这种奇怪的话。”周杨撇撇嘴,对了了的话不以为意,也许是没听懂,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药方先生,如果你能不总是做这种没脑子的事的话。”了了耸耸肩,摊着手表示无奈。
“好吧!你总有你的理由。”周杨小声的嘀咕了一句,帮了了提上裤子。
害羞?不好意思啊,了了表示这个功能他还没进化出来。或者,对于一个八岁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害羞这个概念还为时过早了。
周杨去屋子外头的井里打水,木桶本身有一定的重量,加上水周杨对付不了,摇摇晃晃的拎了半桶上来,早春,水凉的冰骨头,周杨把水倒在木盆里,又去灶房的锅里添点热水,自己洗把脸后就拿了布巾帮了了洗漱。
听见推门的声音,了了掀了掀眼皮子,挺尸样的躺在床上,集中精力对付要人命的疼。挖苦周杨转移注意力什么的,对于天然呆的周杨来说,那是纯属自己找虐。
了了平时说话虽然也是绵里藏针,但是藏得严实,大多数人都发现不了里面的针,了了的自卫心重了点,没有安全感,心思就喜欢比别人细点。他喜欢听别人没说出来的话,然后细细琢磨别人想表达的意思,把这当做一种乐趣。时间久了,他可能都没有发现自己说话也成了这个调调,话里面套着话。
当然,如果周杨能细心点的话,也许能发现了了的不同,比如说了了虽然说奇怪的周杨理解不了的话,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频,再比如说了了虽然经常以打击挖苦周杨为乐,但从来没有现在那么刻薄和拐弯抹角。入乡随俗,了了除非遇到词不达意的情况,否则一般都不用现代的词;周杨的大脑突触太少,海马体也比别人小,说太复杂太拐弯抹角的话他听不懂,说了一通,他还以为你在夸他,白费唇舌。
和别人说话绵里藏针,和周杨说话,针里夹点棉花就成。
今天的了了显然和平常不同,一张嘴就吐刀子,又快又利,外面虽然裹着厚厚的棉花,能叫棉花扒开的人少之又少,但只要刀子出了棉花,保管叫人伤的体无完肤。这话说给周杨就是浪费,了了说十句周杨也未必能懂一句。
也许了了就是想说给自己听的,压根没指望周杨能懂。也许了了就是单纯的说说。但无疑,了了很反常,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这种反常。
或者,他发现了,但想压抑这种反常,结果导致更反常。
反常有妖,反常必乱。
了了是不想乱,想瞒住这妖。
他假装太平盛世,其实是波涛暗涌,暗涌的太厉害,他的太平也粉饰不了了,起码他没粉饰了自己。
周杨的人格分裂,他要粉饰,他得护住周杨,什么鬼怪神佛他都得扛着。自己的诡异身体,他得粉饰,他想好好活着,他不想被当做唐僧肉给分了。能轻易的把别人的伤转移到自己身上,他要粉饰,他不想哪天被当做全自动的医疗器具。伤口愈合快的变态,他还得粉饰,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告诉他,最不显眼的人,往往是活的最长的人,他还不想显眼,他想活的长久点,起码不能唐突了一府三十二人的性命。
那三十二人的血液铺开的生路,他想每一步都好好走下去。午夜梦回故园旧事,他要粉饰什么都没有发生。梦魇勒住他的脖子,一声声的“少爷”抓住他往地狱里拖,他要粉饰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想好好活着,他想护住周杨,他就得********。一府三十二人的命成了他的执念,银线桃花氤氲开的一声声少爷成了他的执念,那个身上带着药香的温婉母亲的一句好好活着成了他的执念,把他拉出地狱的漫山风日琳琅成了他的执念。
他想,好好活着,护住周杨。
周杨帮了了擦脸的时候先看到的是咬破的嘴角,牙印很深,已经结痂了,周杨用布巾沾了温水细细的擦,十岁大的孩子,本来就没怎么侍候过人,平常又是粗鲁,这会子再小心也难免控制不住力道,周杨缩着脖子等了了喷。
半晌没动静,探探头,了了睁着眼望着房梁,眼睛直愣愣的,面无表情。
周杨心里有点发毛,试探着叫“了了?了了?”
“嗯?”了了转转脖子看到蹲在墙角的周杨,“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周杨问,“我叫了你几声你都没有听见。”
“我在想用你做下酒菜,今天的饭会不会格外美味?”了了含糊回答,用手支着床想要坐起来,周杨把被子卷成一团垫在了了的背后,想让他靠的舒服些。
“有饭么?”了了问。
“有。”
“噢。”
了了没再说别的,显然还在出神,周杨噔噔噔跑到灶房把饭菜端来,闻到饭香,了了的大脑才像搭上线,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了。
伤口愈合需要能量,对于自己来说,能量的来源从哪?进食?了了很快就否决了,且不说杂粮的营养价值太低,周杨吃的也不少,没见他前一天断了腿,第二天就跟没事人一样,刚敲断的腿还在疼,但明显能感觉到细胞组织生长的瘙痒,了了感觉自己胃空的一阵一阵痉挛。
也许进食跟伤口快速愈合有一定的关系,但绝对只占一小部分,还有别的什么呢?还有别的什么是能脱离能量守恒定律而存在的呢?
了了敲敲头,想不通。瞥见周杨端着的炒蛋和窝窝头,更饿了。
先吃饭!别的后论。了了拿起窝窝头往嘴里塞。
看着了了的进食速度和进食量,周杨惊愕的挤出一句“我还以为你需要我的帮忙。”但他表情和眼睛都告诉了了他想说的其实是“你是饿死鬼投胎么!”
了了忙着吃饭,没理他。周杨坚持惊愕姿态不动摇,颇有天荒地老之势,了了凉凉的说一句“你不吃么?还是你指望你娘能来喊你回家吃饭?”
周杨的冰封始解冻,就着了了的筷子吃。
了了揉着明显凸起来的肚子消食,又开始双眼直愣愣的盯着房梁,想不通的事情太多,腿明显又是离痊愈不远,了了敢保证,明天,绝对又可以活蹦乱跳。难道……还要再砸一次?或者很多次,好一回砸一回?要不怎么向别人解释?可是自己难道就能保证重新砸断腿别人就发现不了,尤其是还在家里住了一个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的专业医师的情况下,新伤旧伤明显就不一样。
况且,那种砸断腿的疼,了了索瑟了一下,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死了也许会更好。
坦白?了了想了想这个可能,抿嘴笑了,爹爹和娘亲也许能保守秘密,周杨呢?怀清村人呢?就算能瞒过这一回,下回呢?下下回呢?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在再什么有致命的伤?同样致命的伤,为什么你活了下来别人就不能活?同样吃五谷杂粮,凭什么你就比别人伤口愈合的好,愈合的快。人是最不能求同存异的动物,控制不了,了解不了,而又不能从上面获取利益的东西,除了才是最安全。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了了揉肚子的手停了,笑容裂的更大。
看见了了笑的莫名,周杨把手放在了了眼前晃了晃,没见反应,周杨喝了最后一口粥,坐在床边帮了了揉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