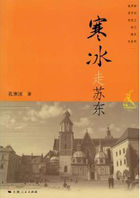这还不够,谭震林是65岁的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种种风雨,见到过党内多次重大斗争。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他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义愤填膺地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他指名道姓责骂起江青来,使会议室气氛更加紧张。
谢富治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也许是为了给江青辩护,朝谭震林摆摆手,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你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不吃这一套,手拍着座椅,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当时,如果有江青出面保谁,谁自然就有了一顶保护伞。谭震林却坚决不要。在场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对谭震林的态度表示“义愤”,叽叽咕咕,也没敢大声说。
谭震林越说越来气,他站起来,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他跨出一步,又回过头来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边说边往外走。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就要出现有人愤然退席的局面。
人微言轻,会议召集人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他不能让谭震林这样离开会场。
周恩来站起身,很严厉地说:“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陈毅元帅也劝他:“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看着几位老战友,谭震林似乎明白了什么。陈老总说得有道理,是要留在里面斗争啊!他放下了皮包。
陈毅元帅借题发挥,讲了一段也相当厉害的话:“这些家伙上台(指蒯大富之类),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说到此处,他望了周恩来总理一眼。总理的脸色很严肃,紧抿的嘴角好像在说:陈老总,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陈毅的脾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谭震林有相似的地方,说起话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又把“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扯到了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对整风运动中极“左”的做法不满。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
周恩来说:“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又转向康生,说:“康生同志也被整。”
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珠子一转,说:“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我不是挨整的。
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
康生可谓旗帜鲜明,给陈毅一个“下不来台”。
陈毅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余秋里站了起来,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抢白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阵垒已经十分分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此时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李先念操着浓重的湖北腔,指责“中央文革”:“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谭震林留在会上,他的气没有消,也不可能消,说话的口气依旧:“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我也哭过几次。”××说。
谭震林拍着手里的皮包,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
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忙说:“我也没有看。”
他们所说的《红旗》13期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主要精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篇社论发表前,陈伯达、康生都看过。见到老同志们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篇社论,他们又都改口说没看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这类政客惯用的伎俩。
谭震林的思路,随着李先念的话题扯到了瞒着中央批发军委、总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他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是什么?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
问题越扯越多,话越说越长,当时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只是低头记录。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
本来预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也只好作罢。
从紧跟到抵触再到抗争,谭震林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要公开反击
谭老板因“二月逆流”而声名大震。
说起“二月抗争”,笔者访问过的几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说谭老板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是这个”!
是的,听听怀仁堂里“就是砍头坐牢也要斗争到底!”的铿锵之声,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物。
然而,谭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干?他为什么敢这样干?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思想脉络是怎样的?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解开这其中的谜团,笔者曾经往返于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马路,寻找一个又一个的知情人士,终于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弄清了谭老板在此前后的言行及思想轨迹。
假如说,谭老板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谭老板本人也反对这种说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点燃的时候,谭老板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并不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权势会那么迅速地膨胀并祸国殃民。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合拍。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投身在这场“反修防修,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来。
对此,谭震林曾经说过,刚开始,我们不了解主席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图,还是他们自作主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时候,谭震林也曾决定向农业口所属院校派工作组。
“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时候,谭震林曾经跟随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待过来京的外地“红卫兵”。
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学院等大专院校的运动开展起来后,谭震林曾经到学校看大字报,同“造反”的学生谈话。
在林彪的主持下,谭震林曾经参与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文件。
……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积极参加,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搞这场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势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反动面目也需要一个过程。至于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那就更是艰难而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了。
面对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局面,谭老板的疑虑越来越深。他是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如果农村都造起反来,8亿人口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他找到刚到中央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诉说了心中的疑虑。在陶铸的支持下,经请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这个规定,定下了许多“框框”,诸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得参加县以下单位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季节,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等等。
规定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应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上级党委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这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形势,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人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
的典型材料。文件成了他们攻击诬陷陶铸的重要内容。
1966年的金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发表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且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这些,都引起许多老同志的反感。
吃饭桌上,会后散步时,谭老板和陈正人、江一真等同志议论,觉得陈伯达的报告有许多片面性的东西,不那么实事求是,而且把问题上纲上线。江一真说:“不少省委书记不同意陈的报告。”谭老板也说:“对反动路线的‘反动’二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他们的这些议论,被专爱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听到了,捅到上头,同时告诉造反派组织,让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加以批判。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果然,在正式的小组会上,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报告,讲群众群众,不讲阶级观点,不讲阶级路线……”“没有强调党的领导,光讲群众,没有党的领导。”
针对陈伯达讲的多数、少数问题,谭老板火了。他说:“少数就好吗?多数就不好?在农村,地富反坏是少数,贫下中农是多数,该怎么理解?……”
这些话,当然很刺陈伯达的耳朵。引起他们对谭震林的不满,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些,仅仅是铺垫。一些令谭震林目瞪口呆的事情相继发生了——贺龙的家,被“造反派”冲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代开国元勋,不得不在周总理的帮助下,住在中南海里面。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同外面的相勾结,透露了消息,外面的广播车开到中南海门口,不分昼夜地高喊:“打倒贺龙!”声言:“不揪出贺龙绝不收兵!”周恩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将贺龙转移到西山……谭老板得到消息后,气得手直抖,说:“这像什么话!”
陶铸被打倒,是典型的“突然袭击”。1967年1月4日下午,陶铸正和周恩来总理等人开会的时候,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公开点陶铸的名,说他执行“刘邓路线”,应该被打倒。谭老板问司机:“是打倒陶铸吗?”司机确认无疑。他沉默不语了。他找到李富春,开门见山地问:“要打倒陶铸吗?”“不知道哇!”“这就怪了!”要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而另一位常委却根本不知道。可见当时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地步!“陈伯达有什么资格讲陶铸的问题?”李富春说:“这得问主席去。”据说,李富春真的去问了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此事,因而引出了后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政治局委员,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委员!”
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相继出现了“曙光”,响起了“春雷”,一场遍及中华大地的夺权斗争全面展开。谭老板愈来愈想不通:共产党的权力机关都被推翻了,还能叫“革命”吗?
一批和谭震林很熟悉的老同志、老部下被打倒,被批斗,被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们刚住到京西宾馆,谭震林就去看他们。
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李葆华等老同志见到谭老板,纷纷诉说心中的愤懑和本人的遭遇。“老板啊,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老板啊,得想想办法啊!”他们的肺腑之言,使谭震林吃不香,睡不着。他们被接到北京来还难保得住,那些来不了的同志呢?井冈山时期仅剩的女同志之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竟不明不白地被整死在厕所里……
那段时间,他时常去李富春家里,同富春交换意见,和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一起忧国忧民。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他说过许多“出格”的话:
“叫那几个秀才(指‘中央文革’)乱搞,国家不垮才是怪事!”
“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他们的野心大着哩!”
“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
“应该找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