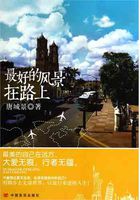从1887年的春天起,他便常去克利西街的“铃鼓”咖啡屋。这幅《铃鼓咖啡屋的女郎》就作于那一年夏天。画中的妇女大概就是这间咖啡屋的女主人奥古斯汀娜,她以前曾当过得加的模特儿。从画上可以看出,凡·高在店内的墙壁上装饰着他喜爱的日本版画,并与贝尔纳、高更、劳特累克等利用此店举行画展。对莫奈、毕加索为首的正统印象派画家来说,他们自称为“反正统的画家”。这一幅画用细微的笔触所形成的律动交响与色彩并置的手法,表现出他有一段时间曾学习过修拉、西涅克的点彩法。
《孤鸟翔空的麦田》作于1887年夏天。这幅画使人有明朗清澈的感觉,好像可以听到远处清新的歌声和潺潺的流水声。
凡·高采用修拉与西涅克的色彩分割理论,又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学习到短促笔触的并置以及从光线中捕捉色彩的瞬间变幻,以色彩的视觉混合手法来表现。
这幅画的彩度高,向上向下的短促笔触,使画面洋溢勃勃的生气:云、麦田以及草地均富动态,云雀的声音暗示了在画面上看不到的垂直轴。麦穗顺着风向俯身,仔细观看会有一种写实的感觉,同时让人感觉在遥远的彼方有一种并非实在的憧憬。
1887年的暮夏,凡·高一口气画了四幅向日葵,给人感觉无比的逼真,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右面的这一幅可视为凡·高画集的代表性作品。孩童时代的凡·高就喜爱鸟巢,这种喜爱可以说是他幻想特性的本质。由他的素描习作可以看出,他尝试着要捕捉由中心向周围旋转的辐射和分量感。他后来到法国南部追求太阳,就是对于旋转、炎热的天体的一种深切渴望。事实上,向日葵就是生长在大地上的太阳(法语称向日葵为旋转的太阳,英语称向日葵为“太阳之花”)。
铃鼓咖啡屋位于克利西街62号,凡·高和提奥同住的公寓也在这条街附近。《克利西街》这幅画采用了色彩视觉混合和笔触的轻妙律动,以表现街道上早春的气氛。在右方的树木是横线笔触,在中央的街树上则可看到简短笔触的轻快飘动,让欣赏者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空气流动。这些与前景道路散落的笔法相映衬,构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空间流动感。色彩上则使用淡紫、淡褐与蓝色为基本色调,这种柔和的色调来自日本的版画。
在巴黎时期,他想捉住艺术上的轻快感,便以轻快为主题画了数幅同类的风景画。
《兰格罗瓦桥》于1888年2月21日创作。凡·高到达法国南部的阿尔并住在卡列尔饭店。这一张是他到达后的3月间所画的。凡·高在信中写道:“今天的工作是画一张5号的画-那是在蓝色天空下,一辆小马车正通过的一座吊桥,和天空同色的河水、绿草、橘色的河堤,还有一群穿着各色衣服的洗衣妇女。”这一张画的色彩清澄而果断,有如金属管乐器奏出的嘹亮声响。天空是一片蓝,水波荡漾的运河,均远离巴黎的喧嚣,漫游在郊外的凡·高,仿佛可以听到他自己快活的气息。这座吊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破坏,现已另在别处建筑新桥。
1889年凡·高从阿尔医院返回“黄屋”。这期间画了两幅自画像,都是右耳包扎着绷带,口里衔着烟斗,头戴毛皮帽。一幅以红色为主色,一幅以淡绿色为主色,背景采用日本版画。由这段时期的信里可以知道他的健康在一天天地恢复,但是他对高更的歉疚仍没有消除,他还表示,以后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作画,不能再陷入过度的焦急。
这幅自画像可以说是透过他自己的眼睛,展望未来,具有一种明确思想的表现。
1890年2月中旬,凡·高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能够提笔写信时,他告诉提奥:“工作很顺利。最后一块画布是画盛开的杏花。你或许可以看出,这是耐着心画的好画。我以冷静的情绪,使用比平常较大的笔触,真实地描绘,但第二天就不行了,这的确令人费解和无奈。”凡·高的母亲在2月15日写信告诉他,提奥夫妇在上月底生了一个男孩,因此他画了这张有“青色背景的天空,数枝开着白色杏花的粗枝的作品”。以便挂在侄儿的寝室。在这幅画上,他运用浮世绘与大和绘式装饰花草图的画法,画下了枝叶和杏花。
挚爱深夜的凡·高,在阿尔时期曾有两件作品描绘星空。在圣雷米的初期画的这幅《星月之夜》是凡·高深埋在灵魂深处的世界感受,体现某种宇宙进化的思想。星云与棱线宛如一条巨龙不停地蠕动着,暗绿褐色的柏树像一股巨型的火焰,由大地的深处向上旋冒。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回旋,转动,烦闷,动摇,在夜空中放射艳丽的色彩……这种回旋式的运动圆形,有如远古时代的土器形体或者装饰在土器表面的螺旋花纹。
在德拉克洛瓦或巴洛克的艺术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回旋的曲线和旋转的运动,但其真正的源头,恐怕还是来源于人类的潜意识之中。促成凡·高产生这种原始意识的,一是得自于农民以劳动征服大地所带给他的共鸣,二是他对德拉克洛瓦的佩服,三是对于日本浮世绘画家北斋和广重的构图主题的把握。在西欧传统绘画的远近法中,画家们常常从观众席来观察舞台、风景与人物。但是对凡·高来说,在他病情尚未发作之前,已感到被另外一个神秘世界监视着。他察觉到受苦恼、受烦闷的,不只是他本身或者如向日葵那样的对象,而是能够把一切万物都包括进去的广大范畴。
这一幅画与《群鸦乱飞的麦田》、《多比尼庭院》,是凡·高在奥弗所作的最后三大作品。凡·高在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这幅画时说:“我正埋头作一幅以像海那样广大的丘陵做背景,有黄色与绿色微妙色彩的广漠麦田的画。这一切存在于青色、白色、粉红色、紫色等色调的微妙天空之下。我现在非常的安宁,肃静,可以说很适合于作这幅画。”同《群鸦乱飞的麦田》比较起来,这幅画含有可怕深邃的寂静,好像要吞没凡·高的一切。在地平线那一端所表现的,不再是德伦特时期作品中可看到的灵魂之憧憬,而是要将他的身心召回的凄美恐怖的压迫感。
这幅画充满着恐怖不安的感觉,凡·高似乎已经超越了灵魂上的生死境界,置身于另一世界的试炼,并试图将此世界置于笔下。他在信中写道:“我的生活,从根基上被破坏,我的脚只能颠跛着走。”这正说明当时他画下这幅悲惨的画的心境。“我担心,我是否变成你们沉重的负担……那时候-回到这里再开始工作-画笔几乎从手中滑落下来……可是,从那时起我画了3张大的作品。”画上的线条很生硬并且失去了次序,不但天地鸣动,所有的凄切、悲哀和绝望,都似乎从地平线的那一端飞扑过来……这幅画是离开圣雷米疗养院之前所作的。凡·高与贝伦博士及提奥商量后,决定离开南法,前往加歇医生居住的奥弗。据633信称:“于此作最后的挥笔,所以我尽情地忘我地工作。”1890年5月17日,凡·高只身前往巴黎,留下了这幅作品。对于这张画,他曾作这样的说明:“紫色的花束,在鲜丽的柠檬黄背景下浮现,而花束本身另有黄色的色调。
放置花瓶的台面,表现出不配衬的补色效果,但这种强烈的对比,格外显明。”凡·高给妹妹威丽明和弟弟提奥的信上,都曾提及此画,似乎他本人好像很欣赏这幅画。
自画像是凡·高绘画艺术中最大的特色之一。在西欧绘画史上自画像数量较多的画家有好几位,但最多的,是同属荷兰籍的17世纪的伦勃朗和19世纪的凡·高,他们堪称自画像中的双璧。他们二人分别以自己的画笔描述各自的生命瞬间,完全真实地凝视自己,表现自己的心灵。
比较两人的自画像,会发觉有很大的差异,伦勃朗在40余年的画家生涯中,像自传似的,用自画像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现存一百多幅。而凡·高,在他10年的画家生涯中,仅仅以3年半的时间,便画了约42幅自画像,不愧是自画像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