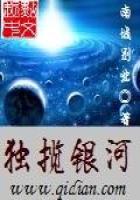全书分四部分,绪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进化和教育的概况。作者的写作宗旨是为国人,尤其是青年提供一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提供批判的新武器和新兴社会科学的新见解。在第一章教育的本质中,作者阐述了教育的起源,教育的作用和效能,并力图澄清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第二章教育的进化,历叙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正在开始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意义的变迁,教育制度的更易之事实及其理由,使读者由此明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教育具有不同的特点,教育是受他种根本要素支配的。第三章教育的概观,作者论证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制约,指出教育由政治、经济所决定,同时反过来也可以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书中还阐述了教师和学生的问题,呼吁教师和学生走向民众,走向社会,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
总之,《新教育大纲》之所以以上述三个方面为论述重点,最根本的是为了表明作者的立场,即与当时一般流行的教育理论反其道而行之。杨贤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时流行的教育学说,对于教育意义的变迁,制度的变迁,其理由何在,其作用何在,它们是不讲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与经济的关系如何,它们没有说明。教育这架机器被贼偷了去,当作鸦片来毒害人,它们没有晓得。反之,它们要说教育如何神圣,如何清高,如何独立,如何公平,如何科学化,如何民众化,乃至教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解决民生……一大堆的对教育歌功颂德的丽字美句。”而作者正是要大声警告读者:“教育是阶级的,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从文明开始以来,只有阶级的教育,没有全人类的教育;只有对立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育。”
《新教育大纲》于1930年2月初版,同年9月即再版,尽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售,但许多革命青年仍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这本著作,一些进步学校把它作为教学参考书,一些倾向进步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该书的基本观点。在革命根据地,此书更是成为师范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读物,因买书困难,许多章节被刻成油印讲义广为流传。《新教育大纲》为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和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批判旧教育的武器和认识新教育的钥匙。
《新教育大纲》是杨贤江一生主要教育思想的概括,在这部力作中,作者并不是简单地转述或注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教育的学说,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联系中国社会实际,运用自己积累的大量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丰富知识和材料,把教育置于整个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世界大势中加以分析和把握,使他的著作不仅立论科学,观点新颖,而且言之有据,生动易懂,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难免存在一些阐述不恰当、不全面、认识不够深入的地方,但这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的特殊需要,是无需也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杨贤江通过译介大量有关苏俄教育的理论和实际的书籍、文章,使我国教育界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认识,直观地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应用,并从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新教育的前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撰写的《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更是直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在我国近代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钱亦石和林砺儒等人。钱亦石所著《现代教育原理》,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该丛书专为中等学生课外阅读,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作者在卷首的例言中表明,该书体系系个人所创新,意见亦大半由“暗中摸索”而来,在执笔时,一方面注重于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社会实际,另一方面强调教育不是孤立的范畴,而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应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联系。
《现代教育原理》共有9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作者指出,教育与整个客观世界一样,始终处于动荡和变迁之中,教育由社会存在所决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变动,并提出了适应新时代的新教育原理就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这是新教育原理的两大基石。可见,作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后,能超越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中国教育的根本出路所在。第二章论述教育的本质和目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的本质不是神圣、清高,不是中正、独立,它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由此澄清了“教育万能”的错误见解。至于教育目的则因时、因地而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其教育目的亦各有特殊性,这是不可混同的。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阐述了教育的生物学、社会学及哲学基础。作者认为教育既要从儿童的特殊兴趣与需要出发,又要注重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联系是社会的基本联系,因此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造就多方面发展的人之唯一方法;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阶级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权才真正回归广大劳动群众,公共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普及,这代表了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在阐述教育与哲学的关系时,作者把辩证的宇宙观看作全部教育原理的原理,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为指导,强调学校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要“行以求知”。第六章到第八章,作者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分别阐述了政治教育、生产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教育是受政治支配的,中国现时所需要的生产教育应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文化的形式与内容跟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最后,作者把这三章归纳为,“民族独立的政治教育、机器工业的生产教育、大众享受的文化教育”,并指出三者间,民族独立是保证,机器工业是条件,而大众教育则对前二者的实现大有裨益,因此,三者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三位一体的。在最后一章即第九章,作者以“教育与人类前途”为题,充满信心地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的美好前景,宣告了资本主义必将在新时代光临之前死亡。指出教育在此应发挥自己的效能,但这一效能绝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必须与整个基本运动战线统一起来”,“教育界孤军奋斗是没有出路的。”
综观全书,作者处处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教育现象,阐释教育原理。书中抨击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新教育。从书后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也可看出作者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所列13种书目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以及苏联教育家平克微支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杨贤江译《新兴俄国教育》和杨贤江著《新教育大纲》等。
林砺儒所著《教育哲学》(1949年开明书店出版),亦是近代中国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林砺儒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强调要以此作为进行教育批判和构建教育理论的指导思想。在《教育哲学》一书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来阐述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和方法等基本问题。如,指出任何哲学“都反映所属时代的经济生活状况,反映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底程度,并表现特定社会集团利益和希望,教育哲学也是如此”,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性。作者通过对现代教育学演进的回顾和分析,批判了以往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是世界上破天荒首次出现的最正确的政治理论、革命理论,也就是指导教育的理论”;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而“我们的教育理论就要从人民革命,社会转型的环境中,通过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探究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作者还强调了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一定要立足中国实际,有选择地学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往在世界上流行的各派教育学说,各种教育制度、教育方法,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判、扬弃,而决不能像旧时那样盲目地摹仿抄袭”。总之,林砺儒以其《教育哲学》及其他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苏俄式”社会主义新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发轫于30年代初的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基本成型,1945年之后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而日益扩大其影响。这一教育实践模式既是对中国传统旧教育和国统区西式新教育的改造批判和扬弃,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在教育领域里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创造形成的,其丰富和生动的内容,不仅为当时的争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和宝贵遗产。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革命根据地实际需要的结合,鲜明地体现在根据地教育从方针政策的制订到各级各类教育的实施,从教育的目的、内容、组织形式到方法手段等各个方面。尽管在这几十年中,根据地自身在不断发展变化,各个时期的教育也随之发展和变化,但从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总的性质和状况,革命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严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质的相对匮乏等总体背景和条件基本相似,因此,各个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教育,虽然也存在变化和差异,其总体特点还是一致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事业服务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就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提出了总方针,即“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就目前的教育任务明确提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7月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政策,就是要用教育来支持抗战,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由此,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训练千百万优秀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设者,便成为这一战时教育模式的主要目标;注重政治教育、干部教育和大众教育是其鲜明特征;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为着战争则是其根本内涵。抗战胜利前夕,面临新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又及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具体纲领:“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