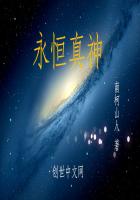一无所有,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自我救赎的一种办法。他说。他早就看透了,物质财富在给人提供享受的同时,也给人套上了羁绊。他这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男人,可不想戴上什么枷锁。掠夺,攫取,占有,这些人类的通病,他总是想躲得远远的。他从小就不喜欢有产者,一直都不喜欢。他这样说过,我仇恨资产阶级,这个仇恨到死方休。当有人提醒他,来看他话剧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时,他想了想说,我与这些来看我戏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喜欢一无所有的萨特,他是不会跟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
什么都不是我的,我什么也不占有。他说。如果说一定要他占有些什么的话,他只想占有词语,他也占有了词语。在我对语言的关系中,我曾是所有者,我现在还是所有者。他说。
如果我的父亲给我留下财产,我的童年就会大变样,我就不写作了,而会变成另一种人。他说。他不想让财产这些身外之物改变了他这个人,他只想做一个他想做的那种人。
我想做一个没有土地和臣民的国王。在戏剧《苍蝇》里,萨特借主人公俄瑞斯忒斯之口说。
4
70岁的时候,萨特对一个记者吹大话说,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对,经常有一百多万法郎,是现金,现在手头就有,伸手就可以拿到,就像香烟打火机,就像眼镜,就像衣服。而且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这样的。看来,萨特是个有钱人。
萨特手头的钱,是他自己写出来的。他一辈子都在写作。他写作时从来没想到钱的问题,也从未为钱写作过任何一篇东西,他写作时更不曾感到自己是在挣钱,他甚至根本就没考虑过这辈子会不会有钱。当他要成为一个作家时,想的就是要写出那种非同一般的作品;当他成了著名大作家时,想的是要写出更好的著作;他出书时,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但他却得到了钱,得到了很多的钱。每个月都得到一些钱,时常收到一大笔一大笔的钱,这让他感到十分奇怪。在他看来,这跟他的写作,跟他的作品是没有关系的,也不应该有。但事实上就是有了关系。在作家萨特看来,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吧。
我觉得钱是别人给我才得到的。就这个角度上看,我一无所有。而且我有点敌视钱,不是因为我不想要钱,而是因为我宁愿没有这个许可证而得到我想的东西。萨特说。这样的萨特很可爱。
在某种意义上说,钱对我是不存在的。我得到了它,然后花掉它。我只要有钱,就自由自在地花。钱对我就像是给了我,而我又把它拿出来共用的资金。萨特说。这个萨特有点怪怪的。
对我来说,钱是某种外在于生活的东西。我想生活不是由钱形成的。但我每做一件事都得用钱。萨特说。这样一个萨特很深刻,很真实,很有趣。
萨特说自己长期以来,甚至几乎整个一生,都没弄清楚钱这玩意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对钱的态度中有很多奇怪的矛盾。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萨特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男人。
对萨特知根知底的波伏瓦,说他对钱有一种农民式的态度。他从来就没有一个支票簿,而总是把钱全带在身上,是那种活动的现钱。出门在外时,他把钱都装在口袋里,当需要付一千法郎的账时,他可能会拿出十万法郎的一把钞票。他花钱是从不算计的,但却又时常担心。所担心的并不是缺钱用,而是担心要被迫地去算计。
要知道,他所担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在为别人担心,为那些要他帮助的人而担心。他的钱大多是给了别人用,主要是些女人。说白了,他是要养活一些女人,多是他的情人。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养活大约六七个女人呢。更早一些时候,要他帮助的,或由他养活的人更多一些。他被借出的钱更多,不论是女人或是男人,或近或疏,只要你开口,只要你有理由(任何理由都行),只要他当时手头有,他就会马上掏给你,甚至会全都掏给你。碰巧的是,他总是有钱的,手头就有很多。他从不把钱攒起来,放起来,存起来,他一定要把它们大把大把花出去,就像是这东西不好玩儿,很烫手,他得赶紧把它扔出去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花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摆脱钱,把钱像手榴弹一样扔得远远的。他是有钱,但他从不想拥有它们,他并不想做什么金钱的主人,当然更不想做金钱的奴隶,他要让它们流走,他要让它们失去,他要让它们烟消云散,钱对他来说是身外之物,他可不想总是把它留在身上,就像人来自泥土,还要归于泥土一样。
5
写《文字生涯》时,萨特就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件文化家产罢了。
这时候,不知道他考虑到了没有,由他带来的文学遗产问题怎么办?精神方面的不必说了,这种丰富的文化遗产早就奉献给世人了,它们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们是不朽的。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如波伏瓦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人总是要死的———他的作品,他那么多作品的版权,由此带来的巨额财产,将留给谁来继承呢?
实话说,萨特没考虑过这种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他可以不去想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会找到他头上的。
于是,就有了出版商和萨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段对话:我死后,所有的作品都归波伏瓦。你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结婚了吗?没有,当然没有,你知道的。你很爱她吗?
当然。你打算跟她结婚吗?不。
那么,你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的家族,属于施韦泽家的人。
事实上,波伏瓦最后也并没有成为萨特的遗产继承人。
继承了萨特的遗产的,是一个名叫阿莱特·埃凯姆的女子,她一开始是萨特的情人,后来成了他的养女,经过了法律手续的。此女子,给晚年萨特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与安慰。
对此,一生与萨特相伴的波伏瓦并无异议,她也没有在意太多,真的没有。波伏瓦与萨特相爱一生,从来就没想到过萨特的遗产什么的,她没跟他要过名分,没跟他要过一个家,没跟他要过婚姻,她要的只是萨特的情感,要的只是和萨特在一起,要的只是她和萨特之间那种永恒的爱情。此生有了和萨特的永恒的爱情,在她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满意了,已经足够美好了。
再者,波伏瓦本人早就是声名显赫的作家了,她凭自己的版税收入,生活已是绰绰有余了,她还要萨特的那些遗产做什么?
事实上,萨特离开人世间的时候,波伏瓦本人也到了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一个老人,对另外一个老人的遗产显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了。
6
我写作过,我生活过,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老萨特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这样跟人说。他的这句话,和他一直奉为榜样的司汤达的那个墓志铭很相像: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但好像萨特有意地漏掉了其中的一句:恋爱过。而且,萨特是轰轰烈烈地恋爱过了,热热闹闹恋爱过了,而且一直到老了他还津津有味地恋爱着呢。
写作过,生活过,恋爱过。对于萨特来说,这一切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美妙的。至于像什么家啦,金钱财产啦,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遗产什么的,那就是他死后的事情了,与他萨特,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