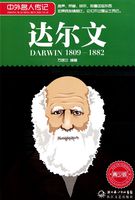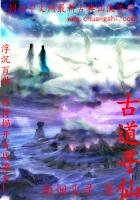1
一条绳子上拴着的两只蚂蚱,跑不了你也飞不了我,又是三角恋爱,又是“四重奏”,显示出五颜六色,有些让人感觉着乱七八糟,但是九九归一,到头来,还是你爱我我爱你,而这一切又是十分复杂而有趣的……
关于萨特和波伏瓦两个人一生的爱情故事,我用如上这些带点谐趣味道的数字游戏,做了一个概括。
为何不可以游戏一下呢?其实,萨特和波伏瓦的爱情,尤其是他们共同商定的那种协议和原则,也多少带有某种游戏以及游戏规则的味道,不过是他们玩这种游戏时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是全身心投入的。
2
有一段时间,身为哲学教师的萨特被一层层困惑和迷茫包围住了。那是因为个人的职业和事业,都一样不能令他满意。虽说他喜欢教授哲学,也很喜欢自己的那些学生,但是他极其讨厌那些官僚机构,也看不上什么校长和副校长以及同事,他觉得这些人很无聊且无趣,跟这些无聊又无趣的人共事,当然是很没意思的。而在他所最看重的哲学和文学事业上,也尚无任何辉煌的成就,他还没有写出任何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向往着名望和光荣的萨特也就日益焦虑不堪起来。再加上从柏林回到法国之后,和他情感上,尤其是性关系上,亲密者只有波伏瓦这一个女人了,尽管她是他精神上的唯一安慰,他十分珍惜这份难得的情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唯一,在萨特的感觉中不免有些单调,缺少了那种新鲜和激情的刺激。眼下这种看起来很糟糕的生活状态,可不是萨特这样一个男人想要的。他想要的是那种新奇的,变化不居的,充满着激情的生活。
这时候,受人之约,萨特放下手头的小说,开始写一部叫作《想象的事物》的哲学著作。由于焦虑,由于(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和(日常意义上的)生活带来的压力,由于对幻觉和梦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注射了那种据说能令人产生美妙幻觉的麦司卡林。幻觉倒是产生了,但并不是那种玫瑰色的幻觉,而是幻化出了各种怪异可怕的东西(比如钟表变成了猫头鹰),并且就此紧紧地缠住了萨特,他一天天地望着日常的事物发呆(比如盯着电话线,盯着一双皮鞋),像个抑郁症患者,像个精神病人。不是像,有时候干脆就是。
那么爱着萨特的波伏瓦当然是很担心害怕的,又心痛得要命。此时,波伏瓦已由马赛调到了里昂来教书。遵医嘱,她不要萨特一个人待着,而是让他住到了里昂,由她来照顾他的生活。看护着病人萨特时的波伏瓦,就不仅仅只是他的情人,同时还像他的母亲,像他的姐姐,更像个知冷知热的妻子。波伏瓦这么陪伴着的时候,萨特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但当时波伏瓦是个教师,她时常得去为学生上课,不可能时刻陪着他。碰巧的是,她身边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闲着无事,波伏瓦就请她来照看病得不轻的萨特。
波伏瓦这么做,可以说是成心的,也可以理解成是无意的。反正是由于她的这种安排,就埋下一颗微妙而复杂的情感种子,而且它很快就破土萌芽,绽开出一束绚丽夺目的花朵,可它终还是荒芜,且有毒,并没有结出理想的果子。
3
这个被委派去照顾萨特的姑娘,就是波伏瓦最亲密的学生奥尔加·柯萨凯维契。这个小波伏瓦九岁的姑娘并不简单,她已经迷住了自己的老师波伏瓦,还将更深地迷住波伏瓦的男人萨特。
奥尔加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个俄国贵族,十月革命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逃亡到了法国。由于命运的驱使,奥尔加就成了波伏瓦班上的学生。在头一节课上,波伏瓦就注意到了这个有着一头披肩金发,一张美丽而苍白的脸,一双明亮而忧郁的大眼睛,一副懒洋洋但神态与众不同的女生。不久,波伏瓦就发现“小白俄”奥尔加是个聪颖、单纯、敏感、孤僻、傲慢,易冲动,才思敏捷,不太好调教的姑娘。这印象一点也不坏,至少很特别。而波伏瓦总是对特别的人与事感兴趣的,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很特别的姑娘。她喜欢她那种漂亮而气质不俗的样子,喜欢她那种纯洁而直率的样子,喜欢她那种狂热,那种激情,那种自由不羁的样子。其实,女性之间也一样存在着心灵感应这种东西。在波伏瓦喜欢上奥尔加的同时,后者也喜欢她这个才貌出众的老师,她佩服她,甚至崇拜她。这种相互的喜欢,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友情,超越了年龄和身份的友情,甚至不仅仅是友情。那是什么呢?说白了,那就是一种亲密的同性恋,尽管波伏瓦并没有明确地承认过这一点。但事实上,就是如此,她们就有当事人不愿启齿的那种关系。后来,波伏瓦追记这种情感时这样说道,奥尔加对我的情感迅速达到了燃烧点。同样地,波伏瓦对奥尔加的情感也十分炽烈。不然,她就不会对奥尔加说出这样的话了:就目前而言,只有两个人对我的生活构成意义,而你,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是指萨特了。
由于波伏瓦的这种喜欢,由于奥尔加不喜欢接受学校的“监禁”,经过和萨特的商量,又最终经过了奥尔加父母的同意,由波伏瓦做了奥尔加监护人(实际上是把她供养起来了),为她租了旅馆里的一间房子,并为她制定了周详的读书及写作计划,波伏瓦单独辅导她哲学课,必要时萨特也可一起辅导她。
奥尔加这位可爱的姑娘,是命运给予波伏瓦的一个馈赠,而波伏瓦把自己所拥有的学识的情感馈赠给了奥尔加。现在,波伏瓦又把她所喜爱的姑娘奥尔加,以一种特别的形式馈赠给了她那个病中的男人萨特———让她去照顾他。
而奥尔加,早就知道萨特这个很有些传奇色彩的男人了。波伏瓦跟她说起过他,说起过她和萨特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奥尔加像别人一样,觉得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太神奇了,甚至有些惊世骇俗。现在,要由她来照看这个患有抑郁症的男人了,其兴奋和喜悦之情就不难想象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味盎然的事情。正如萨特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人在喜欢他和波伏瓦的同时,都会对她或他怀有某种强烈的嫉妒,最后他们往往会由嫉妒变成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们的理由如此纯粹,有些人甚至没有见过她或他。
果然,奥尔加一见到萨特,就喜欢上这个有着非凡魅力的男人,她觉得他非常浪漫,身上有着某些中世纪骑士的精气神。而且他那么博学,那么幽默风趣,那么温存体贴。无数个漫长的下午,奥尔加和病中的萨特一起唱歌,读诗,讲故事,玩游戏,合演小戏剧。有了漂亮可爱的奥尔加在身边,病中的萨特觉得精力充沛,病魔节节败退了,他脸上时常露出快乐而幸福的笑容,看到自己的男人一点点地好起来,波伏瓦很欣慰。而奥尔加呢,看萨特这样一个男人如此需要她,并能给他带来欢乐,她也倍感快乐。
这时候,他们三个也许已经有人意识到,或者同时意识到了,一个十分微妙而复杂的情感故事,正犹如一个调皮的精灵那样,跳着细碎的狐步舞,悄然潜入他们共同的生活了。
4
喜欢。一见就喜欢。萨特一见到奥尔加就喜欢上了。在他恰逢哀叹日常生活的重复单调,缺少新鲜刺激的时候,波伏瓦把年轻漂亮的奥尔加送到了他眼前———这不啻是他瞌睡时,你送来了一只软枕头,他想垂钓时,你递给他一个钓鱼竿———他不喜欢上她才怪呢。
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对于出现在眼前的年轻漂亮的女子,只要有可能,萨特总是会喜欢的;即使不是太可能,他也要尽力把它变成某种可能。或许,萨特认为一切皆是有可能的,只要他愿意。再者,他挚爱波伏瓦,爱屋及乌,波伏瓦喜欢的姑娘,他觉得自己也有理由去喜欢,他没有理由不喜欢她。
萨特之所以喜欢上了奥尔加,当然因为她是个鲜活而漂亮可爱的姑娘,同时也因为她还是一个象征,她象征着美丽的青春,象征着生活中的可能性,象征着神秘的奇遇,象征着甜蜜的冒险,象征着偶然的爱情,而这些呈现在奥尔加身上的象征,都是萨特想要的,都是萨特所要追寻的。
我对奥尔加的感情,就像一只煤气灯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一烧而光。多年以后,萨特这样回忆道。其实,这就是(漂亮)女性之于萨特个人生命的本质意义。
一开始,萨特只是喜欢奥尔加,但很快就爱上她了,就追求上了她,而且是那种十分疯狂的爱恋,是那种不顾一切的,使尽浑身解数的苦苦追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取悦于奥尔加,甚至努力把自己搞成一副年轻潇洒的样子,以期显得与奥尔加更般配些,他像那种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时时刻刻渴望见到奥尔加,渴望和她在一起,奥尔加的每句话,每个眼神,甚至每种面部表情的变化,都牵动着萨特的心,都影响着他的情绪。他对她关怀备至,甚至不希望别人再来关心她,包括波伏瓦,甚至在波伏瓦面前他也毫不避讳对奥尔加的爱,毫不掩饰对她的爱的表现。不仅仅是对波伏瓦不避讳,不掩饰,他还要给波伏瓦诉苦,诉他爱奥尔加,想占有她的爱而不得之苦,甚至还要把奥尔加拉到波伏瓦面前,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在母亲或姐姐面前,说说他和奥尔加之间的短短长长,请家长波伏瓦评个理,要波伏瓦替他做主。这样的一种关系,这样的一桩事情,身为局外人兼当事者的波伏瓦,她还能怎么样呢?我想,无可奈何的波伏瓦只有苦笑吧。
很显然,眼下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麻烦也就来了。
本来,波伏瓦是因为爱萨特,才让自己的学生兼密友奥尔加照顾他的,但他却不再只是喜欢她了,而是疯狂地爱上了她。
奥尔加本来也是喜欢萨特这个男人的,我和你在一起,真是异乎寻常的快乐。她曾多次这样跟他说,相信这也是她最真实的感受。但现在萨特爱上她,而且他想独占她的情感,甚至连波伏瓦也甭想与他分享。而天性自由的奥尔加呢,她可不想把自己绑在一个男人身上,哪怕这个男人是非凡的萨特,何况萨特是自己的恩师兼同性恋人波伏瓦的情侣!她不太情愿接受萨特的这种爱情,但她又不想明确地拒绝他,除了萨特身上有一种难以抵挡的男人魅力之外,其实奥尔加本人也是个骨子里喜欢并擅长调情的女子。所以,她与萨特的关系也就搞成了若即若离,不明不白,不推也不就,或送他一道秋波,或相互打情骂俏,或像恋人一样哭闹争吵,或玩鼠猫游戏,她就像一只狡猾的母鼠,逗弄着萨特这只馋猫,弄得萨特心里痒痒的,甜甜的,酸酸的,苦苦的。
而这一切,波伏瓦都看在眼里,酸在心里,苦在肺里。她那么爱萨特,看着自己的爱人一天天被激情所折磨着,为对另外一个姑娘的爱所苦,心里头很不好受,她只有苦着他的苦,还得苦着自己的苦。她心疼萨特,不可能去阻拦他;同时,她也十分喜欢奥尔加,跟她有着别样的情感,也一样不想多说奥尔加什么。既然她给了萨特以必要的自由,同样也应该把自由给予奥尔加。她理解自己的男人萨特,她也尊重她的女友奥尔加的行为。
如果说萨特和奥尔加之间有什么故事的话,她波伏瓦是干涉不得的,因为她不想干涉他们。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尽管有很多事情未必是她所愿意看到的。
其实,萨特也一样很苦。当然眼下他最苦的是,他特别想得到奥尔加却一直不能够,甚至对最后能否得到她都没把握了。同时,他对自己那全身心得到了的好女人波伏瓦一点点歉意都没有吗?我不相信,人心不是肉长的。
5
事情弄到这步田地,又能怪谁呢?
奥尔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似乎是横插了一大杠子的第三者,但她却实在很无辜。
萨特也是无罪的,至少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波伏瓦也不会那么想的。萨特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子,只要有可能,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他就会爱上她。
波伏瓦同样也是无过的吧。她深爱着萨特,她喜爱着奥尔加。她把她喜爱的奥尔加送到她深爱的萨特面前,只是为了他好,为了让他恢复健康,为了让他得到快乐。显然,她是出于好心,缘于好意的。她说,与其眼看着萨特在那种可怕的抑郁症中一点点地垮掉,我更愿意让他去追逐奥尔加,去争取奥尔加的青睐。她是这样想的:或许,萨特可以由此获得快乐和新生呢。
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谁也不怪吗?
有人说,怪就只怪波伏瓦;有人说,这是波伏瓦咎由自取;有人诬蔑说,奥尔加就是波伏瓦给她的男人萨特拉的一个“皮条”;有人更恶毒地说,波伏瓦这女人变态,她总是喜欢为情夫萨特“拉皮条”,等等。
对此,波伏瓦只是一笑了之,她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而辩护,更不会为爱萨特所付出的代价而懊悔。她只是爱萨特,她就是爱萨特,她就是这样爱萨特的,管别人怎么说呢?
退一步说,退许多步说,即使是她有意或无意地给萨特拉了所谓的“皮条”———把她所喜欢的女子介绍给她最亲爱的男人萨特———那也是她想这样做,她愿意这样做,这是她自己的事情,或者说这是她和萨特之间的事情。她所以愿意并且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犯不着别人来操心,更不要这个或那个闲嚼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