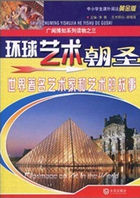华罗庚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只好把工人分成小组分别介绍统筹法,让陈德泉与计雷到现场去与工人一起劳动,制订统筹方案。辛勤的劳动终于获得成果,原计划25天完成的工程由于运用了华罗庚、陈德泉与计雷的统筹法试工方案,结果仅6天就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了任务,一天为国家多创造价值20万元。工人们振奋了!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统筹法是专门为减轻我们的劳动而研究的,我们为啥不能大张旗鼓地学呢?”
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工厂安排周六晚上让华罗庚作报告。可是,天不作美,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
华罗庚按时来到报告地点,他一下子惊呆了:一个只能容纳一百人的小教室早已挤满了,而且窗台上、过道上也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打着雨伞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周围。此时此刻,华罗庚的眼角湿润了,刹那间,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剑桥、普林斯顿、哈佛、伊利诺伊大学的讲台,但相比之下,都没有今天的情景令他难以忘怀。
这天,华罗庚的报告格外精彩,暴风雨般的掌声阵阵传出。报告作完了,听众还不肯散去。这时,外面的雨更大了。忽然,几个工人走上讲台,把两鬓垂霜的华罗庚抬了起来,一直送到汽车里。
会后,一位技术人员悄悄把陈德泉拉在一边说:“刚才我真替你们捏了一把汗啊!开会以前有人布置说,今天的会到底是体现专家路线还是体现群众路线,要大家当场发表意见。这不明明是要批判你们嘛!想不到华罗庚教授今天讲得这么好,没事了,没事了!”
后来,华罗庚与陈德泉、计雷又在上海炼油厂做了其他几项优选法实验。结果“硅片消洗液”的配方问题、“605降凝剂”的配方试验,都获得了成功。
一天,陈德泉拉着计雷到上海南京路买凉鞋,在大街上遇到了他的中学同学裘履正。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华教授?我正在做个实验,想把仪器零件上的氧化膜去掉,但是无论怎样实验也去不掉,能不能请你们帮助解决一下?”
“可以。”陈德泉便带着他的同学见了华罗庚。华罗庚表示可用优选法试一下。他一共提出了八个实验方法,从中找出一个配方,仅需一分钟时间,就可把仪器零件上的氧化膜去干净。
这段日子,华罗庚的心情很愉快,与工人们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诗中写道: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吾爱吾师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
可是,正当他带领学生们为工厂排忧解难之时,“上面”的人也来“关心”他了。华罗庚和陈德泉、计雷被迫离开和平饭店,迁到警卫森严的延安饭店,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最后,还是刘西尧为他们解了围。刘西尧来上海后,考察了华罗庚工作过的地方,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以有病为理由,让上海方面同意华罗庚回 京治病。这样,华罗庚才得以脱身。
刚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研究人员便找上门来,告诉他说,他们正在研制一种新材料———液晶,要从100多种原材料中挑出3种,他们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做了很久,怎么也做不完,想请华罗庚帮忙。
华罗庚听后,笑着说:“如果用排列组合的办法做下去,不但你们做不完,恐怕你们的儿子、孙子也做不完。”
他看了所有实验数据,与陈德泉、计雷一起,用优选法进行试验,结果只用了四个星期便找出了最优方案。
改革开放之后,华罗庚在伯明翰大学讲学时,举了这一例子。英国数学家当场提出,让华罗庚派两个学生帮助他们搞液晶,所有费用从优。
1972年5月7日,叶剑英约见华罗庚,叶帅鼓励华罗庚说:“推广‘双法’是一件大事。一个科学家,团结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对生产起这样大的作用,我替人民谢谢你!”叶老还希望他,在普及“双法”时注意一下军事工业中的问题。叶老还特别叮咛他要注意身体,每天少工作一个小时。
此后,华罗庚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普及“双法”小分队,成员除陈德泉、计雷外,还有李之杰、那吉生、裴定一、徐伟宣、徐新红等,这些人也都是他的学生。华罗庚分批分组地把小分队派往全国各地,深入一些主要部门推广“双法”,解决各类疑难问题。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因推行“双法”而创造的一个个经济奇迹,也从四面八方传到北京:在山东,交通运输部 门采用优选法,一个月节 油69.3万升;
在解放军某部,优选法推广半年,便节油2000多万升;
在全国17个省的粮油部门,用优选法节约了5000万斤粮食和500万斤油脂;
在沙市棉织印染厂,“双法”提高了产品质量,一等品从16%上升到43%;在大庆,两个月间,工人们的上千项优选法试验都取得了成绩。
大庆油田聘请华罗庚担任了科学技术顾问。当他接过用红绸子包着的聘书时,心情格外激动,兴奋地说:“这是我时刻向英雄的大庆人学习的学生证。”
那天晚上,华罗庚夜不能寐,便摊开纸笔,抒发情怀:
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
阴湿覆盖下,养成豆芽菜。娇嫩盘中珍,聊供朵颐快。如或落大地,再润日光晒。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春播一斛种,秋收千百袋。
4.暗箭难防
在“文革”期间,华罗庚遇到了一件很少愿意提起的伤心事,即女儿华顺一家深遭江青迫害的辛酸经历。
华顺的丈夫王敬先,原在中央警卫局工作,“文革”前调往苏州任中共苏州地委副书记。王敬先曾和江青在一个支部待过,对江青的情况了如指掌。再加上王敬先曾说过“江青根本不懂马列,只会喊几句革命口号”的话,江青便十分嫉恨他。“文革”开始不久,江青伙同叶群对王敬先下了毒手。王敬先被迫害致死之后,华顺也一直身陷囹圄,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后来,江青曾几次想接近华罗庚,均未达到目的。据胡伯寿与包谦六回忆说,1972年前后,华罗庚得到的中央文艺晚会的入场券,有两次都是与江青挨座。 第一次,华罗庚偷偷与人换了票,第二次是在江青进入会场的一刹那间,利用灯光转暗的机会,他溜到一边去了。华罗庚心里明白,如果大庭广众之下跟江青坐在一起,不仅有辱自己的人格,而且很可能给江青留下什么置他于死地的借口。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江青等人也决不善罢甘休。
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陈景润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而后,陈景润因有结核病,被安排住进了疗养院。
在陈景润住院前,迟群奉江青之密令,曾去中关村88楼陈景润的住处拜访过陈景润。陈景润当时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锅炉房里(并未安装锅炉,但是按锅炉房设计的),两人谈话的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在科学院影响很大:迟群这样的大“左”派怎么会想起拜访一个书呆子呢?不少人心存疑惑。
在陈景润住院期间,迟群更是关怀备至,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一天,陈景润偷偷对陈德泉说,迟群找他的目的是让他站出来揭发华教授盗窃了自己的成果。
陈德泉被吓蒙了,忙问道:“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偷你的成果?”“没有,但他非让我‘揭发’。我该怎么办?”“那你就实事求是嘛!”陈德泉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罗庚。华罗庚一听火冒三丈,他立刻明白了,迟群的后面有江青在撑着腰,江青还是想整他。可惜,迟群从陈景润身上并没得到什么“口供”,这位看起来呆头呆脑的科学家,政治头脑却十分清醒,不管对方如何诱供,他绝不上套。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我怎么能加害华老师呢?古人都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难道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吗?江青一伙抓不住迫害华罗庚的直接证据,便指派科学院的一些“造反派”头目,千方百计阻挠华罗庚的工作。
有一次,华罗庚等人在广西、山西普及“双法”之后,应陕西省的邀请,来到了西部 地区。这时,科学院派来监视他的人也到了西安,来者是一位年轻女性。
“你的小分队没有党的领导,要回北京去整顿。”她口气很大地说。
“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所在省的省委领导下进行的,怎么说没有党的领导呢?”华罗庚毫不相让。“你们不抓阶级斗争,只知道游山玩水,这错误还小吗?”
“随你怎么说都行,我们并不在乎你!”华罗庚也毫不客气。
华罗庚等人无论到哪里开展工作,这位“革命干将”
都紧跟着。两人常常见面就吵,针锋相对。
有一次,她又想教育华罗庚了,华罗庚问她:“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60岁。”
“我比他还大5岁呢!”说完,便扬长而去。1975年6月,华罗庚与小分队虽已收到四川省的邀请信,但被强行调回北京。回京后,华罗庚表示,他服从组织命令,但保留个人意见。科学院把小分队的成员组织起来学习,让他们批判华罗庚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与华罗庚划清界限。这时,小分队不能出去了,华罗庚便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了四川省。当他看到“双法”工作已在“天府之国”产生了极好的效益时,心情极为激动。可是,当他回 到北京后,小分队的人都不敢见他,但大家又觉得对不起华老师。当陈德泉出面,向华罗庚作解释时,他痛苦地表示,他早就预料到,有人会强迫他们与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限的。
一天,科学院的一个小头目来到华罗庚办公室找他谈话。不料,此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方法,外国有人说它对,中国人就跟着说对,而你为什么能看出它的毛病呢?”
一听这话,华罗庚便顺手写下四句唐代卢纶的名诗: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这20个字有错没有?”华罗庚问道。“没错,这是唐诗,我念过。”对方回答着。“是啊,这首诗传了这么多年,没有人说过它错,可是,塞外下大雪的时候,还会有大雁在飞吗?现在我不是看出毛病了吗?更何况复杂的数学问题,又怎能没有错呢!”
说完,华罗庚又写下了自己改过的诗句:
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
华罗庚改过的诗,令对方称赞不已,后来,他的这首诗在科学界广为流传,被人们传为美谈。
5.慷慨掷此身
1975年9月,华罗庚应黑龙江省的邀请,前往普及“双法”。在此之前,吴筱元力劝华罗庚以身体、安全为重,不要到处跑,可华罗庚哪里听得进去呢?
这次他所率领的小分队,人数远赶不上以前了,但华罗庚仍以“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来鼓励大家。出发之前,科学院的有关人士又派出了两个监视者,插在小分队里。
火车载着他们越过松辽平原,进入了神秘的大兴安岭。火红的枫树林、银白色的桦树林、青翠的红松林,使华罗庚忘却了都市生活的繁扰。伐木工人那高昂的号子声更令他神情激荡,热血沸腾。他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如何以统筹法和优选法来解决“采”、“运”、“用”、“育”的问题,连深山老林里的守林人也用心地跟他学“双法”。
连日的劳累与生活的艰苦,使华罗庚深感力不从心,刚回到哈尔滨他便病倒了。
一天晚上,队员们都去看电影了,华罗庚独自留在招待所里。他突然觉得极不舒服,躺在床上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他无力叫喊,只是拼命地用脚踢打铁床沿。
招待所里的一位服务员听到响声,便推开房门,只见华罗庚脸色苍白,嘴唇发紫,一头冷汗。服务员吓得哭了起来,立即找来了医生。“是心肌梗死。”医生说。“能不能送到医院?”“不能动,一动就有危险,等缓过来再说。”这时,科学院的一位副秘书长也赶来了。病情有所缓解的华罗庚拉着副秘书长的手说:“请您转告党中央,我———毛主席交给我的事,没有做好就病倒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他的话使很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事后,北京的心脏病专家被请到了哈尔滨,华罗庚的朋友黄宛及长子华俊东、儿媳柯小英、长孙华云,接到病危通知后,也连夜赶来了。他们把华罗庚送进了医院治疗。
在治疗期间,医生特别关照,要谢绝一切探视。当大庆的工人和劳动模范以及大连机车车辆厂的代表远道而来,要求探访时,医生们拦住了他们,他们站在医院的走廊上掩面啜泣,久久不肯离去。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下,华罗庚渐渐转危为安了。在病床上,他思绪翻涌,挥笔写下了《病中斗》一词:我身若蒲柳,难经九秋风。打击不算大,狼狈如转蓬。几为仇者快,几为亲者痛。
幸赖群众力,始能顶妖凶。
华罗庚在医院住了40多天,虽然医生准许出院了,但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可他的脑子里所想的仍然是他那放不下的工作与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出院之际,他写下了一首热烈深沉、激昂慷慨的诗: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志千里,翱翔太空意凌云,一心为人民。
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鹰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