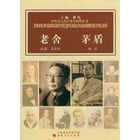一九三三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断了。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关系很密切,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在日本留学,原来想去读四年书,后来不到两年就回来了。一个原因是张允和怀孕了,要回来生育。另一个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当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要考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那么,我到日本就变成读日文了,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张允和在日本是学日本的文学,她对日本文学蛮喜欢。当时日本有名的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受外国的文化的影响,最早是通过日本,中国从日本学西洋。
日本的大学,学生都住在校外,没有学生宿合的。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国青年会,后来我们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里面去。日本许多人家有一间房间租出去给人家,特别是喜欢租给大学生,这样子我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语就进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讲日语,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
张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国,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上海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回来生了孩子,我还在日本,第二年就回来。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日本,他们叫我不用回来,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现在叫京都大学,规模很大,校园很好。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园是日本格式,而且有点宫廷的味道,跟圣约翰大学完全不一样。京都在当时比东京好玩,那时候日本所有大学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很高兴。我起初以为京都讲话跟东京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跟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好玩,很快就学会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东都很好。
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人的生活。还好,可以说在日本留学并没有落空,日语学好了很有用处,解放后回来想搞经济,这个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的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解放后又有那么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这些都是原来想不到的。
十四抗日战争
从日本回到上海家里,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去跳舞,上海有一个百老汇跳舞场在静安寺。跳舞的朋友有邹韬奋、刘凤生,刘凤生是张允和的姑父,有四五个人,有时还带夫人,邹韬奋的夫人不去跳舞。那个地方有舞女,可以请舞女陪跳,在当时是高级的跳舞地方,门票是两个银元,一个银元可以吃两个月的饭。我们星期六去跳舞,那是高级职员的生活,不是资本家的生活。
抗战之前,国民党做了一些经济改革。举个例子,上海人喜欢吃广柑,四川的广柑到上海,一路要收税,运到上海的价钱,成本比美国运来的贵。一路收税,叫作“厘金”,经过一个地方要收百分之一的税。这种税从太平天国开始,是损害交流,损害经济的。不仅长江有“厘金”,许多交通线都有“厘金”,要改变“厘金”很不容易的,影响当地的财政。蒋介石来了,就把厘金制度去掉,作为改革经济的项目之一。“厘金”去掉以后,上海贸易就发达起来了。国民党跟共产党不同,国民党亲美,共产党亲苏。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亲美的。苏联要打倒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统治世界。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来讲,最近有些话改变过来,譬如帝国主义,西欧的帝国主义英国、法国等就主张把中国瓜分,美国主张门户开放,门户开放也可以说是来剥削中国的,但是门户开放中国就不会被瓜分了。
抗战之前的中国一步一步现代化。民主改革,越改革要求越高,要求远远超过改革的速度,所以当时反对政府的声浪还是很高的。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很高,国民党当时是做不到的。同时,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宣传是不惜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宣传部的。后来知道许多宣传都是假的。最近好多文章开始讲老实话。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中国呢?日本人再不打中国,中国就起来了。日本要在国民党羽翼未丰的时候来打,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打下来了,共产党起来了,他们还是下来了。共产党能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左”倾,“五四”以后人们思想越来越“左”倾,日本人打仗,国民党经济就困难了。通货膨胀后,国民党的军队兵无斗志,日本投降了,国民党的军队觉得还打什么仗啊?中国人还打中国人啊?苏联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中国的军火库在东北。日本的东北部队向苏联投降,军火库交给苏联。东北的重武器苏联拿去了,轻武器他们不要,给了共产党。
日本打中国以后,局面就大大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人非常好,军阀政府跟人民完全不一样。
在日本,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轻,交际就是跟同学、朋友,那时候日本人跟中国人做朋友,来来往往跟一个国家一样。中国人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东北日本人更多。打仗了,就把他们赶走了,几千万人都赶走,这对日本也是很大损失。国民党是亲美,美国人跟中国人也是非常友好的,今天变成敌人一样。政府的政策跟群众的要求不一样。
日本侵华的影响非常大,蒋介石大概有四个现代化的师,一个师大概是两万人,是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日本有几十个师,是现代化的,当然敌不过日本了。抗战之初日本打上海,上海是国民党的经济中心,开头日本人打败了,日本在战争局势紧张的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司令,后来大量增兵,蒋介石打败了,他只有两个师就不能再打了,于是退兵。这两个师后来保卫重庆,这样子蒋介石从上海退兵就没有新式军队,只有老式军队是杂牌军改编的,那时候当然打不过日本。日本怕中国起来,中国还没有起来,它就先打你。抗战期间,日本也没有想到打中国那么困难,日本以为打三年能将中国攻下来,没想到打了八年也没有打下来,结果自己失败了。两个大事情改变中国,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友好变成敌对;第二个是共产党,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改变了。
十五从上海到四川
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解放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被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我们一家在重庆时苦得不得了,天天轰炸。有一次我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家里都炸光了,家里人哪里去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为什么住南温泉呢?比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当时日本飞机小,可是一个炸弹把我冲出去,我掉在沟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掉下来就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旁边的人都死了。
跑警报是经常的事情。飞机快来时,就挂起三角球,飞机比较近了,就有另外一个信号,飞机到头上了,就“呜呜呜”。晚上就把灯关掉。有时就要逃到乡下,躲在田里,日本人放荧光弹,亮得不得了,把乡下都照亮了,看到有东西再轰炸。
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这个精神了不起。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蒋介石是重用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打仗的苦难,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东西搞光就搞光,无所谓,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前后连起来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浪费了,不能做学问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抓紧时间来补做学问。
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
有一次,长江有一个地方叫南溪,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的。他告诉我,他那个地方不会来轰炸的,有他可以照顾我的家,当时我一家还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个孩子,我家有我母亲、两个孩子,长江的船往来方便,到那边已经吃晚饭了。吃完饭,人都累得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家被强盗抢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用迷魂药把我们都迷糊住了。我们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顶打开了,强盗弄错了,以为我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我们是逃难的,不可能带有值钱东西,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一路都有强盗的。第二天,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我们的箱子。这一来,就麻烦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