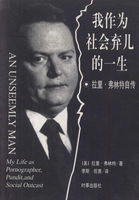研究拼音文字
一九二八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一九三三年从苏联引进的“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林先生的强大共鸣。他认为二者各有不足之处,于是取长补短,设计自己的新方案,创立一个拼音化运动的“中间派”。他的方案称为“简体罗马字”(后来改称“国语拼音”),主要特点是:一、采用“国语罗马字”的基本式,去除烦琐的标调变化;二、规定“定型字”和“定型词”,分化同音词。他说:“我所主张的拼音文字是简化的国语罗马字,也就是改正的中文拉丁化。”一九四二年他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对拼音文字的“正词法”和其中的“同音词”问题,提出了他的新见解,使语文界耳目一新。
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得到如下的认识:一、拼音文字不能寄生在汉字上,应当撇开汉字,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二、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除用声音不同的同义词以及用复音词代替单音同音词以外,需要采取“定型化”方法,对常用的同音词规定“特别写法”。他用“简体罗马字”译写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穷儿苦狗记》,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定型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定型化”指的是“正词法”的标准化,主要是其中“分词连写法”的标准化。狭义的“定型化”指的是一般拼写规则以外的“特定写法”。林先生的“定型化”属于后者。
他变化一部分音节的基本拼法,作为“通盘解决”同音词的方法。他用“变体”“方音”和“符号标调”三种方式,规定了二百四十四种音节的“特别写法”,使四百四十二个汉字所构成的许多同音词都有各自的“特别写法”(后来减少为四十二个“定型字”分化许多同音词)。
一九四四年,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他的《连写·定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和《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两部著作中。他的定型化试验遇到的困难是,“特别写法”只能分化“视觉”的同音词,不能分化“听觉”的同音词,同音仍旧是同音,而“特别写法”的“任意性”使他的拼音文字接近于“汉字化”,难于为其他人所接受。
编写历史故事和提倡成语通俗化
林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
他又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举两得,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
林先生曾对我说:“我一口宁波话,按照我的宁波官话来写,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一位历史学者批评说,林先生费了很大的劲,这对历史学有什么贡献呢?但是,这不是对历史学的贡献,这是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二十四史》有几个人能阅读呢?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越来越了解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又臆造过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群众十分需要的珍贵的读物。
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这样的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实在太少了。
在编写历史故事中,他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都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都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呢?林先生认为是可以的。
他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在《文字改革》杂志上连续发表《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话里“生动活泼、明白清楚”的说法,代替生僻难懂的文言成语。他说:“有些成语,文言里有,普通话里也有类似的话。例如‘赴汤蹈火’,普通话中就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说得更形象化些;有‘上刀山下火海也干’,意思跟‘赴汤蹈火’完全一样。”又如“罄竹难书”,群众的语言中就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意思完全相同。他认为,“普通话比文言好懂,表现充分,生命力强,在群众嘴里有根”。下面再举几个他提出的“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的例子:
“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分崩离析”——四分五裂。
“胸有成竹”——心里有底。
“越俎代庖”——包办代替。
“不辨菽麦”——五谷不分。
“居心叵测”——存心不良。
“暴殄天物”——糟蹋财物。
“不容置喙”——不让插嘴。
“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如火如荼”——热火朝天。
“蜚短流长”——搬弄是非。
“忐忑不安”——心神不定。
“暴虎冯河”——有勇无谋。
“霄壤之别”——天差地远。
他对“成语通俗化”的研究非常认真。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他和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在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文言成语的通俗化。他对我说:把“揠(yà)苗助长”改为“拔苗助长”,虽然只是修改一个字,可是就能使这个成语容易为大众理解了。他多次说过,在白话文中夹用不必要的文言,不能表示知识高雅,只能表示思想落后于时代。
为了语文教育大众化,他尝试翻译中学课本中的文言文为白话文。例如《文字改革》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八期刊登的他的译文《爱莲说》。他提倡大量翻译古代名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做得很不够的一个方面。把文言翻译成为白话,便于读者从白话自学文言,更深刻地了解文言,有利于使文言名著传之久远,同时也推广了口语化的白话文。
林先生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教育家。他一时一刻也不忘记人民大众的教育需要和学习困难。
姜椿芳:《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人
姜椿芳先生是一位“厚今”而“不薄古”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很大。他了解新事物、提倡新事物,同时又了解古文化、提倡古文化。下面谈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两件小事。
大百科全书和拼音序列
“十年动乱”结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候,有一天姜椿芳先生同倪海曙先生来到我家。我问姜先生,您是否仍旧去主持编译局?他摇摇头说:“不去了,想做点别的工作。”倪先生说:“他想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此我们来同你商量。”我对姜先生说:“中国没有一部现代的百科全书,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提倡,但是只说不做;五十年代一度热了起来,后来又冷了下去;这件事如果由您来登高一呼,就有实现可能。”倪先生也对他说:“的确,这件事由您来主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姜椿芳先生的工作特点是: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七十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一九八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接着,姜椿芳先生到美国,跟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约,编译出版中文的简明版,由刘尊棋先生主持,钱伟长先生和我参加“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徐慰曾先生负责具体编译工作。姜和刘二位都认为中文译作“大英”不妥,可以改按音译为“不列颠”。经过五年努力,动员了五百位教授和专家,全书十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一九八六年出齐。这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条目序列方法,姜椿芳先生煞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对百科全书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来说,正文中条目的序列方法是一个关系到检索效率的大问题。传统办法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列,这在卷数不多的辞书中已经证明检索不便,在卷数很多的百科全书中将是十分不便。倪先生和我建议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采用所谓“音序法”。姜先生说,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法”虽有百利,也有一弊,就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不懂拼音,而且社会上有一种惰性心理:宁取不方便的旧方法,也不取方便的新方法。因此,采用“音序法”还得慎重。经过多次跟不同专业者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最后,姜先生得到的结论是:音序法的利点大大多于部首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决定采用音序法。这是大型辞书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创举。中国大陆每年入学的小学生有二千几百万人,他们都学拼音,音序法无疑是前进的方向。《辞海》采用部首法,可是很多使用者说,先查附录中的音序索引,速度可以提高三倍。音序法有两种。一种是纯字母排列法,不照顾汉字。另一种是“字母、汉字、字母”排列法,把条头汉字相同条文排在一起。为了照顾习惯,姜先生决定采用后一排列法,以便逐步前进,不致脱离群众。这是姜椿芳先生“厚今”“革新”,而又保证成功的革命技术。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上都有拼音,作为序列的标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正文条目也用音序法排列,可是排印时候删去了条目上注的拼音。这样做可以节省篇幅和排字工作,可是检索稍有不便。台湾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正文中以英文为条目。英文的纯字母排列法对检索来说是最方便的,可是英文水平稍差的读者用英文条目是不便的,英文水平较高的读者又可能宁愿查英文版而不查中文版。在这里,中文遇到了检索技术现代化的问题。辞书序列方法的革新对中文来说是“信息化”的一个关键。姜椿芳先生毅然走“信息化”的“厚今”道路,在出版史上是一件有开创意义的“小事”。
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
姜先生到我家,一向没有同我的老伴张允和谈过天。有一天,我告诉姜先生,她爱好昆曲。姜先生坐下来对她说:“噢,昆曲。那你认识不认识顾传玠,传字辈挂头牌的?”张允和笑了:“怎么不认识,顾传玠是我的大姐夫。您怎么认识他的?”姜先生说:“我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还到顾家吃过饭。那时我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
姜先生提倡昆曲,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昆曲研究会”成立,姜先生以副会长主持成立大会。在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允和建议要纪念汤显祖,会后写了一封信给姜先生,信中说:“今年是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汤和莎士比亚同在一六一六年去世,汤老比莎翁大十四岁。莎翁七月去世,汤老九月去世,今年秋天开一次纪念汤老的纪念会最好。纪念莎翁有二十四个剧团演出七十多场莎翁戏剧,还演了昆曲的莎剧。可是对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过了几天,姜先生亲笔复信给张允和,表示同意。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向一边斜,显然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亲笔写信困难了。后来知道,姜先生把张允和的信转到文化部,又转到中央,纪念汤显祖的建议居然得到批准。
研究会的秘书长柳以真先生来到我家说,姜先生决定邀请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来参加大会,请张允和代为打长途电话去邀请。十月十一日张元和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天由张允和同她去拜望姜先生。见面时候姜先生说:“顾传玠不但文戏演得好,对耍翎子也很有功夫。顾传玠说过,他练耍翎子是把下颏放在一个小酒杯里,靠着酒杯边缘转,各种各样地转,翎子自然左右逢源,活跃非凡。”这些话,张元和以前也没有听到顾传玠说过。怪不得顾传玠在《连环计·小宴》中演吕布有特别的翎子功,配合传神的“虎步”,显出了吕布的武将神采。姜先生对昆曲的演技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热爱传统文化之深。这是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事例之一。
姜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有学问、有道德的老革命家,他的高尚风格将永远是后世的模范。
(《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前半篇周有光所写,后半篇张允和所写。)
刘尊棋:《中国日报》的创办人
纽约初见
一天晚上,在纽约,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这时候,“二战”结束不久,纳粹主义的威胁解除了,美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内革命尖锐起来了。纽约生活表面上纸醉金迷,好像忘记了外面世界,但是知识分子都暗暗地忧心忡忡,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美国知识分子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