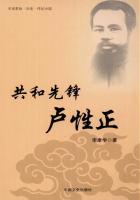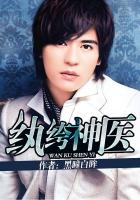王先生是较早重视并参加汉字改革运动的语言学者之一。清末民初,有少数几位语言学者重视并参加了汉字改革运动。例如,劳乃宣提倡“简字”,黎锦熙参加制订“注音字母”,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的原则。但是,汉字改革一向不被看作是语言学的课题。王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写的《汉字改革》的“自序”中说:“汉字的优劣及改革后的结果,都属于语言学的范围。”这句话,奠定了汉字改革的学术地位。
他说:“汉字改革问题,在某一些观点上看来,乃是政治上的问题;我对于政治素来没有兴趣。似乎是不配来参加讨论的。不过,汉字改革的本身虽是一种政策,而汉字的优劣及改革后的结果,都属于语言学的范围。语言学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科学问题去讨论,阐明了改革与不改革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让政治家去讨论它应否实施。”
对于汉字改革,一向有赞成和反对的争论。王先生说,“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加以注意”。这是王先生给汉字改革运动敲的警钟。可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继续犯简单化的毛病,不是简单地赞成,就是简单地反对。
王先生说:“赞成的就说中国人读了几年书还不会应用文字,以至文盲太多,如果改为拼音文字,文盲就可以消灭了,学习新文字只要一两个礼拜就会写会读了。反对的就说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我们不忍中国未亡而文字先亡,所以汉字有保存之必要。这种说法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没有把它的复杂性提示出来。因此大家都觉得事情容易办。其实,只要肯多费心想一想,就会觉得改革与不改革各有利弊,而利弊所关不仅在文字本身。所以这一个被别人说得很容易很简单的问题,一到我的手里便千头万绪,难于应付。我实在也只能做到将问题及具体事实作系统的叙述,注重提出问题而不在具体建议。”
王先生站在“语言学”的立场上来谈汉字改革,使中国的语文问题,从群众运动发展为学术研究,开拓了语文运动的新境界。由此,渐渐有人知道,语文运动不能再满足于简单的宣传,而是要重视科学性和客观性,使运动和学术结合起来。
王先生说:“在本书里,我固然没有替‘存文派’辩护,但也没有替改革派作积极的宣传。因为宣传的口气越多,科学的态度就越不够。凡是宣传,就不免对于不利的事实有所掩饰,同时对于有利的事实有所夸张。掩饰与夸张,都会失了科学的真理。我因为把这问题的政治方面撇开,不当它一种政治看待,自然也用不着掩饰与夸张。素来没有政治兴趣的人来谈汉字改革,其缺点在此,其优点也在此。”
这些话是在五十年前说的。“自序”末尾注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王了一序于桂林”。看了这本书,我感到王先生的改革思想非常崇高、深入、真诚、恳切!可惜五十年来,在一次又一次的语文波涛大起大落中,王先生的话没有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
《汉字改革》是一本袖珍小册子,可是内容丰富,既有改革理论,又有具体方案。
他说,汉字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主要是能超时代和超方言。可是,读懂古书必须研究训诂;方音读书妨害语言统一。缺点主要是难认难写。“当今的急务是把全国的文化水准提高,是在于用最有效的方法把现代文化灌输到每一个国民的脑子里。如果汉字是难学的,哪怕有一百个优点,也为功利派所排斥;如果有另一种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学习,哪怕有一百个缺点,也该为功利派所欢迎。”
谈到汉字与文盲,他说:“人们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太低,就归罪于文盲太多;因为文盲太多,就归罪于汉字的难认难写。其实问题决不会是这样简单的。”在列举文盲众多有许多并非汉字的原因以后,他总结地说:“我们说了以上这一大段的话,无非要给汉字洗刷造成文盲的‘主犯’的罪名,并不想说它连‘从犯’的罪名也没有。”
他认为,汉字改革“有三个很大的难题”:“第一是历代书籍的处置问题”,“第二是语言的选择问题”,“第三是新旧交替的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只简化了部分汉字,改用了拼音字母,没有准备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因此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还没有发生的机会。
关于“汉字改革的可能性”,他认为,“语言文字都是社会的产品,只有社会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们”。
他说:“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的宣传将成为徒劳无功;若不是西洋思想不断地输入,白话文的势力也不会膨胀到现在这种程度。由汉字到拼音文字,比之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更难成功,自然需要比五四时代更大的潮流,然后能促其实现。总之,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的政治思想为后盾,否则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四五十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都是不痛不痒的,这两年来的拉丁化运动竟能掀起颇大的波澜,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我敢断说,将来新字如果有成功的一天,一定是因为某一个政党把它作为政策之一,而这一个政党已经取得政权的时候。”这个“断说”虽然还没有历史机会来加以证明,可是“政治决定改革”的规律,已经为“注音字母”产生于一九一一革命之后和“拼音字母”产生于一九四九革命之后所证实。
王先生着重地说:“不拘任何党派,都能与汉字改革的政策相容”,“语言文字的本身是中性的”。这几个句子都由王先生自己加上“密圈”,表示着重,叫人注意。特别是“语言文字本身是中性的”这句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性”就是“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派性”。这句话跟斯大林所说的“语言没有阶级性”意义相同,而比斯大林早了许多年。可惜的是,在没有平等思想的社会里,学者的诤言没有政客的狂言响亮,而“过早的真理不是真理”。当时没有人了解王先生这句话有万钧之力。
王先生说,“拼音字所引起的问题”有三个:一、方言问题;二、声调问题;三、音标的选择问题。这三个问题,在王先生参加制订并在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里,基本上都解决了。关于“改革的方案”,书中具体地谈论了:一、简体字,二、新形声字,三、唯声字与复音字,四、注音字母与注音汉字,五、自创的拼音字母,六、国语罗马字,七、区际罗马字与文言罗马字,八、中国语写法拉丁化,等等。然后他提出他自己的拟议方案:“类符新字”。他自己说,他“注重提出问题而不在具体建议”,不拘泥于某一方案,后来他也不再谈“类符新字”了。在全书的末尾,他说:“拼音文字如果真的要推行,欲速则不达,与其催产以致婴儿寿命不长,倒不如听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今天,多数人对“拼音文字”的看法是,与其有名而无实,不如无名而有实,这就是王先生“水到渠成”思想的延续。
五十年前王力先生写的《汉字改革》一书,虽然具体情况今天已经变化,可是其中许多论点仍有启发作用和指导价值。
王先生把他的书斋题名为“龙虫并雕斋”。这个斋名包含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我国学者大都重雕龙而轻雕虫,重研究而轻普及,重过去而轻未来。王先生纠正这种重古轻今的传统偏向,正是现代化的思想解放。
(《语文建设》,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事后略作增补)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吕叔湘先生近年来体力和精神慢慢地逐步衰退,最近在医院去世。这像是宇宙中的星星,在光和热经过长期散射之后,终于逐渐衰减而消逝了。我听到叔湘先生的噩耗之后,想起青年时候学到的一句格言:“人生的价值不在寿和富,而在光和热。”
叔湘先生的哥哥,有名的画家吕凤子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是我两位姐姐的老师,所以我认识叔湘先生之前,在幼年就先认识凤子先生。叔湘先生比我大两岁,我跟他是常州中学(当时称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中学时候,我发现叔湘先生能背《诗经》,大为惊奇。这个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时候我就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
一九五五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有机会跟叔湘先生因文改工作而时时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在语文学术上,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在做一件工作之前,把我的想法向他陈述,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把他的意见补充我的设想之不足。我们二人可说是鱼水无间,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上连载,我每期都仔细阅读,作为我的精神食粮。当时,有好多位有名人物都说,中文没有语法,跟英文不同。这种看法,在旧一代文学家中,是很普遍的。《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使文化界的语文认识焕然一新。这不仅是语文知识的补充,也是一次文化的启蒙运动。
我一直注意学习叔湘先生写文章的文风。他的文章,清晰、简练而口语化,完全摆脱了文言的束缚,最值得我学习。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半文半白的新闻体,提倡口语文章化,文章口语化,主张书面语应当跟口头语合而为一,出口成章并不神秘。我认为,中小学的语文课应当就是普通话课。学好普通话就能写好白话文;好文章必须读出来能叫人听得懂,读出来听不懂的不是好文章。这些观点,我曾向叔湘先生在闲谈中陈述,都得到他微笑点头而同意。
叔湘先生有一次发表一篇短文,大意说,好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写文章谈到语文问题,其中有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不知道“语”和“文”的分别,不知道“词”和“字”的分别,更不知道拼音应当分词连写。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没有成为群众的常识,需要在文化人中间进行科普宣传。这是切中时弊的见解。今天我们每天看电视,就看到汉字使用的不规范,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这不能说不是今天我国文化生活的缺点。我们纪念叔湘先生,应当像叔湘先生一样,提倡改正社会用字的不规范,改正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使大众的语文知识水平提高一步。
古人评论人物常用“道德、文章”两事作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学识被语文学界奉为泰斗。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语文学界和一切知识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于人间。
林汉达:大众化的教育家
林汉达先生(一九00—一九七二)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字改革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这里略谈如下几点:一、向传统教育挑战;二、参加扫盲工作;三、研究拼音文字;四、编写历史故事和提倡成语通俗化。
向传统教育挑战
一九四一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强烈的挑战。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育陈规。一种陈规是“照本宣科”:教师只是把自己做学生时候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本《三字经》可以用一千年,这是“轮回教育”,这样的教育阻碍知识的更新。另一种陈规是“模式僵化”:教育方针、学程组织、课本内容、教法实施等,在在都有刻板的规定,不许越雷池一步,教师和学生同样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创造力。
他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熟读唐诗三百首”“填鸭子教育”“铁杵磨成绣花针”等传统教学法。他认为,“兴趣和努力”是不应当分割的,“兴趣生努力,努力生兴趣”。
他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扫除文盲,而这又必须在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之后才有可能。他把“扫盲”“普及教育”“语文改革”“出版事业”“社会发展”,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教育理论,好像是针对着今天的教育实际问题,仍旧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参加扫盲工作
一九五二年,教育部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林先生担任副主任。他满腔热忱、全力以赴,投身于大规模的扫盲工作。这一年,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二千字》。一九五三年,扫盲委员会规定“扫盲标准”:一、干部和工人识两千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百—三百字的应用短文;二、农民识一千常用字(后来增加为一千五百),大体上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不识字或识字数在五百字以下者为文盲,识五百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扫盲年龄为十四至四十岁,后来改为十二至四十五岁。这些标准到今天基本上还没有多大改变。
林先生进行扫盲,重视师资,亲自培训扫盲教师,亲自编写教材,从小学里抽调优秀教师担任扫盲教师。可是,正在他埋头工作的时候,形势大变。军队里冒出一种“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用冲刺式的突击方法,在极短时间内,识字几千,一时传为“奇迹”。于是,停止了扫盲教师的培训工作,把正在培训的教师下放农村,不许回归原校。这件事,林先生不以为然,但是力争无效。林先生曾对我说,这是他后来在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军队里试验成功的速成识字法,向农村推广的时候,完全失败了。不久,“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被人遗忘了。林先生也离开了扫盲工作,但是他始终认为扫盲是个重要问题,继续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