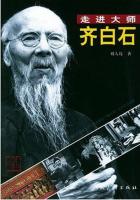黄清跟九吉喝了一通豪酒,摇摇晃晃离开村庄。那时候太阳已经西斜,放学回家的孩子赶着铁圈子走。黄清看见有人围在地头打架,他走上去发一声喝,孩子走兽一般哗然散开。地上坐着一个孩子,衣服被撕裂了,嘴边溢着血,眼睛闪着泪光。“阿牛,你怎么啦?”黄清蹲下身子,孩子看着黄清撇了撇嘴角,可他还是没有哭出来。孩子的身旁只有一杆钩子,铁圈子被人抢走了。黄清放下箱子把孩子扶了起来。孩子的泪水终于还是滴在他的手上。黄清对跑开不远的伙伴大声喝道:“给我站住!你们给我站住!”孩子们被他的凶相镇住了,他们撒不开腿脚,木木等黄清走近。黄清要还铁圈子,指着他们吓唬道:“再看见你们欺负阿牛,我打断你们的狗腿!”孩子们等黄清走近阿牛,突然飞鸟一样跑了。他们边跑边喊:“阿牛爹来了!阿牛爹来了!”阿牛呆呆地看着黄清,他在黄清递给他铁圈子的时候,身子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黄清拍打他身上的尘土:“回去别跟你妈说,省得她操心。你是男子汉,要多为你妈着想,知道吗?”孩子还是没有作声。黄清站着看孩子走开,他突然心里一动又把孩子叫住了:“我这里有点钱,送给你买书好吗?”孩子看了看黄清手里的钱,伸手一推背起书包走了。
黄清在路旁的甘蔗地里撒尿,右眼突然跳得厉害。左眼跳吉,右眼跳灾,不是个好兆头。黄清用手沾上一滴口水抹在眼皮上,口里默念着消灾口诀又上路了。突然,一辆自行车从斜坡上冲下来,黄清和车主都看到对方了,都想躲开对方的路线,结果跳来跳去撞个正着。药箱子从黄清的手中飞去,车上的人也摔了个嘴啃地。黄清从地上爬起来,待要开口骂人,突然“哎呀”一声叫起来:“小高师傅,是你呀!”嘴上吃土的人啐了一口土,身子还是坐在地面上。自行车前轮子朝天飞转,后轮子落下几箱铁盒子。小高慢慢站起来,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你这个猪清,你……你的眼睛是不是塞了猪屎?”黄清连声赔罪,小高扶起车子说:“拷贝箱摔坏了,不知影带子放不放得出来。”小高是镇电影队的放映员,黄清掏出烟递上,点火后问他:“今晚演什么片?好看吗?”小高嘴里吸着烟,双腿夹着前轮,边摆正车把子,边含糊不清地说:“战斗片,爱情片,你们爱看哪片,我放哪片。”黄清说:“我刚才眼皮子直跳,这么快你帮我解了灾,我该谢你撞我呢!”小高虎着眼睛说:“我撞你?!”黄清笑说:“不是你撞我,是我撞你。”小高说:“那还差不多。”
晚上月亮在云层里出没,弯弯的身子像一只波浪中的小船。土场前面坐满着人,后面也站着人,白幕布上剧情正浓。人影通过高音喇叭吆喝打杀,他们揪住观众的心。可是有两个人好像处在剧情之外,他们从人群里走出来,慢慢绕过亮着煤油灯的小摊前,走到悬挂的白幕布的背面。他们坐在幕背看电影,图像的左边变成了右边,看上去怪怪的。看了一会儿,离开人群消失在黑暗之中。他们伏在一处沟渠下边,让身子隐蔽在杂草中,让眼睛渐渐适应无边的黑暗。月光时隐时现,远处的喇叭还在响着,道路上不时传来走路声。“阿信,我们到底要等多久?”阿信像一只卧地的狼,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灵光。他没有回答伙伴的问话,只用胳臂撞了他一下,同伴便不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从沟渠里跃出身子,猫着腰向前直蹿,到了甘蔗地又隐藏下来。“你刚才看电影,片子里的人都是这样夜行的。”阿信开始说话,他显得沉着老练,随手折甘蔗分与同伴吃。他们在黑暗中“咔嚓”、“咔嚓”咬着甘蔗,咝咝地吸着甜汁,竖着耳朵听风声。突然,阿信“嘘”的一声:“你听,有人来了!好戏上演啦!”
甘蔗地里果然来了人,接着又来了一个人。阿信的同伴是八弟,他认出那是一男一女。他们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直走进甘蔗地的深处。甘蔗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可是茂盛的叶子还是把人掩蔽了。阿信和八弟慢慢靠上前去,他们卧着身子,不远处传来了笑声。那笑声黏糊压抑扰人。八弟听见笑声无端地喘得厉害,阿信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人喘你也喘,你喘个屁!你的声音会吓跑人了!”八弟挣扎着小声叫:“你也喘呀,你喘得比我还大声呢!”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两个人都喘不过来。他们听到了声音,男人的呼声和女人的叫声,他们听得入了戏,各自停止了呼吸。阿信突然一跃而起,大声喊叫:“抓人啦!快来抓人啦!”八弟毫不含糊,他冲上前去,揪住地上的人打了起来。
甘蔗地里一片混乱。队长和牛贩子阿万出现在地头时,地里跑出一个影儿。阿万朝着人影儿大骂,追上去用石块砸,被队长拉住了。老实人阿万被怒火烧得哇哇叫着,他冲进甘蔗地的深处,甘蔗地里发出更大声的惨叫。队长过了许久才走进去,他用电筒照着地上说:“好了,让他穿上衣服,给我带到队部来。”可是地上的人动不了,那人脸上流着血,弓着身子用手捂住下腹,两只脚不停地抽搐着。电光移到阿信的身上,阿信没有动;队长把电光移到他脸上,阿信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阿信号啕大哭跑开,疯了的阿信跑开时,居然把队长撞倒了……
牛贩子阿万也离开了现场。那时候电影正好散场,村道上走满了人,他们听到牛贩子趔趄着走在道路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阿万,你怎么啦?是不是家里着火了?”牛贩子不理他们的问话,急急地往家里赶去。牛贩子到家时,孙子阿牛正在摇门喊人。牛贩子问:“阿牛,你妈回来了吗?”阿牛说:“她先回来了,这会儿恐怕睡死了。”牛贩子开了门,家里没有儿媳妇。牛贩子问床上的病婆子,病婆子什么都不知道。牛贩子呆住了。
“我家媳妇不见了!”
牛贩子阿万找到队部,队长和八弟两人正在吃夜宵,他们同时抬起头,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们跟着牛贩子在村里找,哪里还有阿兰的影子。队长打着电筒在水塘里晃,往黑咕隆咚的井里照,没有看到一点踪影。八弟说:“我们到出事的地方看去。”三个人往甘蔗地走去,可那里也没有人,地上躺着的人走了,甘蔗叶片上沾着血迹。“不好,要出大事了!”八弟说。这时候,牛贩子阿万全身抖得厉害,他突然蹲在地上,牛一样地号啕大哭起来:“你们害了她呀,她这会儿是想不开!如果她有个长短,你们得给我负责……”队长说:“你瞎嚷嚷做什么?她一时性子拗不过,躲起来也是有的。”阿万说:“她能躲到哪里去?我儿媳妇是苦命的人,家里如果没有了她,我们可怎么活呀?”
那时候夜已深了,星星在高处闪耀着冷冷的光。牛贩子的身子还是抖得厉害,他的头脑一片空白,他跟在队长和八弟的后面,双脚不停地打着摆子。他抬头看了看夜空,一颗流星从星际间脱轨,在天上划一条白线,落在南方的湖耿湾上。牛贩子突然想到海边看去。他们跑到海边,在礁石边呼唤着阿兰,听海潮在滩边轻轻地拍打着。这时候,风中传来男人的哭声,他们循着声音寻去,一个人影从不远处走来,他的怀里抱着一个人,木呆呆地向前走着。
“阿信!她怎么啦?”
阿信没有听进他们的声音,他在手电光下浑身淌着水,哇哇地哭着。阿兰躺在阿信的怀抱里,她的长发在夜风中像网一样撒开。牛贩子阿万冲上前去,可在碰到阿兰的瞬间停住了。他看到阿兰的手吊在光棍的脖子上,昏迷的女人全身湿透,始终保持她最后的姿势,看上去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似的……
牛贩子阿万养一圈子牛,他做牛的买卖,小牛养了一两年,就牵着它到集镇上卖。碰到牙口好的牛仔,他就买回来养,这样买来卖去,就是他的营生。自从那次事件之后,他成了队长的上客,常被队长请去吃喝,喝得摇摇晃晃而回。队长用人之长,叫他帮队里买牛仔,他就买了两头回来;队长信任他,让他处理一头老牛。那头牛太老了,耕不了地,身体松松垮垮,队长说宰掉分肉吃。牛贩子阿万不同意。他说老牛耕田一辈子,不能宰它吃!队长说,你不吃牛肉,也不让我们吃呀?牛贩子阿万说,我帮你把它卖了。牛贩子阿万牵着牛到了集镇,他一连去了三天,三天都把牛牵了回来:“这头牛太老,没人要呀!”
“那你不会卖给宰牛的?你不让我们宰它,卖给别人你看不见。”
“我看得见的,队长。”牛贩子阿万说,“杀牛的人走过来,我马上就知道。”
“你这个人也真是的!”队长不耐烦地挥挥手,让阿万离开那头牛。他私下里交找阿土猴说,卖得掉就卖,卖不掉杀掉它。阿土猴牵着牛离开村子,被阿万拦住了。他们在半路上纠缠不休,最后一起到了队长面前。
“不行!”牛贩子阿万说,“队长你知道,这牛跟人相近,它们十月怀胎,就差不说人话,你怎么下得了手?”
队长大笑起来:“那你说怎么办呀?老牛不会耕田,又不准宰杀,你说——”他指着牛贩子阿万的鼻子说:“这头牛怎么处理?总不至于给它养老吧!”
“是该给它养老,”牛贩子阿万缓缓说道,“它最多再活两年,你不能杀它!”
队长生气了,大声地说:“这个村是我说话算数,还是你说话算数?”
阿万说:“当然是你说话算数。”
队长摊开双手说:“那不就得了,我要杀便杀,你敢不听我的话?”
牛贩子阿万看了看队长说:“我听你的话,可不听你这个话,我说不能杀这头牛!”
“那我要杀它,哼!你有鸟法子!”
牛贩子阿万又看了看队长,突然站起来牵着牛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牵着另一头牛回来。队长一看那头牛,笑着问:“以牛换牛,那要队里贴你多少钱?”
“我一分钱都不要!”牛贩子阿万丢下牛走了。
队长拗不过牛贩子阿万,叫阿土猴把牛牵还给他,对阿万说老牛不杀了,就寄在他家养老算了。牛贩子感激队长,逢人便说队长的好话,他跟队长贴得更近了。队长叫他干什么,他都心领神会,且做起来不打折扣。有一天队长说,这做人呀,明的不怕,最怕暗地里飞刀,风言风语伤人。你可知道,自从那件事情后,村里人在背后没少嚼舌头呀!牛贩子知道队长说什么,对光棍阿信有了忌惮之心。阿信要跟他家套近乎,他不理不睬,且扬言说要打死阿信。两个人关系逐渐恶化,有一次还厮打起来,由队长出面调停了事。
湖耿湾春季大雾弥漫,海水退潮的时候,淘沙人迅速地分布在海滩上。这是一个很壮观的场面,村里人抬着淘沙槽,槽里搁着必要的工具,肩上扛着铁铲子,成群结队到海边淘沙去。在村庄百年历史上,淘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收入,也是除了产盐之外,第二个非农收入。队长从当初打击产盐中醒悟过来,他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允许村民开采铁沙子。他叫飞歌制作那种淘沙机器,可这种机器太难做了,且不适宜在湿地开采沙子。他躺在床铺上叫人把洪丹招来,微眯着眼睛问了几句话,又让他跟村里人忙去。这时候,理发匠洪丹关起他的发屋,他以非凡的才能当起沙贩子。他的声望回升到当年种蔗的位置。他在炼铁厂和农民之间,架起了一道购销桥梁。他把村民开采的铁沙子收购起来,集中装到船上卖到远方的厂家去。他以当年分发甘蔗款的方式,分发铁沙子的钱款。人们在接钱的时候,看到洪丹的手上闪闪发光,那是一只金戒指,套在他夹着香烟的手指上。
阿信又在淘沙浪潮中,过上他的野地生活。他被洪丹雇佣为一个看夜的人。洪丹在海边大量地收购囤积铁沙子,他和老婆秀娥无论如何照料不来,他便叫阿信来看管。那是一些喧嚣而安静的夜晚,光棍阿信卷着铺盖,睡到海水荡漾的海边去,守着身旁黑乎乎的铁沙子。洪丹找阿信时说:“你是光棍,睡哪里都是一样的,你帮我看紧沙子,我给你票子,你想睡女人还不容易?别像疯狗一样在夜晚游荡。”阿信抬起他发眵的眼睑说:“海边到处都是铁沙子,谁像你洪丹这样守夜?”洪丹说:“他们只有一点沙子,当然不怕被人偷了。”阿信说:“你派我看就不怕被人偷吗?我可是一睡就死的人。”洪丹出手重重地捶在光棍的肩膀上:“阿信你少来这一套!你没有把我的铁沙看好,看我怎么收拾你!”阿信嘻嘻笑说:“我最近手头紧,你给我钱吧,先给我一百元,我给我娘买药去。”
洪丹看了看光棍,从钱夹子里掏钱。阿信看他慢吞吞的样子,干脆出手抢了钱,在沙地上跳着跑了:“哈哈,我有钱了,我有钱了!”秀娥看着男人摇着头说:“疯疯癫癫的人,他哪里可靠呢?”男人说:“你别看他疯癫,他再疯癫也比一条狗好。”洪丹用悠悠的声音看着跑远的光棍说:“况且,谁也拿不准他真疯假疯呢。”
阿信当晚睡到沙地上。海边有一股潮湿的咸涩味道,它们通过风钻到他的鼻腔里,穿透他的身体和五脏六腑。阿信觉得一股骚动的血液正在身体上奔驰,无数的鱼儿在血液里吐着气泡儿。多么难挨的春日呀,阿信翻来覆去,久久不能睡去。他侧着耳朵听海潮的声音,仿佛听到水边有人在呼唤他。那是不久前发生的事,那是一个充满激动和忧伤的夜晚,阿信在海边上救出一个人。那人在齐腰深的海水里站着,既不敢往前走,又没有往后退。阿信听到女人的哭泣,听到涛声中哭泣的声音如歌如诉。阿信扑上去把她救下来。阿信清楚地记得女人被救时,发出揪人心肝的叹息。女人无限依赖地搂住阿信。女人把手吊在他的脖子上,让阿信一步一步地抱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