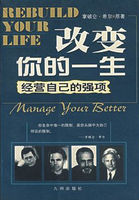全世界都在纪念安徒生诞生二百周年。这就是说,二百年中(不,应该说是一百五十年吧,因为他三十五岁才开始写作童话,五十岁之前可能作品还没有成为经典)他已经用自己的童话征服了世界。我们如果不常看报,不常上网或者读书,比较地孤陋寡闻,可能就不知道丹麦王子和王妃的故事,不知道丹麦这个国家多大,地处何方,有何特产,国民生产总值几何。但是我们肯定知道安徒生,知道美人鱼,知道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皇帝的新衣。一个作家,用自己充满童心和爱心的写作,使他的国家伟大,使“童话”这种文学形式伟大,使语言和文字伟大,我想不出安徒生之外是否还有第二个人。
在我成长和学会阅读的六七十年代,应该说是文学最贫血的岁月。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从哪儿知道安徒生这个名字,如何读到了他的这些童话作品。想起来真是奇怪,那时候全社会都把外国文学作品视为妖魅,藏着掖着也会被人揭发,以至于写检讨、挨批斗,我一个小小城镇上的普通教师的孩子,是如何读到了《海的女儿》和《丑小鸭》?努力回想,依旧茫然。能够解释的只有一点:人类需要审美和想象,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总会有野花不屈不挠地开出,总会有阳光的香味丝丝扣扣散发。
第一次完整地阅读安徒生,已经是文革结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读中文,又是中文系的文学专业,安徒生自然必读。可怜那时候外国文学作品还没有被允许出版,我只能在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去图书馆外国文学阅览室排队抢位。排一个小时,能换到最多四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坐在灯光雪亮的狭小空间里,手中翻着稍不注意就碎的发黄的书页,鼻子里充满了纸张年久生霉的气味,目光机械地、匆匆地、一行行地扫过去,惦念着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多的作品,及至交了书牌,起身出门,人瘫软得成了一团破布,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依稀记得我读到的那本安徒生还是竖排版。不过也许是错觉。人的记忆实在最不可靠。
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文学在中国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文学作品印数最多、销量最大的时代。几乎从女儿满月开始,我就蚂蚁搬家样地从新华书店搬回各种童话的文字本、绘图本、拼音本、缩略本。非常清楚记得的一幕,是女儿睡在床上,我倚在枕上,给她读《海的女儿》。读着读着,她的小嘴巴一扁一扁,晶亮晶亮的泪珠儿就慢慢地涌出来,溢满了眼眶,又噙住不散。那时候女儿不过三四岁。至多三四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为安徒生着迷、伤感和哽咽,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不凡。
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去年还写过一本《中国童话》。每次把自己的作品交到编辑手中时,我很得意,因为我的文字怎么读都是一个顺畅。每次翻开安徒生的作品再对照自己,我又沮丧,明白丹麦的大师的确是一座高山,今生今世要想翻过山去,很难很难。
四十五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买《安徒生童话》,是译林版的精装本。四十八岁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读安徒生童话,是叶君健的译文。不不,不能说“最后”,只能说“最近”,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还会再买再读。我读着,不是在北大时的疯狂吞咽,是饱食之后的反刍,细细的,悠悠的,丝一样绵长和阳光一样温暖的。这样的阅读,是生命中无以企及的享受。
感谢安徒生。有了他,我们才有了童年,有了梦想,有了忧郁、感恩和伤情。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孩子们有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