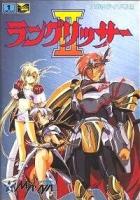宁夏、隆德、联财、张楼,这四个地名连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境界。
张楼是隆德县西南边上的一个村,属联财镇管辖。联财人做事稳稳当当,说话也喜欢带条尾巴,于是,张楼便被他们叫成了张楼儿。
到了张楼儿,我顾名思义到处寻找,始终没能找到可以算作楼的古建筑。
张楼儿三组的人说,张楼儿原来是有座楼,没楼怎么敢叫张楼儿。张楼儿三组的农户差一点全姓张,只一户陈家。这户陈家早先独独住在孤僻的南山根,而南山根有条沟,进了沟,上了大洼山,往下就是甘肃静宁古城管辖之内的挂挂牛湾了。
挂挂牛是蜗牛,许多地方都这么叫。
张姓在中国是大姓,在张楼儿三组就更大了。据说张楼儿在清朝出过一位统帅三军的大总兵,村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指着对面高高的张堡子崖说,那就是见证,坡上的将军墓也是见证。
据他们讲,有一帮盗墓贼在村里打探了许久,又在那座墓前转悠了许久,最后失望地走了。他们终于没下手的原因,说是坟上不见墓碑,也没栽松柏,不是将军墓,倒像将军母亲的或将军其他亲属的墓。
将军当兵走了以后,他母亲孤独无依,只能靠上山砍柴苦度日子。据说寒冬腊月将军的母亲冻死在砍柴的路上,乡邻们就地把她掩埋了。
看来盗墓贼也听说了这位将军母亲的故事。
我本想打听清楚,去看看这座将军或将军母亲的坟墓,但一片寂静令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几位老人用怪异的目光审视着我。
“想看看么?”一位年轻些的老人问。
我忙忙摇头,灿然一笑,表示不用了,然后把话岔开:“听说你们这儿有两座古堡,怎么一座也看不见?”
他们见我不是来打听将军墓,也就把话移到了古堡上。张楼儿不仅有古堡,古堡上还有楼,这古堡正是张总兵回乡后建的宅子。
“不过你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些痕迹,民国9年大地震把楼从墙上掀了下来,堡墙基本上给掀倒了。”
他们见我很失望,又把话拉回来,扯到张学良、张治中上。那位稍显年轻的老人说,北京也有个张楼儿,他年轻时本来想去看看,可农业队打水库,修梯田忙得走不开,现在上了年纪又懒得出门了。
我问了一句:“古堡没了?”
他们集体一愣。
最终还是那位年轻些的老人告诉我,南山根还有座小堡子,是独门独户陈家老人陈文治一个人打的。他不但打了这座堡子,为了灌溉自留地,还在堡子后面的喳沟里打了两座小水库。
我猛一惊。
我从他们口里得知,陈文治老人一个人用背篓背土,打堡子、打水库打了一辈子,打到83岁过世的时候,还有一个堡子角没有完成,是他的后人接着打成的。不过,他的后人在他过世后,就搬出来和村里人住到一块了。
据说喳沟并不大,沟里有股很细的泉水,野鸡、野鸽子和鸟儿们常在这里栖落。中午寂静的时候,老远就能听见它们唧唧喳喳的叫声,这使我的想象活了起来。我告别几位老人,沿着小路向那里走去。
小堡子果然很小,小得简直不可大胆地称其为堡子。它四周种满了各种树木,有的刚开花,有的才生叶,有的歪了头,有的挺直了身。
夹在树中的小堡子,看上去既苍老又萎缩。堡墙夯层并不均匀,土质、颜色也不统一,墙高也不过六米左右。
堡门锁着,门框上贴着迎春的楹联,门板上有一副已经褪色的门神,看来堡子里还是经常有人走动。
我正迟疑,从小道上走来一位扛着铁锹的农村媳妇,她宁静地看着我,从她的眼神中,我知道她就是这座堡子的主人。我告诉她我只想在外面仔细端详一下这座土堡,没有打搅主人的意思。
她讷讷地打个招呼走了。
我围着小堡子转了一圈,转到东边,见有一个生了石锈的碌碌和一面落地的石碾盘。面对这对曾经为生活碾轧过粉末的石具,我迟疑了一会,在迟疑的时候,我听到了两声黄鹂的鸣叫,我记起了那首有关黄鹂与挂挂牛的儿歌。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
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
我没有去看那两座小水库,我已经从挂挂牛身上感知到了这位陈文治老人的愚公精神。我想一个人哼着这首歌慢慢地离去,在离去的路上我发觉世上所有的城堡都像挂挂牛。
堡门深深
五哥,我们住在这座古堡里
你常年背着背篓在院里转悠
你一生只出过两次门
每次刚要出门
风,总是先把门关上
五哥,你第一次出门赶集
把鸡蛋便宜卖了
回来,揣着一双绣花鞋
第二次去赶庙会
走到半道,又回来了
五哥,这堡门不是关老爷的门
不是门,是阴谋
是你的报应
是因为这双绣花鞋的花色太鲜艳吗?
——啊,五哥
我不知何时才能把它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