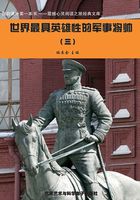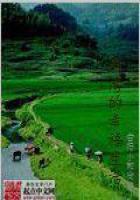一路走来,历程跌宕,然而当祖国需要我们努力探索时,当患者需要我们解除病苦时,我仍责无旁贷,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陈灏珠
陈灏珠,1942年生,广东省新会人。我国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1949年毕业于前国立中正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在研究心血管病的流行病学,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及其诊断和治疗、国人血脂异常、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危重心律失常等方面也作出卓越贡献。历年发表论文 300余篇,主编各类教材、专业书籍数十本,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 2项,部、省级科技和教学成果一等奖 8项。培养研究生 73位,其中部分已成为现在我国心血管病界的领军人物。
88岁高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若身体无恙、合家美满已是人生大幸。
然而,对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陈灏珠院士来说,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情景:在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 7楼的会议室里,坐在我们面前的陈院士有着普通老年人的平和睿智,却毫无耄耋之人的消极与慵懒;有中年人的自信进取,却不见不惑之年的纠结和挣扎;有年轻人的乐观求知,却不似青年人般锋芒而单薄。与陈院士一席谈话,会被他那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深深吸引,会使人重新审视“大医精诚”的意义,更会让人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热爱生活。
坎坷求学路
1924年11月6日,陈灏珠出生于香港。从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到“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日子里,硝烟尚未波及香港,少年陈灏珠在这里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直到 1939年,陈灏珠的母亲因为高血压引发脑卒中去世,这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悲伤之余,细心的陈灏珠发现母亲的疾病似乎根本无法医治,当时的医学水平仅能对高血压患者予以镇静类药物治疗,然而疗效甚微,无力回天。就此,一颗学医的种子在少年陈灏珠的心中埋藏了下来。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成功,发动臭名昭著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东方之珠”香港受战争之累而沦陷。尽管这场横祸发生时,陈灏珠距离高中毕业仅余短短一个学期,然而兵荒马乱之中,年少的陈灏珠也不得不中止学业。当时香港曾为物资周转中心,仓库里贮存了大量的各类物资,沦陷后各种物资特别是粮食等重要物资都被日本军队控制,香港当局限定市民的粮食供应紧张,限令颁布不久,曾经富庶的香港饿殍遍野。陈灏珠的家庭虽千方百计地节约口粮、维持生活,也难免生活每况愈下,陈灏珠的父亲作出一个冒险的决定—逃亡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先逃到尚未沦陷的老家广东省新会县,再到当时广东省临时省会韶关市。逃亡之路艰辛困苦,长途跋山涉水之后,陈灏珠一家终于死里逃生来到了广东省韶关市。这时已经是 1943年的春天,一家人惊魂未定却相拥而泣。
少年陈灏珠随家人在韶关落脚,在一家也是从沿海地区流亡到韶关的中学读完高中课程,等待着进行“高考”。战时的一切事务都处于非常状态,大学的招生也不例外:各个院校在其所在地附近城市自行招生。当时在韶关市招生的有三所高等院校:国立中山大学(现中山大学),国立广西大学(现广西大学)和国立中正医学院(经过数次合并、更名,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三所学校陈灏珠都填报并且都考取了。国立中正医学院是当时第一个发榜的学校,想起母亲得病弥留之际的场景,他立志学医,帮助像母亲一样的病人。一接到通知书,还没等到另外两所大学的榜单,他便收拾行囊北上赴江西入学。“后来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的通知书送到我家,我父亲写信来告诉我,我说我已经在这里扎根了,我决定学医了,做一辈子的医生。”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陈院士的语气仍然充满着坚毅。
“杂交”来上医
青年陈灏珠就读于中正医学院,之所以能结缘上医,这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中山医院一直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主要安排本校的学生进行实习工作,这也是历来的传统。当时的院长沈克非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普通外科教授,同时他对神经外科也很有兴趣,力图将上海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发展壮大;沈克非院长还是一位热心教学、积极培养新一代医学生的教授,他提出了一项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吸收各地优秀的医科学生到中山医院来实习。沈院长认为,医学教育不仅需要传承式的“纯种”,更需要“杂交”,才能博采众长,吸收各个院校教学中的精华,这样一来不仅对于医学生的培养有利,也为各个医学院和医院的思想交流、融合以及人才的培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国立中正医学院院长王子玕教授非常支持沈院长的提议,并且选拔了成绩最优秀的两位医学生赴沪参加实习。“我是来参加‘杂交’的。”陈院士打了个幽默的比方,“虽然说我不能严格意义地算是上医的学生,后来我一直在上医工作,成为上医的校友,也可算是当年沈教授提议的一个成果吧。”
陈灏珠过人的才智让他获得了留院的资格,1949年从医学院毕业后便当上了中山医院的内科住院医师。之所以选择心血管内科作为自己的事业,除了个人兴趣因素,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1950年,上海郊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地,战士们因为训练游泳,导致大规模感染血吸虫病;已经担任内科住院医师的陈灏珠跟随中山医院派遣的医疗队伍前去开展诊疗工作。当时治疗血吸虫病只有依靠静脉注射三价锑剂,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副反应的药物,尤其是会产生心脏毒性反应,因为三价锑剂会损伤心肌而产生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引发晕厥甚至猝死。所以,医疗队队长 —著名心血管疾病专家陶寿淇教授反复叮嘱队员,在使用锑剂时,要注意密切观察心脏功能,防止发生意外。他运用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心电图机为每一位病员作检查以了解心肌受损的情况。基于这次治疗血吸虫的经历,陶教授和他的团队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1956年,陶教授在瑞典召开的欧洲心脏病学会议上作了《用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过程中心脏方面的毒性反应》的学术报告,并于1957年发表在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获得了极高评价。跟随陶教授的这段经历让青年陈灏珠开始对心脏病这一研究方向萌生了兴趣。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青年陈灏珠随“上海市抗美援朝第七大队”赴齐齐哈尔的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参与后方的救治工作。由于大部分战争性创伤都在前方的医院得到救治,陆军第二医院主要负责诊治疑难的病例。陈灏珠被分配到肺科病室工作,发现了一些被误诊为肺结核的肺吸虫病病例。在此期间,他和担任副大队长的陶寿淇教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陶教授谦和的风格和正直的为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要求让他受益匪浅。1953年,陈灏珠被派参与调查山东胶州半岛的一起医疗事故,那是治疗黑热病病人发生的事故。当时使用五价锑静脉注射治疗黑热病,虽然五价锑的心脏毒性没有三价锑那么猛烈,但是,一旦使用剂量超过中毒剂量,也会很快引起心脏类似于三价锑的毒性反应。
陈灏珠一行通过细致周密的调查,澄清了人们对于药物本身质量的怀疑,并指出了基层医院在使用五价锑剂的不够规范之处。至此,青年陈灏珠对于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有了充分的信心,在他 1954年担任主治医师开始就致力于做一名心血管内科医生。“其实我对于内科的其他分支也非常感兴趣,比如血液科啊,疾病千奇百怪,临床症状也很多,治疗方法更是不同于普通的内科,我念书时选修了不少血液科的内容;再比如消化内科,那时候消化科病人最多,最缺医生。可是真正会很快使病人丧命的,就是心血管疾病了,我觉得诊治这些疾病挽救病人的生命就是我要追求的事业。”
恩师陶寿淇可谓是青年陈灏珠在医学道路成长过程中的一位指路人,这位老上医人有着深深的上医的烙印 —严谨、求实并且两袖清风。1964年,中山医院提出要对各科室进行骨干医生培训时,时任科主任的陶寿淇教授找到陈灏珠,两人一拍即合 —陶教授欣赏陈灏珠的才干,陈灏珠也仰慕陶教授的为人、学识与威望,他们很快就制订了培养的方案和一揽子计划。就在一对一培训开始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被迫搁浅。尽管如此,陈灏珠依然非常感激陶寿淇教授对自己的信任和栽培,并且将自己坚定地选择心血管内科作为毕生事业这个决定一大半归功于这位恩师。
行医六十余载
陈灏珠院士在自己的事业上倾注了所有的心血,行医 60多年,他对心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有很深的造诣,其中最耀眼的成就莫过于成为中国心血管病“侵入性诊治法”(现称介入性诊断治疗)奠基人之一。心血管内科,作为内科的一个分支,擅长使用对病人无创伤的方法来诊疗疾病。在陈灏珠院士的恩师陶寿淇教授的年代,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主要依赖两种手段:一是医生的手、口、眼、心、耳,也就是说利用医师所掌握的体格检查的方法结合病史的询问和分析来达到诊断目的,这种方法虽然实用,但依赖经验,且不够直观。二是心电图和心脏 X线检查。前者操作简单,对诊断心律失常有决定性作用,但对心脏病的解剖和病因诊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后者比较直观地显示出心脏的大小,但对心脏内部的解剖变化仍难以作出准确诊断。如果有种方法能够进入心脏内部,看到心脏的解剖和生理变化,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检出率和正确诊断率,对于医生制订治疗方案无疑有巨大裨益。
到了陈灏珠成为主治医师的年代,中山医院的心内科和心胸外科跟随着世界医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医师们经常阅读国外的医学文献资料,学习新的技术,追踪心脏病学的前沿。那是 20世纪 50年代,他们看到国外医学杂志报道“心脏导管检查术”,即把一根导管从周围血管置入心脏内部各心腔,测量其压力和抽血做氧含量检查,以诊断先天性和瓣膜性心脏病。这里面还有一则故事。1929年,德国埃伯斯瓦尔德的一家医院有一位名叫福斯曼的泌尿科医生,他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试图通过周围静脉把一细长的管子放入心脏。当时他所用的管子是泌尿外科用的输尿管导管,他在手术室护士的帮助下切开左肘部的静脉,成功地把输尿管导管送入到心脏,然后他和护士一起到放射科在 X线透视下由护士向输尿管导管注入造影剂,证实导管顶端已到达右心房,并拍下了 X线造影照片,可以说这是人类第一张心脏导管检查的照片。可惜福斯曼医师的这项研究没能继续做下去,因为医院当局认为他所做的试验是危险实验,并认为他可能是个疯子而开除了他。他的创举后来经美国寇尔南特和理查特斯医师继续研究,发展成为规范的右心导管检查术,并于 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开辟了此后数十年内人们对心脏介入诊治研究的先河。
当时中山医院心胸外科的石美鑫教授大受启发,1950—1951年将这项技术运用到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并获得了成功。然而,囿于当时的条件,中山医院开展得不够规范。1957年,医院决定派陈灏珠赴北京协和医院参加“心导管观摩班”,负责培训的老师是刚从国外学习这项技术回国的黄宛教授,陈灏珠在那里借鉴到许多其他医院的经验。从北京回到中山医院后,陈灏珠在恩师陶寿淇教授的支持下建立中山医院心导管室,除了进行大量右心导管检查,他还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染料稀释曲线测定、氢和维生素 C稀释曲线测定、心腔内心电图检查、心脏内心音图检查等。这些“侵入性心内检查”极大地提高了各种先天性心血管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诊断水平,心脏外科直视手术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快速发展。1962年,他总结多年来心脏导管的研究和利用导管进行侵入性检查的经验,编著出版了《心脏插管检查的临床应用》一书,于1980年修订为第二版并改名为《心脏导管术的临床应用》,此书被我国学者誉为是心脏导管技术实用而经典的著作。
然而陈灏珠并没有就此满足,既然可以用心导管来诊断疾病,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治疗疾病造福病人呢?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和同事们继续潜心研究心脏导管在治疗方面的突破。1964年,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一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病人身上,第一次将一根自制的在普通的心脏导管的顶端安装一对用白金制成的电极片的导管电极,通过静脉送入患者的右心室,导管的尾端连接一个也是他们自制的体外起搏器来起搏心脏,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紧接着 1968年,在心内科和心外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为一位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的病人,安置一台永久埋藏式的起搏器,即将整个起搏器装置安放在病人胸大肌深面,开国内之先河,引起极大反响。1978年他们与医疗器械厂合作制成的锂电池埋藏式起搏器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是陈灏珠院士对我国心脏病学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1952年瑞典医学家 Di Guglielmo成功开展了全球首例非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1953年美国医学家 Sones开展了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此后,冠状动脉造影术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但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国医疗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拉大了差距,加之国际社会对中国施行的技术封锁,国内该领域一直鲜有人涉及。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学术交流开始逐渐恢复,一些受邀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学者在学术报告中介绍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等心脏介入技术对冠心病等的诊断作用,这些学术报告引起了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领导的关注,他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上海市有一定基础的医疗单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由于陈灏珠此前一直进行心导管检查方面的工作,上海市卫生局便将开展冠状动脉造影研究的任务交给了他。陈灏珠接下这项沉甸甸的任务后,立即着手组织团队开展研究,他们结合国外文献报道,利用之前数十年积累的心导管诊疗其他心脏疾病的经验,在动物和新鲜尸体上进行了大量实践,初步掌握了冠状动脉造影术的技术要领。“在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当我们学会一样技术,他们又发明了另一种新的技术,我吞不下这口气,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搞出来,发展我们的新技术。”时隔 40年,描述起这段经历时,陈院士仍旧激情澎湃。
忘我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很快有了用武之地。1973年4月23日,一位病人因胸痛住院,经各种检查怀疑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但以当时的技术尚不能确诊。为了明确诊断,陈灏珠决定为病人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尽管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手术方法也已了然于胸,但首次在病人身上实施这种手术还是让陈灏珠有些担心。顶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压力,陈灏珠成功将心导管送入了病人的冠状动脉,注入造影剂后,目标冠状动脉顺利显影,整个手术宣告完成。这一手术开启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目前冠状动脉造影术已成为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凭借造影结果,医师可以清楚地看到冠状动脉的病变,进而可以针对性地对病变冠状动脉予以球囊扩张、放入支架或施行动脉搭桥手术。此后,在陈灏珠等的带领下,国内的心脏病介入诊断和治疗获得了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早期确诊率和治疗生存率。陈灏珠因此也被誉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诊断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心血管内科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院士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坚持”,他回忆当年参加北京协和医院举办的“心导管观摩班”十多位同道中,后来能够接受并坚持将这项技术发展下去的仅有他一个人。他认为只有倾心和坚持投入进去,才能取得成功。“后来许多同道也意识到了心导管术的重大意义,到我院来进修这项技术的也越来越多,而上医是国内第一家在右心导管术的基础上发明和开展这么多心导管诊疗技术的医学院。”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实行对外接触政策,国际交往有所恢复,来华访问的外宾开始增多。国宾和重要外宾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医疗保健工作由外交部指定国际交流组织部门统一协调负责。当时,陈灏珠已经是国内心血管界的知名专家,是外宾保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陈灏珠救治过的外宾中,巴茨博士(Dr。 Paul Basch)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学家,系中美建交后美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华医学代表团—血吸虫病代表团的副团长。1975年 4月 22日上午,在参观位于无锡的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巴茨博士突发胸骨后压榨样疼痛、出汗、面色苍白、手指脚趾麻木,随即被送到该研究所的治疗室。通过心电图检查,证实有急性前壁心肌梗死。陈灏珠接到紧急通知,前往无锡抢救病人。当天下午,陈灏珠和两位上海同事赶到了无锡。上海市和无锡市的卫生行政领导任命陈灏珠为医疗组组长,全面负责抢救工作。陈灏珠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代表团介绍了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提出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 —应用中药丹参加入低分子右旋糖酐中静脉滴注,以促进微循环和灌注受累的心脏组织 —那是他以前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的科研成果,所以他对此很有信心。经过一番波折,美方同意由中国医护人员负责病人的治疗,但由于对中药丹参的药理作用不熟悉,美方婉言拒绝采用丹参治疗。陈灏珠虽感遗憾,但还是尊重美方的意见,放弃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办法。经过一周的 24小时不间断监护治疗后,病人度过了病情最危重的时期,转危为安。又经过两周的治疗和休养,巴茨博士得以痊愈。1976年,美国权威杂志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文献》)对这次救治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该文最后写道:“由于美国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次数增加以及美国人患冠心病的多见,使美国旅行者在中国访问期间难免会发生心肌梗死。我们报道这一事件,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心脏病学家的优良技术状态……”“虽然冠心病和其后发生的心肌梗死直到最近才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心脏病学家们在此病的诊断和治疗的趋向保持与西方并驾齐驱……”一时间,中国上海的陈医生在国际心血管内科界名声大振,中国的心血管疾病诊治水平也让西方国家刮目相看。
陈灏珠不仅在介入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锐意创新,取得了一些国际首创的成果。1976年,陈灏珠所管的床位来了一位患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成功施行了二尖瓣瓣膜分离手术的病人,她手术后发生心房颤动。按常规他们选择术后两周左右给予将心房颤动转复为正常窦性心律的治疗,采用“体外直流电同步电复律”的方法。在应用此种方法的前一天常规给病人口服“奎尼丁”作准备。“奎尼丁”是一种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的药物,可以用来把心房颤动转复为正常窦性心律,但当年它主要用于“电复律”治疗前的准备和治疗后的维持。这位病人在一天的口服“奎尼丁”作“电复律”准备的过程中,她的心律已从心房颤动转复为窦性心律,只需继续服用“奎尼丁”来维持,不需要进行“电复律”了,这样病人和医生都很高兴。不幸的是病人服用第一剂“奎尼丁”维持量后一个小时左右发生“奎尼丁晕厥”。“奎尼丁晕厥”是“奎尼丁”的一种毒副作用,病人发生室性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晕厥和抽搐,这是一种很危急的情况,要尽快终止它的发作,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这位病人在 10小时内反复发生晕厥、抽搐 29次,用各种方法治疗都仅取得暂时的效果,病人生命垂危,陈灏珠和他的同事半步不离病床观察病人情况,经过密切观察终于找出病人对各种药物反应的规律,选出用异丙基肾上腺素静脉滴注来治疗,而且用量越来越大,达到正常剂量的 15倍才将室性心动过速完全控制住,维持用药 6天并逐渐减量,病人最终被救活。当总结这次治疗过程时,查找文献他们才发现,这一方法从未有人用过,属国际首例。这一方法他们在国内推广获得良好效果,还多次在国际会议中作介绍。
“医学不仅仅是一门自然科学,我们研究疾病、研究人体,从大体水平到系统器官,再到组织细胞,现在都发展到了分子水平;它还是一门人文科学,我们研究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病人的,千万不能偏离了这个目的;临床上治病救人,我们的对象始终是完整的个人,而不是一个受体,也不是一块组织。”陈灏珠一直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心血管疾病作为目前患病率最高的疾病,病因涉及范围较广,除了目前已经研究清楚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致病因素外,很多都与患者的遗传背景、生活习惯、承受压力等综合因素有关。时下陈灏珠的心内科特需门诊常常有年轻病人因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等非特异性症状来就诊,往往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方面的检查都显示为正常,“其实这些‘病人’更多的是出现了一些心理和精神障碍,他们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压力、工作负荷等所致的心理和精神障碍‘躯体化’而出现这些主观症状,于是我在工作之余还向心理咨询科的医师学习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帮助这些患者解决问题。”陈灏珠说,不是所有检查结果都阴性就是没有问题了,如果这样去对待病人,仅仅是将病人当作待修理的机器,那么对他们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医生一定要从全局的角度去审查每一个经治的病人,懂得如何常去安慰病人。“一个好的医生,首先要有高超的技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其次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与领导、同事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与病人的关系。”这是陈灏珠行医多年的深切体会。
桃李满天下
陈灏珠不仅自己成就非凡,也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家。他著有多部经典著作,如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专著《实用内科学》、《心脏导管术的临床应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心脏病学》、《实用心脏病学》、《心脏病诊断治疗学》、《心血管病鉴别诊断学》、《心血管病新理论和新技术》、《高血压及相关疾病》、《心脏危重症监护治疗学》等,被国内外学者、医生和医学生奉为“宝典”。如今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担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人民卫生出版社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教材的编写委员会顾问和五年制教材的主审,严格把关教材的质量。陈灏珠认为,著书立说的目的是将自己的看法和所积累经验表达出来,一是取得别人的肯定,二是希望自己的经验和理论能够得到推广,“如果说好的东西不表达出来,而是束之高阁,那就太遗憾了。教学医院除了治病救人,还必须要有教学和科研,即所谓‘医、教、研’。为了医学的继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培养人才,我写这些书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医学这个事业,并且让这些参与的人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最终造福于整个医疗卫生事业。”
从医 60多年,陈灏珠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达 70余位,更不用说陈灏珠所教过的本科生、进修医师的人数,他的学生们遍布世界各地,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为医学事业奋斗:有的在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所研究高精尖的技术,有的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活跃在国内三甲医院的医、教、研一线,有的在西藏、新疆边区从事着医疗支援的工作。
其中让陈灏珠印象最为深刻的研究生之一是姜楞教授,曾经担任中山医院副院长、心内科副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长,将中山医院超声心动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如今她在美国 Tufts大学担任内科学教授、附属马萨诸塞州 Baystate医学中心无创心脏科主任。她能够在国外拥有较高的学术地位,从一个研究者升任正教授,对于一位华人女性而言实属不易,也体现了她在心血管疾病诊治和研究方面的极高造诣。另一位让陈灏珠十分器重的学生是葛均波教授,他于 2011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过去数年来,国际上对冠心病介入再狭窄机制方面存在争议,葛均波通过研究发现,斑块的增生而非血管的挛缩是介入术后再狭窄的主要原因,有关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近来对冠心病的治疗方面正向着缩小残余狭窄的方向努力,也验证了该观点的准确性。最近,葛均波正致力于冠心病病人心肌微循环灌注障碍方面的研究,他对冠状动脉血流缓慢综合征的研究阐述了假性冠状动脉血流储备正常的机制,并受邀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心脏病大会上做专题讲座,是目前在国际心血管界成就卓著的华人。“葛均波是我的一个得意门生,他很年轻就做出了成绩,院士的称号证明了他的成就。”还有一位舒先红教授也让陈灏珠赞叹不已,舒教授继姜楞教授之后担起中山医院超声心动图诊断室主任的工作。她工作兢兢业业并且卓有成就,她不仅在临床中对病人热情和蔼,还在多项科研工作中表现出色:在国内率先或较早开展了多项心脏超声诊断新技术,例如实时三维经胸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心肌应变和应变率显像、经静脉实时心肌声学造影显像、斑点追踪显像等,获得了多项荣誉和国内外心血管内科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当然还有一些在偏远地区坚持医疗工作的人,他们所处的艰苦环境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和佩服!看着我的学生们如今也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我非常欣慰,上医‘心内’后继有人,前途一片光明。”
陈灏珠对上医精神—正谊明道有着深刻的领悟。他在中山医院实习时,上医对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的要求就非常严格:实习医生每天大量重复问病史、检查体格、写病历、抽血、留样本,甚至要完成一些现在由检验科技术员和病室护士完成的职责;而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都被要求 24小时值班,这看来是一种近乎“不人道”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严格管理,才造就了上医一批又一批像陈灏珠这样的优秀人才。“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我们很快就掌握了医院的日常工作模式,我到现在都能流利地作病史汇报,而现在的年轻医师有些还必须看着事先写好的提纲才能完成病史的汇报。所以当今年轻的医学生一定要严格按照上医制定的培养方案来接受训练,这对医学生而言将是终生受益的。”
关于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陈灏珠告诉年轻医师们,首先要相信这个社会必将淡化这些矛盾,重新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其次,从我们自身做起,恪守医德,牢记校训。不管病人知识层次高低,都要与他们进行良好沟通,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沟通是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的第一步,非常重要;不管自己工作有多么繁忙,都不要跟病人发脾气,要真诚地对待他们。这些都是他在 60多年行医生涯中一直贯彻的信条。
“谨记上医老前辈们留给你们的院训,‘正谊明道’,‘严谨求实团结创新’。上海医学院 85年走来,经历风风雨雨,但是最终都一一克服,为祖国人民的健康、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现在我们仍旧面临许多难题,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尤其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团结一致、不断奉献、努力创新,继承上医的优良传统,让上医精神发扬光大,成为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优秀医学院!”在寄语年轻人时,陈灏珠慷慨激昂,语气铿锵,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兵,对事业、对生活、对未来充满着热忱和期待。
(采写:周英杰吕海辰刘佩玺张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