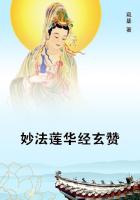“傻子”其实不傻,而是哑,因为整日沉闷无语,不和人交往,人们就把他归入“傻子”之列。
傻子接任队长时,公社驻队干部老郝已经把一面小白旗挂在七斗冲生产队办公室的墙上。
一天前,老郝来七斗冲检查生产,一看,大吃一惊:红薯没插完苗,棉花没打完杈,花生没扯完草,芝麻没间好苗,稻田没除完稗子……季节不等人啊!老郝一生气,便骂队长。队长又骂社员。社员不敢骂人,就骂鬼天气。老郝总结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怨天怨地,不如怨队长。于是一面往墙上挂白旗一面宣布:开会,重选队长!
选谁不都一样?社员心中最清楚,队长选来选去,不照样穷横?不照样骂人?有个社员悄悄出主意道:“队长不是老骂人吗?咱就选黄傻子,他是哑巴,看他怎么骂人。”社员们笑着说:“中!就选黄傻子,反正他也是个种地好手。”
年届四十的黄傻子不愿干,可驾不住社员们纷纷朝他作比划、竖拇指,说你行你行一定行。他就叹口气,扭头望了望四周茫茫的田野:去年这时,该完的活儿早完子呢;而如今,唉!心里一着急,便软了下来。黄傻子一点头,就有人笑:有好戏瞧了;且看他如何派工吧。
带工的第一道活就是派工。过去村东头老柳树下的钟响了半天不见人来集合。家家门前露出一个脑瓜子,东瞅瞅、西瞧瞧,等那第一个走出来的傻球。结果,等了半天,被队长骂得爹不是爹、娘不是娘,这才迟迟出来。如今这傻子队长可不,钟一敲定,就站在那里默默数数儿,数了一百整,便不等人,第一个背家什下了地。那些人探出头一看,见新队长撇下他们走了,便娘啊一声,不敢耽搁,急忙赶上队长求分派活儿。
从此再没人敢小瞧这傻子队长了。
正是旺夏,日头毒。太阳迟迟不肯爬上来,好不容易上来了,又迟迟不肯落下去。偏偏是“锄禾须当午”的季节,社员们在地里死受着,个个骂着叹着,眼光不时地打量着队长。可傻子队长不言不语,光知道干活儿;他光着膀子,汗珠儿在那黑黝黝的脊背上蚯蚓一样地爬着。有人想打歪主意,见新队长干在前面,远远地拉了自己一截,便不敢再说啥。干到日头当顶,有的社员忍不住了,给傻子队长扔一块土坷垃,朝他鼓鼓嘴巴、挤挤眼睛、指指头顶,意思是:该收工了吧?哑巴却摇摇头,朝前面一片没锄完的地指了指,啊啊一番。社员们抬头一瞧,“娘呀”一声,吓得直吐舌头。
一天下地,把社员们累得腿软手酸,腰驼头抬不起来。想骂队长,却发现黄傻子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呲牙咧嘴,脸扭成一团。
“该死的傻子!”人们终于还是骂出口了。
“真是闷葫芦不吱声,肚子里有家什。”
骂也骂了,活儿也干完了,人人身上脱了一层皮。这天,傻子严肃着脸,突然比划着宣布:歇工三天,照记工分。
嗬,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的事儿。可又合情合理。消息传出,社员们欢呼雀跃,有人禁不住喊“反动”口号:傻子队长万岁。
傻子女人却吓得屁滚尿流,跑到哑巴男人跟前,手指指天,指指公社方向,又指指自己的脑袋,然后鼓着眼睛吓唬男人。哑巴男人怒目圆睁,脸上青筋直暴,指指地、指指自己的胸脯,然后一跺脚,气呼呼地干自己的自留地去了。
果然,老郝听说七斗冲停了工,不由得火冒三丈。就怒气冲冲地来找傻子队长,指着傻子的鼻子一顿臭骂,骂得傻子队长嗷嗷乱叫,又说不清,急得脸红脖子粗,只得抓住老郝的手往地里跑,老郝的手甩不脱,痛得嘴牙咧嘴叫唤。到了地头一看:地松了土、草除了根、庄稼绿油油的好壮。看完了,傻子把老郝拉到田边,手指稻田啊啊了一番,只见稻子不仅除了草,添了一层粪呢。接着,傻子又嗷嗷叫着要拉老郝进山,老郝早累得大气接不上小气,吓得身子直往后退,比划着说:“我知道、我知道,那山地里的花生芝麻都收拾好了不是?”“啊啊。”傻子连忙点头。“可也该派人广积农肥呀。”正比划着,突然看见水沟边上已有几个人正在扒土粪。原来他们都是生产队的缺粮户,傻子队长照顾他们,每天记双工分。
老郝站在那里,呆呆地半晌说不出什么话。这个过去一直落后的七斗冲,很快一跃成为全公社的先进生产队,在农忙过后休息几天,算不算错误呢?他没有琢磨透,只得抱着这个问题离开了七斗冲。
据说,有劳有逸的生产制度就是从这个时候扩广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