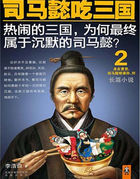一
曾殿臣老夫子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牛田哥了,他时常叫家人热一壶酒,炒一盘米粉与阿海对酌聊天。阿海也并不白吃白喝,他离开之前总让曾家的水缸注满井水,且时不时地替曾家砍一担好柴晒在门前。曾家自此柴、水不缺。自然,由于有曾监生的关照,使得渔溪人遇上喜事丧事或什么急事,都首先找牛田哥做帮手。在曾殿臣的眼里,阿海这个人,是不在乎你看不起他,但太在乎你看得起他。你因情急请他帮你“捉虎尾”,他也会不计风险地一口答应,而且说到做到,从来不计报酬。在此动乱年代,不但曾殿臣需要他,渔溪的许多家庭也都需要并得到阿海的帮助。特别是农忙季节,缺男劳力的侨属田户,犁田耙地、下种插秧,阿海是首选的好手。阿海也因此有点进益,日子过得不错。但阿海毕竟已有妻室,他不能不顾家。因此,曾老劝他把妻子接到渔溪来住,并准备为他找住房。不过,老外婆却有个心结解不开,死活都不肯到渔溪来。无奈,阿海只得经常两处奔走。
上次海口之行,使阿海对美玉有点失望。但他后来冷静地想了想:她嫁给谁对我阿海不都一样吗?自己在娶亲时已想过了,尽管她已成家,“感觉”也就是情谊,还是可以埋在心头的。因此,一时的失望感觉过后,他又开始想念美玉,惦念着她们母女俩,也连带地想到郁家贵。阿海知道,海盗出勤无非是拦船抢劫或沿岸打家劫舍。但不知他们此番出兵何处?他更为老十二郁牛弟的安危担忧。
郁家贵因为识几个字,又加带了几个人入伙,很快就当了“和平救国军”的大队长,相当于连长,但他手下实际上只有二十多人。他的上司支队长也是龙田人。和平救国军是占据南安堂的海盗,投靠日本人,据传某些头儿暗中又与老蒋的军统头目戴笠挂钩,进行所谓“曲线救国”。由日本人任命的第二集团军司令是张逸舟,副司令是福清县渔溪镇人郑德民。这帮海盗号称兵力三万,领了日本的武器在海上打劫,其装备自然是一般海盗比不上的。
郁家贵他们早就打听好消息并等待着林继祖回国。他们要一个渔溪人参加行动,以便出面认人。但那个渔溪人临时变卦,那无非是想到林家村在渔溪镇的长久势力,怕将来有麻烦。因此,郁家贵的快船等在渔溪浪官海面上,见到一个年纪、人样很像那个渔溪人描述的“林继祖”刚从轮船上跳到驳船时刻,就将此人一掳而去。当他们发现有误时,继祖已被林家村人接走。
那个被误劫的人,是张家村张雅悟的堂侄张兴旺,张家老少都急得团团转。过了三天,渔溪“兴福祥”杂货店,转交了一封张兴旺的遵命亲笔信,要一百块银元去赎人。张雅悟首先想到的是请牛田哥出面赎人,道理自然是充分的,但他的侄儿张四自告奋勇,要抢这份功劳,张老也只好让步。
张四按指定在龙田薯粉店接头,并到船上见了堂兄张兴旺时才交割银子。郁家贵他们劫不到林继祖的大钱,对这笔小钱并不是很看重,收钱放人了事,还跟张四交了朋友。张四对郁家贵他们说,山虎、海龙其实是一家,如果你们能带这么好的武器上山,山大王应是你郁某,而不再是阿头。此话容易说动郁家贵,因为他也感到日本人的炮艇在海上太威风了,常常使他抬不起头来。为了表示诚意,郁家贵命令煮黄虾炖米粉为阿四送行。
张兴旺回到家里才三天,“兴福祥”杂货店又收到一封来信,这次是给林老秀才的。
林尚南接到信时,见信封没贴邮票却又封了口,认为这是写信人对递信人很不礼貌的行为,想来自己不应有如此低俗的亲友。但他再想想,已民国了,世风日下,见怪不怪,也就启开一阅。那信上写道:
“林尚南秀才先生钧鉴:兹由筹集钱粮武器,敬请先生出面备齐计白银三千两,黄金一秤,步枪一百支,机枪十挺,子弹二十箱,三日内傍晚时分送至浪官码头。若逾期一日,本部即倾巢而出,蹈平贵村。专此奉告,届时勿怪言之不预也。”下面署名是:和平救国军副总司令郑德民谨识。信落款日期是二月廿四日当日。
林老秀才看完信,呆若木鸡,汗由头顶滚下,许久不说话。
秀才的三个儿子,继祖、宗祖、孝祖轮流看了信,没有一个能拿出主意。继祖人在客厅里团团转,脑子里却浮现神枪阿海沉着冷静的形象。在此紧急时刻,他多么需要阿海在身边啊!
“即刻持此信去请曾叔速来相议。”老秀才六神无主,想到老友与外间世面接触多,或有良策。老子是对着三子孝祖说的,但继祖认为自己是长子,家难临头,应主动承担责任。因此,他接过信就往外走。
已过了午饭时间,但曾殿臣跟阿海还在就着一盘炒米粉对酌,正谈论着经张四加油添醋的“义救张兴旺”的惊险故事。林继祖进门时,突然见到阿海,一时呆住了。随后他们便热烈地握手。阿海在新加坡见过这时兴的亲热动作,但他还是第一次亲自实践。
“你们认识?快坐下一起喝一杯!”曾叔热情招呼道。
“来不及说别的了,有急事!”继祖拿出那封信。
曾殿臣看完信后,交给阿海。继祖感到奇怪,阿海识字了?
阿海把信读得很仔细。他联想到陈美玉被送回海口,张兴旺被绑架却只要一百块银元就让赎身的这些情节,心中涌上当时在海上护航,听到熟悉的海盗枪声的那种感觉。但他未作声。继祖是第二次看到阿海如此专注与沉着的神态,仿佛眼前出现化解危局的曙光,但他也不想即刻追问什么。
曾殿臣读完信,知事态严重,但此时如无良策,只凭空口去安慰老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迟疑良久,想到那位新来的保安队孙连长。此人是黄埔军校出身,原在十九路军当团长,当年在上海与抗日英雄谢晋元团长交厚,是位爱国志士。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等闽变失败,孙团长无着,幸而他认识渔溪苏田村人林雅荪。林是保定军校出身,与陈仪省长同学,因此,出面请陈仪安排。陈将孙氏交给黄珍吾,黄仅将此事交给手下人办理,以至孙氏只当个保安连长。虽然,有关孙氏的身世,曾殿臣只是道听途说的,但连长不改爱国志气,把一连兵士管得军纪严整,却是他亲眼看到的。
孙连长初到渔溪时,经受了八闽乡绅惯例的下马威。大凡到渔溪上任的镇长、警察所长等,必由曾殿臣领衔宴请。那第一道菜甜蒸芋泥,是将煮熟的芋,在反面钵底里细磨,之后,加上猪油、白糖、芝麻粉等等拌匀,并在锅里蒸至少两个钟头。此菜端上桌时不冒烟,白得像冷盘点心,不知其厉害者,一口吃进必烫伤口腔。马镇长,熊所长都为此出过洋相,被烫得泪汪汪地吐出来。但那天请孙连长时,他俩都没提醒孙,以便让“新客”出同样的洋相。不料孙在一片“好客”的“请!请!请!”声中,把一匙烫芋泥咽下,只见他目光发亮,说不上是流泪,还笔直地坐着,一席人都服了。曾老跟林老秀才讲述这则故事时,还评论了一句:“看来‘叹为观止’也可用来称赞英武的仪态。”
曾殿臣带领继祖及阿海,急忙去找孙连长。孙本来就想结识这位深居简出而又德高望重的秀才,况且,治安本是自己任内的事,因此,他与曾老联袂而行,继祖与阿海随后。他们离林府还有里把路,门人就进去通报,于是林尚南亲自在后院西门口相迎。
“黄埔军校孙连长。”曾老特地介绍孙的出身,因为他知道老学兄很看重黄埔军校。
“幸会!幸会,大门请!”秀才作出引路的手势,家人赶紧去开大门。孙连长自然客气谦让,不过显得很兴奋。他虽然才来此地不久,但已听多人说过秀才的傲气,连林雅荪先生在此君面前,也要执晚辈礼,不敢平起平坐,今日受到之礼遇,非同一般。
这林府大院是“三进六扇”布局,大得像宫殿。孙连长到了大门口,只见那一对大红门联写着:
“西河忠孝无双士,南渡衣冠第一家。”
心中暗叹,好大口气!但那浑厚的严书,孙连长认定必是秀才亲笔。他想,来日若有幸得一纸墨宝,也不空此行。
上林府礼厅要进三道大门,而且每重大门内尚有一个屏风门。为越过那三个高门槛,把曾殿臣折腾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如此非常的时刻,老秀才还不肯缩短礼仪程序,要等上茶,上点心之后,才分宾主坐下谈话。
“今日事态严重,多劳二位贡献良策,以解燃眉之急!”老秀才这时语调急切,但并未将老友带来的“长工”看在眼里,因此只口称“二位”。
客厅里静得连各人的呼吸声都可清晰听出。林家的三个儿子,都站在老人身后,妇女小孩都躲在后厅偷听。
曾殿臣没主意,朝连长看看,也朝阿海看看。他感到有些尴尬:林兄在上茶上点心时,都未招呼牛田哥,此刻要出主意了,还把“能人”冷落一边,如何是好?于是他喧宾夺主地指挥道:“大家都坐下来,好好商量个对策!”
曾老对阿海如此说的时候,老秀才用异样眼光看着老友。但曾殿臣想,或许过几分钟你这老朽便知,我带来的粗人有多了得。
继祖心中有数,自己不坐下来,阿海是不肯落座的。因此,他打发佣人搬来几张凳子,让三兄弟及阿海都坐下。孝祖只见过阿海一面,但他立即想起这个大汉哥是大哥的护航保镖。他一时想不透,大哥怎能如此及时地找到自己的心腹?
“南安堂号称三万人马,就算三千,倾巢而出也算是大股的。我连虽然满员,有一百二十名士兵能打烂仗,但兵力相差悬殊,一时又无处可调援兵……”连长说得很慢,像是在思考、分析敌我态势。曾殿臣不明其意,以为没办法了,于是出主意道:“我看你们全村撤退,到我亲家的张家村去暂避,那儿一人当关,万夫莫入。”他用了水浒语言。
老秀才朝他看看,似乎在说“老弟,你又来了”,但此时自然不便如此说,只是叹了口气道:“撤退也只能一时,田产是搬不动的,这局势也不知几时了结!”
“不赶走鬼子,国无宁日!”连长接口说。他的话语虽然被打断,但他很快又回过头来说:“动用这么多的兵力,目标只限在你们林家村?”
“在下理解连长的意思。即使是,这大部队一展开,临近乡村也难保。况且,海盗是乌合之众,他们抢劫比打仗要紧,能保住他郑德民老家上郑村无殃吗?”阿海接着连长的口气说。
“先生说的正是本人的意思!”孙连长称赞道。
“英雄所见略同嘛!”曾殿臣再看秀才老友一眼,凑趣地说道。
“在下是粗人,请免‘先生’,渔溪人都叫我牛田哥。”阿海笑着对连长说。他继续说:“打听一下上郑村有无防备动作,便知虚实。”
“三天限期很快就到,应立即着人去了解!”连长说道。
“这不难,请二嫂回娘家走一趟便知。”孝祖对着他的二哥说道。
原来,这上郑村民特别看重亲友情谊,每遇风吹草动,都把四乡八里的亲友请来避祸。因为他们深信,大股、小股土匪,都不敢指染郑德民的祖家。
“即便是着人回娘家,也应只听不问,切不可惊动他们!”连长很认真地说道。
“照在下所知,土匪当得越大就越不肯吃窝边草。他郑德民对外吹牛说南安堂有三万人马。就算有,其中外县人占多数,福清籍不会超出五百,渔溪人顶多几十个而已,他带外乡人来洗劫家乡,将来祖墓都不保。”阿海话犹未尽。在他的脑子里,这事十有八九是郁家贵他们干的,只可惜当年自己不识字,如今无法根据字迹辨别是非。但他同时认为,即便能肯定是他们,也不可说出来,总不能让面前这些人特别是林老板知道,那帮海盗是我阿海的乡亲及结拜兄弟!
“你很了解敌情,这是很重要的。”连长称赞道。他接着说:“此外,如果郑德民的动作大了,他如何向戴老板交代?”
连长说此话时,老秀才目光疑惑,不知这姓戴的开什么店铺。曾殿臣用目光示意:“等一会儿我告诉你。”曾老虽然并不是三教九流都结交,但消息较灵通。他知道南安堂这班所谓“和平救国军”,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家伙,眼前日本鬼子强,他们当了汉奸。但他也曾听说,本镇乡亲郑德民是军统戴笠暗插的人。由于曾老与郑氏交情不错,这种传说对他是一种安慰。
“因此,我看这封信未必出自郑德民秘书之手。”连长拿了信再看一遍,认为这限定的日期、时刻都不确切。他正要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刻,阿海俯身指着信上的几个字,对他说:“此信行文不通!”
“唉呀!”林秀才接过信,仔细再读一遍之后,只发出这一声,就不说话了。他一生咬文嚼字,今日被吓昏了,那“倾巢而出”是贬义语,司令部公文哪能用此词自贬?老夫子用赞赏的眼神看了一下牛田哥。继祖注意到父亲的表情,有一种想法在心里酝酿着。
“郑德民本人识字,司令部更不缺管笔墨的人,何以见此童生笔迹?且公文用农历,这也是马脚,假货,假货!”曾殿臣打起边鼓,场面就热闹来了。
“这印槛也并非金石。”秀才很在行地补充一句。
“木雕的?”曾老不太在行,因而问了一句。
“番薯雕的都有!”阿海插了一句。
至此,好像紧急状态已解除,但孙连长并不这么乐观,他还继续思考着。
“不是倾巢大股,也不像小股散匪。对散匪来说,这胃口又太大了。”他仍然边想边说,大家又开始担心了。
“就渔溪下海的人来说,他们对林家村必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知道靠几十个人是拿不下村庄,更吓不倒你们的。所以最可能是外镇的那帮人,他们有所听闻,但还不知深浅,才有此举。”连长以所掌握的敌情,进一步推演,令在座的都肃然起敬。
林秀才的目光一直盯着这位后生,也很有兴趣听牛田哥再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