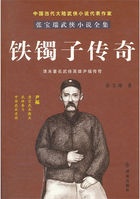说到跑板这事儿,其实是想说我干娘的浪漫史。说是浪漫史,其实也没有啥。说没啥,其实也有点啥。我干娘从宣传队里回来后不久,正是初春时候,树上的叶子都绿了,院里的那棵老槐树长出来很多新枝子。老槐树其实也是他们家的粮食树,散大伙那会儿,槐花儿、槐叶都充饥了,最后连树皮都被剥了一半。月桂再来剥时,我干娘死活不让,好歹是祖上留下的镇宅树。老槐树因此幸存下来,每年都是病恹恹的,被打了很多虫眼。我干娘没事儿就用竹签子一个一个地捅虫眼,往里灌水。无论如何也得保住这棵镇宅树,老娘不在了,这树还有倭瓜的一半。她心里这样想,也没有跟倭瓜透过,怕月桂惦记上,不定出啥麻秧儿,毁了这棵树。
那天,吃过中午饭,我干娘正在院子里捅虫眼,可能一个虫子被捅死了,一股腥臭放出来,我干娘就有些反胃。她用手去捂鼻子,手上也有味儿,便干呕了一阵子。她扔掉手里的竹签,听到西院的月桂跟倭瓜说:你这支书当的啥啊?整天不着窝,你的脑子还不是长在柳圈儿头上。你看看,连树都刺挠(欺负)咱。分家时就该是咱的,偏偏你窝囊,硬是圈到墙外边。这下好了,树是人家的,枝子偏遮住咱家的院子。不是欺负人吗?
倭瓜跟我干娘家还是在老宅子里东西院住着,中间只隔了一堵半截墙头。那月桂也是故意让我干娘听的,才高声大嗓地泄话(大声说话的贬义词)。我干娘听到他们吵架,故意咳嗽一声。
倭瓜听到我干娘咳嗽,想是我干娘可能听到月桂说话了,就骂月桂:你这张臭嘴就是说不出人话来,那树长着碍你吃碍你喝了?那是咱爷栽的树。月桂继续骂道。您爷栽的咋了?就是您老太爷栽的,不是咱家的树,就不能长到咱院子里。看你那熊样子,有点出息没,缩头乌龟似的。
你这个夯货就是欠打。于是,就传来了月桂的叫骂声,想必又打上了。其实,自从倭瓜当了支书,月桂比以前好多了,倒是倭瓜长了脾气。
我干娘转身进了屋,胃里又开始翻腾。她到了里屋箩筐里捏了一块红薯片,放在嘴里嚼着,谁知越嚼越反胃。
突然她想到了什么,就开始在屋里蹦跶。我亲娘去她家里借簸箕,看她正在屋里蹦着,惊叫道:哎呀,锨儿他娘,你这是咋了?
我干娘“嘿嘿”一笑说:没咋啊?吃撑了,蹦蹦。我亲娘将信将疑地说:你啥时候吃撑过啊?
过了两天,我干娘去了倭瓜家。倭瓜不在家,月桂正在翻柴火。我干娘说:月桂,倭瓜呢?
谁知道死哪儿去了。月桂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更不会停下手里的活儿。
我干娘也不介意,她说:你家的锯子借俺使使。
你借锯子干啥?是不是剶槐树枝子。我干娘笑道:你咋猜恁对哩。俺把它剶了,省得罩你家院子。
月桂一听要剶槐树枝子,连忙放下手里的杈子,去找锯子。她把锯子递给了我干娘说:谁给你剶啊?
俺自家,俺会上树。
月桂态度有所回缓地说:等倭瓜回来,让他给你剶吧,剶树哪是女人干的活儿。
啥女人男人的活儿,只要有劲儿就行。
中午放工回来,我干娘做好饭让柳铁锨、柳桂儿先吃。柳桂儿吃过饭就跟那帮小妮子下地去挖菜,柳铁锨去看剃头匠柳罗锅剃头。我干娘吃完剩下的饭,把锯子绑到腰里,“噌、噌、噌”爬到了老槐树杈股上,站在那枝杈股上开始拉锯。
那老槐树总共才四个老杈,她剶的正是伸进倭瓜家里最小的那枝。那最小的也有碗口粗。树枝剶到一多半时,她在上边晃了晃,觉得还得锯几下。她锯几下晃了晃,又锯几下。这几下锯完,把锯子用绳子绑着送到树下。待锯子落地,她闭上眼睛使劲儿地摇晃着,只听那槐树枝“咔嚓”一声,就和我干娘一起落到了地上。
我干娘掉在地上,就嗷吆嗷吆地喊起来。我亲娘正缝补我哥鞋帮后面的窟窿,听到我干娘叫喊,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进了她家的院子。她找了一圈也没看到人,便叫:锨儿他娘,你在哪儿啊?我干娘喊道:前进他娘啊,这儿,俺在这儿啊。
我亲娘说:俺咋看不见你啊?
俺在枝子里啊,俺上树剶枝子掉下来了。我亲娘这才看到墙头不远处有一个大槐树股杈,赶紧过去,我干娘就在里边裹着。幸好我干娘个小,一蓬槐树枝把她捧住了,不然,还不摔个粉身碎骨啊。
你剶树咋能掉下啊?
俺站在剶的那枝上了。
啊?你恁笨啊?剶哪枝站哪枝。
我干娘“嘿嘿”一笑说:俺忘了,掉下来俺才知道站错了。我亲娘把我干娘扶起来,我干娘说肚子痛,八成是摔着肚子了。我亲娘摸摸她的腿、腰问她痛不痛。她说哪儿都不痛,就肚子痛。我亲娘看着她的一双没穿鞋的大脚说:脚呢,脚痛吗?我干娘说:脚也没有事儿。我亲娘说着顺着我干娘的脚往上瞅,这一瞅不要紧,就像蝎子蜇着似的跳了起来。一条蚯蚓从我干娘的裤腿里钻了出来。
曲鳝(蚯蚓),你裤腿里有曲鳝。我亲娘叫道。
我干娘也害怕曲鳝,顾不上肚子痛,从地上跳了起来。她这一跳,曲鳝就洇到地上了,成了几个点。我亲娘说:锨儿他娘,不是曲鳝,是血啊。哪儿出血了?
“身上”(月经)来了。
“身上”也不能一摔就来了。
我干娘“嘿嘿”一笑说:那儿摔烂了吧?
我亲娘说:啥事儿搁你身上都不是事儿。摔成这样,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亲娘把一拐一瘸的我干娘扶上了床,血就不停地流出来了。我亲娘找了一块破布片子给她垫上。
我干娘说:前进他娘,真是身上来了。这回咋恁厉害呢?你见了倭瓜跟他说,俺腿摔断了,得几天不能上工。
可不是啊,摔成这样还能上工?你啊,咋恁耿格(坚强)哩,你找谁不能替你剶啊?只要言一声,倭瓜、前进他爹,都在家里。剶树哪是女人干的活儿啊。
我干娘肚子痛得龇牙咧嘴的。她说:前进他娘,给俺烧碗茶吧。我亲娘说:中,烧茶下点啥?
下把槐树叶吧。
算了吧,烧茶下槐树叶算啥呢?
俺屋里还有一些红薯片,丢上几片也中。
我亲娘说:你这日子过的,俺回家抓把小米给你下锅吧。
我亲娘给我干娘烧了一碗小米茶,就回去了。
第二天,柳铁锨去我家玩儿,我亲娘问他娘起来没有。他说,还没有起来,柳桂儿做的饭。我亲娘问做的啥饭,他说烧的红薯片茶。我亲娘揣了两个鸡蛋去了我干娘家。那是我家换盐的鸡蛋,我亲娘是冲她们的革命友谊,才下了狠心拿去的。
我干娘蜷曲在床上,因为出血过多脸色蜡黄,躺在床上不能动。看我亲娘去了,少气无力地说:前进他娘,你说俺真不能活了?
说啥你,去卫生所包点药吧。要不俺把柳大牙叫来,给你看看,肯定是摔伤哪儿了,恁高的树。
柳大牙是我们集上的赤脚医生,现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柳国强他爹。我干娘大闹我们学校那场事儿,就是听了柳大牙的女人——柳国强他娘的话引起的。
我干娘一听我亲娘要找柳大牙,着急地说:别,别,俺就是死了也不吃他的药。前街柳大傻的婶子,不就是吃了他的药才死的吗?
那柳大傻的婶子是跟人家混有了(怀孕),让柳大牙给她弄的打胎药,打得忒狠了。人家让她吃两个,她吃了一大把,不死才怪哩。
小月子也能死人啊?可怜孤儿寡母的,却遭了那殃。你说,谁想当寡妇啊?都是命赖。前进他娘,俺前天从她家门前过了,不会是她扑俺身上了吧?
我亲娘说:你从树上掉下来,跟她扑不扑啥碍了?你先躺着别动,俺拿了俩鸡蛋,给你打碗茶喝吧。
我亲娘打好鸡蛋茶给我干娘端上,突然就想去茅房。那时候,女人一般不会在别人家里上茅房的。可是,我干娘还没有喝完茶,再说她家里也没有别人,我亲娘就去了她家的茅房。在茅房里,我亲娘惊得说不出话来,茅坑里有个血糊糊的肉疙瘩。想起我干娘将将(刚才)说的话,她明白了我干娘到底是啥病了。只是,葫芦不在家,也不见我干娘跟谁有过特别来往,咋就有了这种事儿呢?我亲娘出了茅房,找到她家的铁锨,把那个东西埋了起来,同时也把这天大的秘密一同埋掉。
关于我干娘的病,没有人怀疑过什么。外边都传说她剶树摔下来了,都笑她笨,后来竟然传为柳家集笨人的经典:柳司令剶树——剶哪枝站哪枝。
我干娘病了半个月,半个月后又上工了。我亲娘注意到她这半个月竟然没有去谁家串门,要知道她可是个“串门精子”,只要有个放屁的工夫也得到外边转一圈。在柳家集,谁跟谁相好,谁跟谁有仇,谁和谁走得近,谁和谁有隔阂,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柳家集真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连谁家的鸡把蛋丢到谁家,谁家的两口子夜里闹出了大动静,都会像水蒸气一样冒出来。哪怕是“没眼儿”(没根由)的事儿,也能传得跟真的一样。当时还有人说柳大成跟月桂相好,要说后来也有可能,可那时倭瓜当着支书,咋有可能?都是因为倭瓜顶替了柳大成,柳乔氏才编派出来的。这柳乔氏也是精明过头了,你编派谁不成,非得编派自家男人和人家女人。还有人说柳大傻跟胡桂荣有秧儿(关系)。可是关于我干娘的病,竟然没有人说啥,就像她打了一个嗝。连放个屁都不及,放屁还有一股子臭呢。当然,这事儿除了我亲娘的猜测,也就成了柳家集永久的绝密了。我干娘大概从来也没有后悔过,没有怨愤过。照她的脾气,爱就爱了,做就做了,有怨也不会憋在心里。她心里从来不放跟情绪有关的东西。路弯理直,远近亲疏,都在骨子里长着呢,就跟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让我干娘剶树坠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大概在葫芦出去的几年里她有过一个可心的人,爱不爱的说不上,只是她竟然没有闹出一点动静,这也太不合她的性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