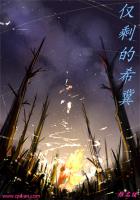“文革”中涌现出一大批敢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豪的青年学生,实在不值得奇怪。“文革”前的教育使他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使他们有充足的语言技巧训练。1963年起中共与苏共论战而发表的《九评》,许多学生反复吟诵,烂熟于胸。那大气凛然的口气,恰到好处的引证经典,咄咄逼人的反诘和尖刻的挖苦,学生们已经在作文和批判会发言中演练多时了。比如描述形势时总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管论敌是否日子混不下去,都要送他一个“向隅而泣”。这一类语言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直到1994年我在海南,一个朋友——他是某公司经理,在职的经济学博士生——给法院的诉状中也使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拭目以待”之类套语。
1967年夏季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我愈来愈感到困惑:“文化大革命”怎么变成了“武化大革命”了呢?我和几位新交的朋友开始坐下来研究形势。他们是总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机关报的编辑,因此收集全国各地运动形势的资料比较方便。我们有计划地阅读理论和历史书籍,不时聚在一起交流讨论。我们特别重视各地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呈现出来的规律性。这种关注,使我现在对于“文革”的研究都获益匪浅。探讨到一定程度,我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与热衷于打派仗的总部头头发生分歧。记得在秋天,总部核心领导制定一项代号为“上甘岭战役”的计划,我们听到消息后,深感全省几十万人的政治生命不可儿戏视之,于是破门而入,陈述自己的意见。总部大员们当然并未采纳我们的主张,继续一意孤行,但对内部冒出的一批“持不同政见分子”,他们也并未采取任何警戒或制裁措施。
我们这个自发的、未挂牌的“文革研究小组”后来散了。其中最令我怀念的是何,他沉静好思,想得多,说得少。当两大派实行大联合之后,他作为总部工作人员,参加了C市革委会成立的盛大庆祝会,被本校原对立派同学发现,然后抓回学校,连夜拷打,最后被装进麻袋毒打致死。我和同伴去向他告别时,看见遗体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他从不参加武斗,招恨的原因是他当初是对立派的头头,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改变了观点加入我们这一派。他被视为“叛徒”,可以说,他是因为坚持自己信念而死的。我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小曾,他血气方刚,喜怒立见于色,是成都第一名牌中学学生,我们讨论或辩论时,他总爱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引证材料或数据。他下乡后开始研究中国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曾写信给陈永贵,问他是否真相信大寨道路行得通,对全国有指导意义。信被转送到省革委会,他被扣上“怀疑大寨道路”的帽子,差一点被逮捕。1977年恢复高考,他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上成大学。前几年他出差途经北京与我相见,显得神情颓唐。当然,以他的聪明和能干,现在得到的地位和待遇并不差,但他在科技或文化方面的志向,却落空了。他是因为自己的天真、热忱和执着而遗憾终身。和我们一起探讨的还有一位女同学蔡,她1977年考入英语系,接着移居香港,后来从事新闻工作。以前红卫兵的那股劲头,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但关心国事和吃苦耐劳仍一如既往,因此很快就干得有了些名气。
二、深入“虎穴”的舌战
为了加强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我决定与对立派最优秀的理论家对话——他们是S校某个战斗队的成员。那时候,一些大学高材生不一定是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比如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宜挂帅),他们就形成了类似高级智囊团的圈子。我要找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周围的人听说我们准备去S校,很担忧,纷纷劝阻。当时武斗中双方都有点杀红了眼,S校的理科大楼据说是一个武斗据点,被我们这派的人称为“盖世太保大楼”。据说外省与我们观点相同的某一派被打垮后,一些武斗高手窜到C市,策划了一次行动,穿上军装,开着摩托,冒充警备司令部军官到S校,谎称接他们的头头去开会,直到上车的最后一刻,阴谋才被识破,一次传奇性的绑架遂告失败。这个故事也许不那么真实,但在我派人员心目中,S校一定是戒备森严、阴森可怖的。
接待我们的是化学系一位高材生,曾是校游泳队队员,百米蛙泳冠军。我对这种人相当看重,我们信奉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座右铭:“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希望自己的对话者,都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概。这人开始似乎没有把我们这群中学生放在眼里,企图开导我们,搞策反。我心中暗自生气,一旦抓住发言机会,便滔滔不绝地向他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是有备而来,很多问题他明显没有想过,只见他不断地皱眉蹙额,刚才居高临下的气势全没有了。
第二次对话,对方显然派出了空前强大的阵容,有五六个大学生等着我们,一见面就发起了凌厉的反击。这次轮到我张口结舌,感到力不从心了。与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论点不同,他们的核心思想是“继续革命”。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具体内容已无法复述,但迸溅的思想火花,其耀眼和多彩的感觉至今没有消失。再经过一两次拉锯战,双方一致同意,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上,各方侧重点有不同,继续探讨和交流是有益的。
在这种交往中,我和该校数学系学生萧成了好友,友谊持续到现在。萧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声若洪钟,是学校长跑冠军和排球队队员。与我们交谈时,他常着运动短裤,背心,赤脚,风度全不落俗。他思维严密,气质超脱,最善于从问题的纠缠中抽身而出,专注于论述中隐藏着的前提和预设。他影响我们在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自然科学上下工夫。我们一起阅读和讨论的书有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林赛和马根脑的《物理学的基础》。后来我和他一起自学数理逻辑,我们经常发出感慨,只知“诗书礼乐”的中国式文人要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是先天不足的,与科学和理性精神隔膜,犹如儿童发育过程中严重缺钙。
萧借给我一本怀特编的《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使我爱不释手。我后来考取了此书主译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
此书编者称摩尔为“哲学家的哲学家”,称怀特海“是一位试图在狮子自己的鬃毛竖立的兽穴中捋住唯智主义、唯物主义及实证主义的狮子的胡子的英勇思想家”,还把维特根斯坦的教学法比作禅宗大师的棒喝,把他的教学效果比作禅宗僧人所说的超脱经验的顿悟,这些都使我感到新鲜和刺激。但萧也有一点使我暗中不满,他宁愿将此书长期借给他当时的女朋友,一个初二的学生,而害得我用一个笔记本抄录此书主要内容。相比而言,另一个朋友就慷慨得多,他见我对他的《西方名着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十分喜爱,就送给了我,还说:“宝剑赠英雄!”从萧的行为中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再理智和有思想的人,处在爱情状态也是盲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小姑娘的拔苗助长并未成功。
三、探寻“第三条道路”
C市两大派斗争日渐激烈,两边营垒中都有一些主和派,但力量很小,成不了气候,我们考虑,这些力量能否先聚在一起,从两派中超脱出来,形成第三种力量?于是,许多人经常在九中聚会。
九中的组织是唯一不隶属于任何一派的独立力量,他们人数众多,纪律严明,头头好学深思,敢于坚持己见。我们去九中时,先与我们交谈的是一个高三学生谢。刚一接触,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头高大,肩宽腰细,披一件军大衣,目光炯炯有神,手势有力而夸张,使人想起电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后来知道他父亲是省人艺导演,他九岁时就登台表演,扮儿童角色,现在摆出“列宁在十月”中的领袖姿态当然不难。我认识了一位来自西南局机关的干部,他是某群众组织的第四号人物,厌倦了派性斗争,想组建第三势力。虽然我与他来自不同的派别,第一次见面,彼此毫不熟悉,但他讲起话来给人极其坦诚的感觉,分析形势既一针见血,又高屋建瓴。与此人打交道,我才明白了什么叫恢宏气度,大家风范。
西南局是党中央派驻西南三省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我这一派的头头作出响应姿态,大造“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的舆论,对立派显得越来越被动。在这关键时刻,西南局一个姓洪的女将,抛出一篇《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的文章,一下子就把舆论扭转了。这篇文章写得极为老练和雄辩,如果落款不是某群众组织,完全会被当成《红旗》杂志的社论。
这也难怪,据说洪女士是原西南局第一支笔。和这种官方专业秀才相比,我们这些业余的“理论家”就感到自愧弗如了。我前些年经常在《光明日报》上看到S省某些理论刊物的目录预告,知道洪女士正致力于论证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很想再睹其文采,看看她的笔力是否雄健如当年,但终究没找到有关刊物。
与我们接触的那位第四号人物,终于不能见容于他们组织中洪女士一类的多数,逐渐失去权位。我既尊敬他,又替他惋惜。不过“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他的失势,倒可能躲脱了日后当“三种人”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