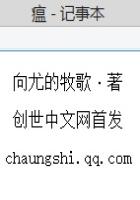第二部百乐门 第一章两个身世飘零的人 (1)
密集的乌云把天空遮得阴沉昏暗,一阵阵劲厉的寒风吹得一个小小土坟上的枯黄乱草颤栗抖动。这里没有高大的树,没有光滑的墓碑,满目尽是凄凉与荒芜。
一个神态严肃,头发花白散乱,胡髭很长的壮年人,捧着一束鲜花,一步一步很缓慢地从这荒冢崎岖不平的泥径上走过来。他走到这小坟之前把鲜花放在微微耸起的黄土上,默默地凝视这一堆黄土,眼眶中掉下一颗颗的泪珠。
阴霾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开始落下细雨来,他似乎并不觉得这是雨点,而是千千万万人的眼泪,悲悼长眠在这堆黄土下的年轻女子。
一年前的往事,像烟雾一般地在他湿润的眼前掠过……
夜色已深,悄然无声。像黑丝绒一般地天空中印着一条小舟似的残月,透出清冽的光来,萧瑟的寒风把秃了顶的树枝吹得不住摇荡。
画家王伟艺倚在平屋的门框上,仰望着无际的天空发呆,他的心灵上感觉无比的空虚与寂寞。
他一个人孤饯饯地住在这西郊的乡野平屋中,一年一年地消磨着悠长岁月。亲友嫌他太而看不起他,他嫌亲友傲慢现实而同样的瞧不起他们。于是没有亲友来探望他,他也不去访问亲友。
孤独使他的性情寡漠,沉默寡言,似乎像一个隐世的人。虽然年仅四十,头发已微微花白,神态严肃。他常将仅有的什餐或晚餐给附近比他更穷苦的村人充饥,而自己挨饿。
在这样一个清冷寂寞的深秋之夜,孤独的人更是容易寂寞的。
突然有一阵不规则,微弱的步履声从西面泥土小径上传过来。在这冷僻的乡野,在这深秋的什夜,这个步履声是不能令人不诧异的。
步履声渐渐近了。他隐约看见一条黑影正向他的屋子方向摇晃而来。
在他能研究这黑影是怎样一个人之前,这黑影已到了他屋子门前,并且倒了下去。借着屋内一盏煤油灯透出来的微光,他看清楚这是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子。他俯身下去对她仔细观察,发觉她仅仅是晖厥。
在他简单的救护下,这晖厥的女子缓缓地苏醒,挣扎而起,坐在地上对王伟艺凝视。
‘你感觉舒服一些吗?’他问。
‘好多了!是你救了我吗?谢谢你,老伯伯!’她的声音很微小,似乎身体已衰弱到极点
王伟艺听得这女子唤他为老伯伯,有一种不快的感觉,因为他根本不老。但是他自知微微花白的头发以及微微花白的长胡髭,容易给人家一个老的印象。附近村人的孩子们也唤他为王老伯伯,经他力加抗议与纠正,那些孩子们才唤他为王伯伯,他虽仍不很满意,但去了一个老字,无论如何总感觉年轻一些。
‘算不得救你,我只是给你灌了一些温水,’他说,‘你患了什么病吗?’
‘不,一点病也没有……’她的声音还是那样衰弱,王伟艺见她年纪最多不过二十岁,枯槁瘦削的脸蛋配着一双深黑的大眼睛,虽然不很协调,然而她的脸圆润一些的时候,毫无疑问,她是个很美丽的女子。
‘你既没有生病,怎会晖倒的?’他问。
‘噢!我已数天未睡,数天没……没有……’她吞吞吐吐地说。
‘你说呀!’
‘没有吃饭!’
‘噢!你饿慌了,凑巧得很,今晚我还有剩余的面包和糖酱。来……来……来,请到我的屋子里来!’
她挣扎了半晌,才勉强站了起来,王伟艺不得不扶持着她走进屋子。
屋子里的陈设非常简陋,一张白木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两条白木长凳,一张藤靠椅,此外并无长物。墙上却挂了不少油画与水彩画。
‘这是我的客厅,你在这里坐一会儿吧!’王伟艺把她扶在藤靠椅上。
在这客厅的右边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左边有一间小小卧室。王伟艺到厨房去了片刻,拿了一盒面包与一小碟糖酱出来。
这面包与糖酱增加了她的体力,她已不似刚才那样痪软了。
‘谢谢老伯伯!’她感激地说。
又是老伯伯——他最不喜欢听的三个字。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朱小翠。’
‘你好像受了极大的折磨?’他问道。
小翠点了点头。
‘你受了什么折磨呢?’
‘我是……’小翠欲言又止,‘不讲也罢!’
她既不愿讲,王伟艺也就不追问了。他已尽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义务。现在他希望她可以离去了。可是,那个小翠倚在藤椅上显著极为疲倦的神情。他没有铁一般的心肠催促她离去。
不久,数天未睡的小翠已因倦极而甜睡在他的藤椅上。
这使他感觉局促不安。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在屋中,是相当不便的,但唤醒她,叫她出屋他也于心不忍。他踌躇良久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年轻女子的身世,一定非常可怜,他应该尽力援助她。
他在卧室内取了一件自己穿着的大衣,替她盖在身上,并把大门关起来,为了屋子里多这样一个不速之客,他不得不坐在木凳上,等待天亮,等待她醒来。终于他也伏在桌上睡着了。
早晨,阳光从东面一扇小玻璃窗透射进来。小翠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身上所盖的大衣,又看见屋主人伏在桌上熟睡未醒,深深地感谢他给她人世间最温暖的照顾。
她轻轻地站起来,观看墙上那些签着王伟艺名字的图画,再环顾屋内萧条的光景,知道这屋主人是一个极穷困的画家。
当她正在观画时,王伟艺醒了。
‘噢!小翠,你睡醒了吗?’他问。
‘睡醒了!’小翠说,‘我衷心地,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仁慈的待遇。我已麻烦了你一夜,现在我要走了……’
‘且慢!我始终觉得你有难言之隐。昨夜你欲言又止,为何不告诉我,也许我能够给你一些援助呢?’
‘噢!你的热忱,使我刻骨难忘,然而……’
‘没有什么然而,你尽说何妨!’王伟艺说。
‘我是从海盐一个恶霸家里逃出来的丫环!’小翠说。
‘是否因为你的父母贫穷,将你卖给这一个恶霸?’
‘不,’小翠的眼眶里滚出两颗泪珠,‘这是一个惨痛的故事——二十年前,一九二五年的春天,那时我才一岁。我的父亲朱荣根是一个种花农人。我们世居在山东济南市郊外,有一块小小的园地,数代以种花为生。’
‘当时,盘据在山东的军阀手下,有一个姓张的大鼻师长常常带了卫队,到我们花园来买花。他窥见了我母亲长得非常美丽,于是就起了歹意。有天晚上,我们家中忽冲进五六个强盗,不问情由,将我们一家三口绑上了汽车疾驶而去。在离城三十余里外一条荒僻的公路上,张大鼻与他的卫队突然出现,拦住了去路,命令强盗把我们一家三口放下车来。那些强盗不服从这个命令,于是双方互相拔枪射击,这一场交战结果——强盗一个也没有打死,张大鼻与他所率领的卫队也未伤亡,仅仅把我的父亲击毙了。
‘那些强盗射击了一阵,弃车逃遁。张大鼻告诉我母亲,他从强盗手中把我们母女两人救下来,并且声称他将缉捕那些强盗,为我父亲复仇。他又殷懃地邀我母亲到他住宅里去当一名管家,当时,我母亲不知他的诡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带了我到他的住宅中去。
‘从此我们母女两人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我母亲在他住宅中做了几天管家妇,就被他强辱了,变成了他的侍妾。此时,我母亲明白了我父亲之所以被杀害,完全是张大鼻的阴谋。但一个弱女子要反抗一个带兵的军阀是很难的事;同时师长太太白梨花又用尽各种方法虐待我的母亲。
‘当我十岁时,我母亲一病不起,乘室中无人时,将此血海深仇详细地给我讲解,那时,我虽年幼,但这惨痛的故事已深深地刻划在我的脑海中。
‘没多久,我母亲逝世。我就变成了张宅中的小丫环。之后,军阀的势力消失。张大鼻挟着民脂民膏返归海盐原藉,做了当地大富豪,大恶霸。我则日夜侍候着残酷凶暴的白梨花。祇要稍不如她意,鞭苔立至,因此我终年体无完肤。
‘我忍受着无比的痛苦,是想等我长大之后,为父母复仇。宅中有一个老管家是比较忠厚的人,我偷偷地请他教我读书识字。十年来我读了不少书籍,懂得不少的东西。我虽已长成,难灭复仇之心,却苦无复仇之机会。
‘张大鼻在上海另有一所住宅。他不常待在海盐的家。白梨花见我长大成人,也不再我侍候她了。她把我调派在花园中打扫花园,并且不准我踏进住宅中去。有时她到花园里来游玩,身旁也总有四五个心腹佣妇追随左右。因此我只能一天一天地挨在仇人家里等待复仇的机会。
‘四日前,一个傍晚,张大鼻带了他的爪牙,回到海盐住宅里来。其中一个是先前当师长时的陆参谋。他们到花园中来恰巧遇见了我。
‘“小翠,三四年没有看见你,居然长得如此美丽了!你比你的母亲更美丽呀!”
‘这个天诛地灭的张大鼻一边说一边竟伸手来搂我。我用力挣扎脱身,逃往花园角落里我所住的一间石屋中,把门紧紧关闭起来,张大鼻与他的爪牙追了过来。
‘“小翠——你开门,我有话和你讲……”
‘我不理他,也不开门。我听得陆参谋对他说:“老张,你要这个小姑娘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