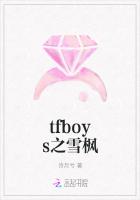让她舒心,让她忘却所有的不快乐,让她做回最本质的那个,颜知恩。
那个女人,根本就不会知道,她轻易舍弃的,如垃圾般舍弃的女儿,会在七年后,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宝。
他的傻姑娘,那么傻的傻姑娘,那么骄傲,那么勇敢,那么善良。
是秦墨涵这一生,最重要的宝,他们理所当然地,为了那么个可笑的近乎滑稽的理由,抛弃的人,是他的心头肉!
剜掉,整颗心,也会随之废弃。
她缩在他怀里,嚎啕大哭,是诉尽了被抛弃的不公那近乎划烂心脏的委屈。
她记不清他说了什么安慰的话语,却有一句,她未尝刻意,却一不小心,记到了永远。
那么清晰,那么动听。
“恩恩,现在,你有我……”
那些曾经狠狠伤害过我们的人,不要去记得,因为你,总是能够将我那庞然的恨意无声无息的,泯灭化解。
颜寒风被连夜送回了颜家,秦墨涵抱着他的傻姑娘,哄着,和衣睁眼到天亮。
与人无尤,与己无忧。
外头,冬风作恶,呼啸张扬。他用双臂,分离出另一个世界,安静的,美好的,温暖的,舒服的,惬意的,安全的,不必担心醒来后,陌生茫然,不必担心,白天颠倒成黑夜,黑夜逆转成白昼。
“醒了?”秦墨涵看着怀里猫儿般的姑娘,弯起半边唇,笑,继而凑过去,额际印上一吻,“我去准备早餐。”
说着,翻身下床,与往昔的清晨无甚差别,仿佛,昨晚歇斯底里的一切根本就不存在般。
知恩悬在半空中的心稍稍降落,望着那优雅挺拔的身影,揉了揉酸胀发红的双眼,深吸一口气,努力牵动唇角,绽出大大的笑容。
然后,冲进浴室,换衣服,洗漱,打扮,看着镜中原本憔悴颓废,面色惨白的女子一点一点明媚起来,心情,无端跟着渐次变好。
或许,她便是这样的女子。
哪怕天塌下来,也能在一夜之间迅速恢复,永远以最闪亮耀眼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肯泄露出半分软弱,不需要廉价而干瘪的同情。
可是,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厨房里的那个男人,如海洋般,肆无忌惮的宠溺与包容。
女为悦己者容,而她,仅是为了自己那份摇摇欲坠的自尊,与己者无关,从来如此。
她需要面具,需要将那个不坚强不勇敢不美丽不聪明的自己遮掩起来,哪怕,现在他已是她最亲密的人。
她出来的时候,秦墨涵深邃的墨瞳微亮了下,莫名多了些许复杂的意味,就是这样,她才一直一个人撑到今天,真是个傻姑娘。
软弱,不是坏事啊,笨。
“要帮忙吗?”她笑着开口,雪颊上打着淡淡的桃粉色腮红,像墨染开的桃花。
“放心,我的手艺在颜大厨的指导下,精进不少。”乐得顺其自然,她扮相完美,他不会点破,微笑着,眉眼清澈悠远。
心底,却不觉生出了些许无力感,他所能给的时间已然不多,但她心里的结,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得了的。
好不容易才宠出来些许女儿家的性情,一个晚上,全被她逼回去了,那双雪眸,明明溢满了苍凉,脸上,却有着比太阳花还绚烂三分的笑容。
宝宝,在我的面前,你可以不必伪装,不需要那个样子,知道吗。
很想说,很想开口告诉她,但终究,还是全数化成了眉眼间柔软的笑意,无声无息,寂静安好。
“当初不知是谁差点炸了厨房的?”知恩眨眨眼,笑容里多了丝狡黠的意味,转身,打开大门,出去拿报纸跟牛奶。
却在撞见门外角落里蜷缩着的小小身影时,诧异的惊呼出声——
他,他怎么会在这儿?
秦墨涵听见声音,快步走了出来,看了眼面色煞白错愕不安的知恩,再看着墙角里那张童稚无辜的睡颜,生疑,昨天明明已经将他送回颜家,今早,怎么又来了?
难不成,他一个人半夜三更偷跑出来,走路过来,又不敢敲门,所以躲在门外冻了一夜?
走过去,俯身,伸手覆住那额头,像被蛇狠狠咬了口般,瞬间缩了回来,他的额头,烫得几欲灼伤他的手!
“恩恩,快去开车,我们要马上送他去医院。”秦墨涵当即决断,眉头皱得老高,漂亮的墨瞳细细眯起,似在审视着颜寒风的病情。
知恩心口一悸,看着那张难受而无辜的小脸,双颊浮着不正常的酡红,唇瓣毫无血色,微微起皮,定然是烧得不轻。
管不了什么私人恩怨,救人要紧!
到了医院,值班的医生一量体温,蹭蹭蹭近乎三十九度的高温,看着孩子皱巴巴的小脸,十分可怜,不由得板起了脸孔。
打了退烧针后,出于孩子年幼抵抗力差,保险起见,大抵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彼时,接到电话的颜奇山匆匆赶来,发丝凌乱,双眸充血,满脸风霜的味道,面色苍白而憔悴,似是一夜未眠。见了知恩,眼神踟蹰带着心虚,喉结干涩,半晌,颓然开口。
“寒风他,没事吧?”
知恩攥包的手紧了紧,指骨抿白,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雪眸细眯,平平地“嗯”了一声。
秦墨涵看在眼里,眉头拢了拢,不动声色地将她揽进怀中,小心的,维护着她脆弱不堪的外壳。
“恩恩,我们回家。”
颜家,始终是她心底的一根刺,他不敢撼动,否则,一个不好,这根刺,会刺得更深。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她远离。
知恩点点头,虽然她很想推开他,挺直脊背,自己一个人离开,但如果这个人是秦墨涵的话,那么,可以相信!
孰料,刚一转身,便被一道糯糯而焦灼的女声给轰然定住——
“小风!小风!奇山,奇山,小风他,他怎么样了?!”
这个声音,软糯中涵盖着担忧,那么急促,那么紧张,仿佛见不到颜寒风下一秒就会死掉般,于她而言,又是那样的陌生,陌生到整整七年的时光瞬间,都不复存在。
知恩全身失控地颤抖着,像是被强行扒光了所有的衣服,硬生生赶到雪地里狂奔一样,冻得连骨髓都是寒的。连着呼吸,都变得十分难受。
小风?奇山?
呵呵,喊得真甜啊?真亲近啊?真熟悉啊?
知恩笑,却在听到那个声音的瞬间,脸色煞白,眼眶熏红,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
双脚像是植根于冰冷的瓷砖地,任凭怎么抬腿,可偏偏,愣是迈不开一步。
七年,多久?
按照三百六十五天的算法,总共两千五百五十五个日夜,亦或者,可以再精确一点,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个小时。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恰恰好,是她尚处在少年时期,便被迫一夜拔节,以成人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日子。
原本庞然的恨意,未曾随着时间的洗礼而减淡,相反,愈次加深,凝结,成了心底一枚坚硬的壳,将所有的脆弱无助,还有那个最本质的自己,统统锁在里头,坚固无比,堪胜金石。
很想知道,您,究竟有着怎样一颗残忍的心,竟可以心安理得的,将那么强烈而可怕的恨,加在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身上。
封存了七年的称呼——
母亲!
“恩恩——”唤着她名字的声音陡然变得凄切,似夹杂了万千情绪,好比那涓涓细流汩汩汇聚,成了浩瀚江河,内底暗潮倾涌,滚滚翻腾。
知恩隐于裙间的五指攥紧,纤长的指甲刺进掌心,原本惊愕狼狈的眉眼,在那一声过后,变得僵滞森冷,身子虽未动,可血管里温热的血液却“咔嚓咔嚓”寸寸结冰。
相隔不过两米,却像是隔了两个世纪那般遥远。
秦墨涵眼角的余光轻轻扫过她的脸,明明她的表情已由惊诧错愕复杂纠结恢复成平淡,如常的平淡,但他,却穿透了那层壳,看到了她悲伤到愤怒的火焰,绽出强大的光芒!
身后是不堪重负,悲伤地,呼唤着“恩恩”的声音。
恩恩,恩恩。
他想,他应该快点将他的恩恩带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她却抓住他的手,生生,掰开。
转身,回头,扬唇,微笑,淡定从容地姿态,找不出半分破绽,完美的一塌糊涂。
她笑,“冥女士,好久不见。”
简短的七个字,平平淡淡的口气,仿佛她们真的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今日不小心遇见,亲切的打招呼一样。
可她们,是母女!
是用骨肉鲜血连结在一起,紧紧牵绊,哪怕用劈天巨斧,也无法斩断的血亲!
七年未见,好久不见。
物是人非,莫过于此。
她微笑,说,冥女士,好久不见。
不是母亲,不是妈妈,而是,冰冷而清晰的,冥女士。
冥秀兰。
冥秀兰,那个苍老得能清楚看见皱纹的女人,早已失了曾经的圆润丰满,变得颧骨高凸,身板单薄,仿佛轻轻一阵风飘过,便可把她吹到似的。
站定,目光悲伤,看着她,无比心痛。
换了七年前,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表情,无需一句话,哪怕要她颜知恩豁出性命,她连眉头都不会眨一下。顶多,奉着《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母亲,就算失了性命,她亦心甘情愿。
可现在,她只觉得恶心,恶心得胃里面满是酸水,汩汩外涌,连昨夜睡前喝的牛奶都要呕出来了——
还要演多久?还想要骗她多久?
总是这一套,不觉得可笑吗?
然而,偏偏,更可笑的是,望着这个女人悲伤的脸,她竟然,半分,都恨不起来?
七年的思念——
午夜梦回。
岂能在一瞬之间转成庞大得几欲将人压扁的恨意?
“恩恩……”冥秀兰看着女儿微笑的脸,哽了嗓子,声线又凄切悲凉转为隐忍沙哑,隔了七年,终于得见,虽是末途,却仍然叫她红了眼。
这是她的女儿啊——
七年了,还以为有生之年不可能再见,原来,长大后的恩恩,是这副模样,着实,比她年轻时要好看的多呢,还那么能干,真好。
“冥女士,您的儿子在里面,麻烦以后请管紧一点,毕竟,这个年纪的孩子,家教可是很重要的。”
知恩脸上仍是笑,半开玩笑的口吻,可眉眼,仍不自觉冷淡几分。
应该说,一开始,就没有温暖过,只是被完美地掩饰住,骗过了所有人,甚至,她自己。
冥秀兰眼眶红肿,抬起经络明晰,干枯苍老的手抹掉泪,别过脸,叹息一声,“恩恩,是妈……妈对不起你……”
那么悲伤隐忍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在梦中。
知恩唇畔的笑意不觉敛去,淡淡的远山眉挑起,是冰冷到近乎虚无的神色。
她已不是七年前那个懦弱无依,无能为力的少女,不会再轻易的恨,当然,也不会再,轻易的,原谅。
此时此刻,心口郁结,非要说原因。
那就是她恨当年的自己有眼无珠,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生是死都分不清!
竟像个傻子般,被骗了整整七年——
枉她这么些年来,还自以为孝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强大,自以为狡诈,事实上,她从头到尾都是一枚可笑而滑稽的棋子,一个笨手笨脚的木偶,被人操控,看似自主,实则没得选择。
是她活该啊,怎么不聪明一点?怎么七年前跟七年后都一个样,还是那么蠢?
蠢得,无可救药……
“恩恩,原谅妈妈好吗?当初是妈傻,成天担心些有的没的。妈本来,没打算瞒你,但你这孩子,从小眼睛里就容不得半点沙子,我是害怕……所以才求你爸爸瞒着你的。”冥秀兰支吾着解释,头微微垂下。
害怕?害怕什么?
害怕那个温柔慈爱的母亲角色一瞬之间变成粉碎?还是害怕以生女儿为耻的想法被你那个傻兮兮的女儿得知?
绝妙的理由。
很好,很动听。
可惜,听上去,却让她恨不得自己此时此刻是个聋子!
“冥女士为何一直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我的母亲,七年前,可是由我亲手埋葬,不信的话,我现在可以开车带你去墓园参观一下。”
知恩挑眉,再度,笑了。
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口气,姿态落落大方,坦荡得连在一旁看着,不曾出言的秦墨涵,都不免深了眉眼,墨瞳掠过一丝无声的悲哀。
“恩恩,她是你母亲!”颜奇山豁然开口,疲倦的神色已被翻涌的怒容所替代,看着知恩,浓眉紧锁。
“所以呢?我是不是该称您一声父亲?”知恩冷笑,心脏一寸寸裂开,淌出嫣红的血,无声无息,痛入骨髓,漫过四肢百骸。
颜奇山语塞,他万万想不到真相揭开后,这个女儿居然还会如此偏激?
原以为,她至少,会稍稍谅解一下自己,不要求一夜之间冰雪消融,但不应该,这般凛冽才对。
知恩面无表情地看着父亲僵滞的脸,轻轻合上眼,半晌,睁开,唇角干涩,冲着冥秀兰深深地鞠了一躬。
她说,“对不起,我无法原谅您,很抱歉……”
妈,我有多爱您啊,可是现在,我却只能对您说对不起,以及,很抱歉。
如果不是曾经付出过那么庞大而厚重的感情,此刻,我又怎么会连一句,妈,这些年来,我很想很想很想你。都说不出口呢?
真的,我情愿您骗我一辈子,让我以为,母亲死了,然后,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思念您,想着您。
看,我多不孝。
呵呵。
可是从现在起,我连思念的资格都没有了,没有了——
我是您不要的!
我是你们都不要的!
颜知恩,什么都不是。
您口口声声哀求着我的原谅,可视线却一刻都没有从病房里的男孩脸上移开过,我不想嫉妒啊,但这颗心它却不听话,疼死了——
我真的,很想再喊你一声的,妈,但此时此刻,我更希望的,是你们就此放过我吧。
既然一开始就决意舍弃,那么,就维持原状,如何?
这些话,她没有说出口。
昨夜,已经哭够了,哭恶心了,所以,现在的她眼眶干涩,流不出半滴眼泪,连半个哀伤的表情都没有。
她也不会容许,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因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哭泣,颜知恩,没有这么脆弱,也不允许这么脆弱。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吐着吐着就习惯了,而胸腔里的那颗心,呵呵,痛着痛着就习惯了。
一切,没什么大不了,不是吗?
她还有手有脚,四肢健全,没病没灾,也没穷困潦倒,有房住有车开,有画纸有颜料,有能够完成梦想的能力,有供她展示的舞台,还有,一个能与她共同分担喜怒哀乐的男子。
上帝对她,已经足够仁慈。
那么,她知足。
作为回报,不再计较,任何……
临近年关,香港的天气愈发怪异起来,初晨还阳光熏暖,一到晚上,却倏然变了天色,乌云大作,狂风不止。
隐约,是要下雨的征兆。
秦墨涵近日出差,知恩本想着呆在家里构思新一季的设计稿,却不想童大小姐一通电话过来,噼里啪啦,愣是将她从窝里拉了出来。
美名其曰,老娘相亲第五十次失败,怎么着,这个面子你得给吧?
末了,放狠话,那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小修修现在已经喝高了,周围缠着一大帮狼女呢,你丫敢不来,嘿嘿,就等着你家小修修****吧。
知恩,握着听筒,黑线。
****?
这词听着咋这耳熟?
噗——
这不是一个礼拜前自己咒穆豪那厮吐出来的词吗?
驱车赶到时,才发现童大小姐真是大手笔啊——
竟然将整个场子全给包下来了,就为了庆祝相亲第五十次失败?
咳咳,问题是,那啥,这个需要庆祝么?
Few虽算不上香港最有名气的KTV,但因为其亲民的风格,所以场子几乎是夜夜爆满,离之一里外都能听见鬼哭狼嚎声,足见其音响效果之好。
知恩进去的时候,地板都在轰隆震动,高亢的电子音乐飞扬起舞,蓝紫色的灯光相互交替变暗变亮,打在脸上,像极了晕染的冷墨,泼在宣纸上,无须执笔,自成气韵。
墨绿色的U型沙发里,由于灯光太暗,根本看不清人,玻璃桌上散落着若干精致的酒瓶,瞅了下,啧啧在心底慨叹两声,奢侈啊奢侈,堕落啊堕落。
手腕倏地被人握住,滚烫的指节带着灼人的热度,回过头去,正对上一双琉璃般澄亮的蓝眸,彷如凝冻的钻石,闪着耀人的光彩。
此刻,却因为喝多了酒,蒙上了一层氤氲的醉意。
贺冥修猛一用力,将她扯进怀里,黑暗中,他一点一点摸索着她的脸庞,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柔软的指尖,愈发烫得惊人。
知恩被他勒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当即想要推开,奈何对方力道大得惊人,将她钳制得更紧。
她可以清晰地听见他胸腔内强而有力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泛着醉态的蓝眸一点一点,逼近。
对方纳闷开口,“你是谁,气味怎么跟恩恩一样?”
知恩笑,个死孩子,才几天不见又犯浑说胡话了。
还问她是谁?
“恩恩?假的?假恩恩?”贺冥修呢喃着,清甜的酒气扑打在她的脸上,微微瘙痒。
下一秒,竟一个倒栽葱,直接扑到在她胸前,呼呼大睡。
知恩囧,斜睨了沙发角落里醉得不醒人事的童微微一眼,此刻,她像只困倦的猫儿,蜷缩成一团,彼时眼睛已适应包厢内的昏暗,环视四周,哪有什么狼女啊?
敢情这桌子上一大堆空酒瓶子都是冥修跟这野丫头解决的?
正想着,忽然沙发上的童微微睁开眼,站起来,醉得厉害,步子踉跄,从后面抱住知恩,埋首于她的长发间,呵呵笑。
“我家恩恩,我家恩恩来了。”
知恩翻白眼,难不成自己今晚来就是要被酒鬼轻薄来着?而且还是俩?
“恩恩,我家恩恩,多好的一孩子啊,不能被他们毁了,不可以。”孩子醉了,稀里糊涂噼啪乱语。
知恩腹背受敌,眼见自己成了无辜的‘夹心饼干’,顿时一个头变两个头大,郁闷不已。
“恩恩,咱不哭哈,欺负你的人老娘一个个给你打回去!”孩子振臂一呼,豪气冲天。
知恩继续翻白眼,她几时在童大小姐面前掉过眼泪么?
额,没有吧?
“所以,不要再偷偷跑去医院看那女人了,她不要你,老娘要你!”又是振臂一呼,高亢的几欲刺穿她的耳膜。
知恩笑,“乌鸦嘴,我没事去医院干嘛?”
“靠,你丫忘了我妈是医生来着?傻恩恩,我跟你说,需要骨髓移植的不是那女人是她那便宜儿子!那女人从头到尾都是在演戏!她妈的根本就没病!”
知恩笑,眼眶却溢出了氤氲的雾气,微微发红,扒开她缠在腰际的手,轻叱,“知道啦,今晚咋这烦?”
“你知道?呵呵,你又知道多少呢?恩恩,你这傻丫头,你还在希冀什么呢?
丫为毛表面这么精明,实际上,真是傻逼透顶。
当初为了个疯子不惜众叛亲离,现在又因为个野种搞得自己进退无路。
奶奶的这年头你讲个屁的良心道义啊——
恩恩啊,我啊,冥修啊,我妈啊,我爸啊,姗姗啊,都很喜欢很喜欢你呢,所以,没有那个女人也无所谓,无所谓的……”
知恩脸色苍白,终于,再也笑不出,双肩失控地颤动着,指攥成拳,努力压抑着那份好不容易才藏好的悲伤。
这厢,童微微还在不停的说着,絮絮叨叨,反反复复。
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势,亏得穆豪赶来,三下两下,将她塞进车,动作干净利落,接着,迅速发动引擎扬长而去。
而她,自然负责将冥修送回家。
刚拦下一辆taxi,却不想贺大公子一个酒劲上来,长腿一伸,姿势矫健漂亮,直接给人车门上印了一个大大的脚丫子,气得司机差点当场呕血,二话不说,“啪!”地关上车门,有生意也不做了。
他撒娇,满是幽怨的口气,泪汪汪,“恩恩,我好难受……”
她点头,轻轻的嗯了一声。
他继续撒娇,整个人重心全倾斜在她身上,紧贴着她,咬手指,“你是喜欢我的吧,恩恩。快说,说你喜欢我,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
声线渐次沙哑,仿佛喉咙里哽着了什么东西,吐字不清。
他说,“你骗了我一次又一次,是不是越对你好就越不招你待见,对你不好,你反而上心?
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假装看不到我呢?
而且,还偏偏是秦墨涵,你明知他的底子,明知道他是言家人,你明明……都知道,还……
他那样的人,岂会为了你,背弃言家的根?
恩恩,不能再装糊涂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回来吧……”
知恩低头浅笑,只当他是喝醉了说胡话,疏淡的眉眼透着无奈,轻叹,“你又知道什么呢?”
如果,没有雪山的劫后余生,她兴许,就信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她想试着,去相信并且依赖那个人,与颜家无关,与言家无关,与他是言落川还是秦墨涵无关。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你会猜不到吗?
只是,你不信罢了。
贺冥修苦笑了下,沁骨的夜风冰寒森冷,他本就未醉,此刻,愈发清醒,清醒的无比痛苦。
他伸手推开她,踉踉跄跄地跌靠在街边的灯柱上,昏黄的灯光打在他微笑的脸上,俊美妖孽,一如初见,让人惊艳不已。
他说,“恩恩,我记得的,你还记得吗?”
知恩呵呵笑,走过去,牵住他的手,只当是任性的孩子,“我记得,你当时揍费罗,可厉害了,原来我家冥修打人也一样漂亮。
“恩恩,你是想重新变成我的小恩姐么?”他唇畔的笑容哀伤的近乎凄切,澄亮的蓝眸中水雾弥漫,映衬着苍白的面容,晕出些许落拓不羁的美感。
我家冥修……
自从我喊你恩恩之后,你就没再用过这四个字吧。
我全都记得,可是,你记得,多少呢?
设计稿被费罗那混球盗用,甚至还遭到威胁恐吓,在我面前,却半个字不提,笑笑笑,一直笑,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曾经不愿依赖我半分,现在,却可以全身心信任秦墨涵?
知恩不语,看着他,面色微微变样,雪眸细眯,眸底掠过一丝错愕。
握着他的手,指尖倏然僵硬无比。
他深吸一口气,笑,“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随时回去……”
他伸直了双臂,敞开了胸膛,骨骼肌理,一寸寸,伸展。
唇角的笑意愈深,“小恩姐,欢迎你回来。”
只要不离开,只要不被舍弃,那么,就算是姐弟关系,他也可以忍,绝对可以忍。
直到,她被那个人伤得体无完肤,他再带她离开。
此时此刻,谁都不曾想过,到底是谁被谁伤得体无完肤,又是谁,为了谁,不幸殒命,长眠黑暗。
好好珍惜吧,这末途的岁月。
等到再见时,不至于物是人非,反目成仇。
不至于,倾轧利用,残忍无情。
次日,清晨,公寓大门外。
“恩恩,你现在左有秦墨涵右有小修修,就忍心看我一个人唱单身情歌,哭到天亮啊——呜,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啊情分啊!天呐,你不分忠奸何为天!地呐,你错堪贤愚何为地!恩恩呐,你不帮小微微怎是人——”
小微微?
噗——
知恩嘴里的牛奶瞬间喷洒一地,《窦娥冤》都用出来了,这厮,狠。
敢情她颜知恩还能跟天地作比较不成?
“一大早的,扰我清梦,童小姐,我本可以将你轰出去的。”知恩重新叼了块吐司放进嘴里,眯起眼,看着眼前穿着一身正统过膝长裙,顺直长发,颇有几分淑女味道的童微微。
一没打雷二没下雨,这丫抽什么风?
抛弃性感路线转投纯情路线了?
“讨厌,明明每天晚上没有我孤枕难眠,现在人家来了,却要赶人家走,女人啊,就是这么喜欢口是心非——”边说,边伸出手环勾住知恩的下巴,暧昧的眨着眼,软语低喃。
温热的气息扑打,知恩嘴角抽搐,一脸吞了苍蝇的表情,半晌,脸色突变,反手握住童微微的手,轻舔舌尖,眸光四溢,含情脉脉,不怀好意地掐着嗓子,“死相!”
童微微轰地红了脸庞,触电般弹跳开来,指着知恩,哆哆嗦嗦,“恩恩,你你你你……”
知恩笑,无辜地抛了个媚眼,唇角弯弯,红唇微张,纯洁的像只待人捕捉的小白兔。
从小到大,戏弄人这份上,她可没输过。
更何况,还是戏弄外荡内纯的童微微童鞋。
童大小姐这次的请求相比之前有小小的不同,虽然都是相亲,不过,这一次,是她母亲挑的人选,一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家世虽不及童家显赫,但好歹书香门第,古韵悠长。
但刚一归国,就迫不及待要娶童家大小姐,呵,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相亲地点设在香港最高的旋宫餐厅,全天候,底座都在不停的旋转,约莫旋转一周,需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坐在这个餐厅里用餐,可以尽览整个香港的夜景。
男人名为金文,长得斯文有礼,全然对得起君子端方,温润如玉八个字,可偏偏她童大小姐听到人名字后,却是噗嗤一笑,金文?啊呸,老娘我还银文呢!
而金文身旁还坐了个男人,面目英俊,一身暗蓝色的西服配银灰色领带,深沉内敛,却掩饰不住一股狂狷之气,让人觉得危险。
“童小姐,你好。”金文礼貌的伸出手,一番寒暄后,介绍道,“这是我在英国的同学,唐武。”
知恩闻言,端着咖啡的手一抖,金文?唐武?文武双全,囧……
不过,更囧的还在后头。
好戏继续开演,咳咳,广告时间,马上回来,请不要走开。
旋转餐厅属西式,点餐时,金文要了一份鹅肝,唐武点了一份虾,童微微点了份七分熟的牛排,轮到知恩。
嘿。
她拿着菜单,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认认真真看了半天,然后,扬起头,冲服务员微微一笑,语气温柔的不能再温柔,像三月春风,拂人心弦。
“一份臭豆腐,再加两个咸鸭蛋。”
金文,一脸吞了大便的表情。
唐武,眉角抽了抽。
童微微低头喝着茶,哀怨抽搐的模样,就是肩膀抖啊抖一直抖个不停。
服务员小姐漂亮的笑脸当场僵住,那表情,无异于结了霜的茄子,白一块,紫一块,飘忽不定,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勉强一笑,问道。
“抱歉,小姐,您刚刚说什么?”
知恩吸了吸鼻子,“啪嗒!”把菜单往地上一摔,怒了!“臭豆腐!咸鸭蛋!我要臭豆腐咸鸭蛋——!”
气势豪迈,嗓音嘹亮,唰唰唰,餐厅周围的视线雷达般扫射过来。
好奇的,探究的,鄙视的,冷漠的,戏谑的,没表情的,看好戏的,齐刷刷全定格在知恩身上。
一定在想,哪来的乡巴佬,跑到西餐厅点臭豆腐跟咸鸭蛋?
孩子脸皮厚,孩子不脸红,孩子撅起嘴,用豪气的眼神一一顶回去。
心底却早已将童微微祖宗十八代上到高堂下至孙子统统拜访了一遍,丫丫滴,她的声誉啊声誉啊——
童微微肩膀抖得近乎羊癫疯,拼命地喝茶喝茶,单手捂住憋笑憋得肠子打结的肚子。
无声大呼——不愧是我姐们,够义气!感动啊——
一旁的唐武反应快,赶紧递上几张钞票放到点餐盘里,唇角轻扬,“请你想想办法。”
面如土色的服务员见有台阶下,赶紧拿着钱,屁颠屁颠地去买臭豆腐咸鸭蛋。
待其跑掉后,那厮还挑眉冲知恩一笑,“颜小姐很有个性。”
知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弯了眉,抛媚眼,拖长了音调,“合您胃口不?”
唐武还未来得及回答,这厢知恩已微笑着吐出一句。
“聊天五百,一次五千,包夜七千,唐先生人长得帅身材又好,我不介意打个八折喔。放心,我有定期去做检查,身体很健康。”
噗——
金文似是被茶水噎住了,连连咳嗽不止,原本白皙秀气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瞪着眼睛,看了知恩整整十秒钟,像是盯着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连着唐武,也不自觉地将椅子往后移了移,隔开些距离。
童微微见时机成熟,无辜地眨眨眼,皮笑肉不笑的补充道,“唐先生想玩的话,我有的是姐妹,给你叫上十个八个,我想,她们见着你,一定舍不得收钱。”
语毕,金文与唐武的脸均红橙黄绿青蓝紫一样样换了个色,精彩之极。
不用说,这出相亲,绝对黄了。
不过,咳咳,好戏还在后头。
“小贱人!原来你在这!”一声怒吼,四人齐刷刷转移视线,看着不远处一头发散乱,挺着大肚子,风风火火冲过来的浓妆女子。
三人成虎,除却颜知恩,童微微,剩下的,不就是姚姗姗了么?
金文跟唐武吓了一跳,登时站起,彼时姚姗姗已发了疯般扑打过来,“贱货!你还我老公!还我老公!”眼神疯狂凄厉,看了叫人毛骨悚然。
童微微猝不及防,忙一个闪身,躲到金文身后。
“啪!”
姚姗姗抡起一个大巴掌,不偏不倚,恰恰落在了金文脸上,力道深厚,五个鲜红的手指印赫赫发红。
金文傻了眼,用手捂着胀痛的左脸,目光有些呆滞,半秒后,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一样,尖叫出声,“你敢打我?!你竟然敢打我?!”
接着,扯过身后的童微微,指着知恩,大骂,“你认识的都是一群人?垃圾!杂碎!妓—女!泼妇!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我会看上去?要不是你是童家独女,我会想娶你?!不要发梦了!”
骂着骂着,这个斯文的男人泪汪汪,哭得一塌糊涂。
他哭了!
他竟然哭了!
然后,金文一头扶着他的唐武怀里,像受了伤的小动物般,嘤嘤啜泣,用一种令三人听了鸡皮疙瘩哗啦啦狂掉的语气哭诉道,“唐唐……她们坏,她们打我!呜呜,唐唐,我要回家,我不呆在这儿了,我不要——”
唐武一边安慰着怀里的人儿,一边愤愤地瞪了错愕僵滞的三人一眼,深情地抱着金文,哄道,“好了好了,别怕,别怕,我在,我在呢……哎,我早就说了,女人没一个好东西!你偏不听,笨,还去贪图人家财产,走,我现在带你回家,咱们现在就走!”
说着,两个大男人深情相拥一番,飞快的跑掉了。
留下三人目瞪口呆,风中凌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僵愕的说不出话来。
“靠之!”童微微率先反应过来,吐了口唾沫,“白费老娘这么多心思!”
“额……”知恩翻了个白眼,“他们竟然是……”
“GAY。”姚姗姗接过话,顺手抽出衣服里的枕头,高高耸起的腹部瞬间干瘪平滑。
正郁闷之极,一个戏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包夜七千,包一辈子,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