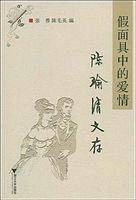淡泊是一种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它是人生挫折和坎坷的升华,它是九九八十一难的佛果,它是一个人心灵走向成熟的标志。
年轻气盛时,多数人的心中自然会蕴藏着万丈豪情,尤其是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更是如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切困难险阻似乎都不在话下。它洋溢着青春气息,充满着勃勃活力,它至纯至真,至善至美,浩气冲天,光照人生。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罗干十二而拜相,霍去病年方二十一而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刘胡兰年方十四就用生命和鲜血去印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人生哲理。”
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多少风流人物在年轻时欲奋发有为,安邦治国,一展抱负,可是在倍遭坎坷后,或纵情山水,或游戏人生,或退隐山林、皈依淡泊,就拿大家所熟知的李白、柳宗元、陶渊明等文学家来说,生平经历莫不如此,而且无一例外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二十六岁的李白在开元十四年,就确立“奋其知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远大政治理想,而且李白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屡次以大鹏自比。有诗可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终于在天宝元年,李白被唐玄宗召至长安,此时此刻,李白满以为从此以后便可平步青云,鹏程万里,实现毕生夙愿。“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人的狂放和喜悦溢于言表。可是宫庭的歌舞升平和腐朽没落使诗人李白陷入极度苦闷之中。由于李白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岸,很快招致宫庭内外的谗毁,不久被逐出长安,当然,他是在极度怨愤和深深失望中离开长安的。可是李白该怨谁呢?在现代人眼里,该怨的似乎是他自己。你李白虽才华横溢,但太不会“混”了,太无眼头见识了,像李隆基、杨玉环、高力士等权倾朝野的人岂可得罪,怨你自己不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无尊卑之分,无君臣之礼,酒醉后更是让人难以容忍,你怎敢醉后失态让高力士为你脱靴?你怎敢在醉后吐出“天子呼来不上船”?当然,李白还是值得庆幸的,倘若在长安再多呆上一年半载,恐怕小命也难得保了。理想破灭后的李白,只好纵情山水,借酒消愁,借诗抒怀,因酒而醉,因山水而痴。他终于怀着对官场的厌恶和对淡泊生活的神往之情写下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
与他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大文学家柳宗元,年轻时曾积极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革命,革新失败后,遭到长期贬谪。在他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他的二兄在今广西南宁市宣化的邕州马退山上建造了一座观赏风光的茅屋。每逢兄弟五六人相聚,他便手执古琴,登上山巅,目送还云,山间凉爽在襟袖之间,高峰万物,一览无余。我相被贬后的他,肯定看透了封建官场的险恶,功名利禄的无常,他把一切世俗的欲望置之脑后,心中只有这山,这水,无法这样去面对坎坷,无法这样去理解生活,诠释人生。另外,大家所熟知的晋朝陶洲明也曾做过八十一天的澎泽县令,只不过他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辞官,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平淡的生活。我想他向往的不是那种因诌媚而受宠,因苟且而偷生,因巴结而平步青云的官场生活。在他的眼里,一个洋溢着自然美和率直的人性美的归隐生活才是弥足珍贵的。
试想,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能有几个人能拥有淡泊的心境。时下,很多人得为家庭生计而奔波,为油盐酱醋而操劳,为子女择校、升学而发愁,为生病就医而伤透脑筋……哪容得你有喘息的机会去想“淡泊”二字。我忽然想起了时下流行的“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的叫人难堪的格言。我是一介书生,也曾读过几本诗书,身上自然有股书卷气,可我不得不生活在一边对功名利禄无限眷恋,一边对淡泊生活深深神往的矛盾之中,年少时那股傲气似乎难觅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