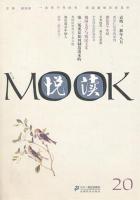在我开学的第二个周末,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小弟弟已经去了。我无言,我的前途是用小弟弟的命换来的啊!那晚我在操场上徘徊了整整一夜。
五月份,学校里为母亲节征文,这勾起了我对母亲的强烈思念。一篇《母爱》感动了全院师生。我把这篇获得一等奖的散文寄给了父亲,只想让他明白他的不负责任对子女造成了多深的伤害。
一周后我接到了父亲的回信,沉甸甸的足足十几页:“……你母亲被那个没良心的人抛弃了,同时抛弃的还有她肚里的你,我娶她是为了救她,我们商量好了,等你长大点再离婚,你刘阿姨还等着我呢。为了你母亲的名声,对外声称是我另攀了高枝,反正我要离开那个地方,听不到别人的唾弃。没想到的是你愿意跟随我,我亲爱的女儿……幸亏有了你,我和你刘阿姨才有了寄托……”
读完父亲的信我傻了,他并非我的生身之父,然而,他却给了我山一般深厚、海一样宽广的父爱。我竟然却一直在怨恨他,甚至报复他。我真后悔……。
寒冬
文/陈永林
一位农民父亲为了让儿子当兵去送礼,竟然冻死在冰天雪地的河里,这场面让人震惊不已。
空中溢满寒风狰狞的微笑。光秃秃的树干冷得瑟瑟发抖,发出凄厉无助的呜咽。空中铺满铅色的乌云,严密密地压在头顶上。
要下雪了。
我立在风中,脸被刀子样的风扎得生痛生痛。几个脚趾头好像断掉了,已感觉不到痛。
“爹,上岸吧,要不会冻坏的。”
父亲不搭理我。父亲仍摸他的鱼。父亲只穿了一条短裤衩。
“这些王八羔子都躲到哪儿去了?”父亲下湖快半个时辰了,可乌鱼一条也没摸到。在夏季,乌鱼很好弄。夏季,乌鱼怕热,总浮游在水面上,在鱼钩上放只青蛙或块面粉团,就立马能钓上乌鱼来。可在寒冬,乌鱼怕冷,藏在泥土里一动也不动,很难抓。即使人踩住它,它也动都不动,让人很难感觉到踩住它了。乌鱼鬼精。
湖水对湖岸怀着满腔仇恨似的,猛烈而凶狠地撞击着湖岸。我感觉到脚下的地在抖。我听见湖岸痛苦的呻吟。湖水一点也不同情,仍一次比一次凶狠地咬噬着湖岸。
父亲被湖浪冲了个趔趄,险些摔倒。
“爹,别摸鱼了,回家吧。”
“放你妈的屁,不摸到乌鱼,你狗日的能当成兵……”
父亲的声音打颤。
都是那狗日的村长!
听说在一些富饶的地方当兵很容易,可在我们这个穷山沟,想当兵的挤破头。每年冬季,都是亢奋而慌乱的季节。许多人都为当兵奔波。我们这些没考上大学的,如又想挣脱脚下这贫瘠的土地束缚,那只有当兵一条路。在部队考军校比地方上考大学要容易得多。如考不上军校,可学些技术,今后就不愁没饭吃。
学不了技术,争取入党也行。入了党,可进村委会当干部,或者进乡办企业,人了党的军人也不愁没饭碗端。
我也往当兵这条狭窄的路上挤。
去年,我验中了,可乡武装部只分给我们村委会四个名额。我没争到。原因是我们想抓住鸡却又合不得一把米。
今年,我验中后,父亲就忙活开了。
父亲拎了两条“红塔山”、两瓶“茅台”进了村支书的门。村支书见了烟酒,满口答应,又说:“只是村委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让村长同意。村长同意了,我没二话。”
父亲又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进了村长家。
父亲对村长说明来意。
村长说:“这事,我当然会帮忙。只是今年指标太少,只三个。而村里验中了的却十几个,能否去得成,我不敢打包票。但我尽力帮忙。”
父亲又把烟酒拿出来,村长不收。父亲说:“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不想帮这个忙。”
“忙是要帮,但东西不能收。”两人争了很久,最后父亲执拗不过村长,把东西拎回家了。
父亲脸上阴阴的。
父亲说:“村长死活不收东西,他不实心实意帮忙。唉!”
父亲心里急。
正巧,村长的女人得了一种妇科病,医生开了药,说要乌鱼做药引子才行。
父亲得知后,立马就下湖了。
父亲的身子开始抖了,“妈的,这……王八……躲……哪里……”父亲话都说不囫囵。
“爹,回家吧。这兵我不当了。”
我的泪掉下来了。
“闭……上……你……臭嘴。”
父亲仍摸他的鱼。
忽然,父亲笑了:“哈哈,终于……抓……住……你……”
父亲双手举着一条三四斤重的乌鱼。
父亲上了岸,身子一个劲地抖。父亲的嘴唇已冻得乌黑,身上发紫,可父亲还笑着说:“这回没白来。
村长见了这鱼,准会动心的。你当兵有望了。”寒冬,乌鱼捕不着,鱼摊上根本见不到乌鱼。
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汉子。汉子们见我手里抓着乌鱼,都转回头走了。
我知道他们也是为村长抓乌鱼的。
回到家,母亲把一红本本给我,说:“通知书刚下来了,过几天就走。”
父亲不识字,却端着“入伍通知书”看了许久。
父亲问:“这通知书谁送来的。”
“村支书。”
“那你把这乌鱼剖了,红烧,多用香油,要煎得焦黄焦黄,村支书喜欢吃。”父亲对母亲吩咐后,又对我说,“你去买两瓶好酒来。”
“那这乌鱼不送村长了?”母亲问。
“不送。”父亲生硬地说,“娃能当兵,全是村支书帮的忙。这情我们得谢。”
酒买回来了,父亲就去请村支书。
父亲把脊背上的鱼块一个劲地往村支书碗里夹。村支书说:“我自己来。”父亲说:“多吃点,这东西冬天里吃了,补肾。”父亲又端起酒杯,说,“我在这敬你一杯,娃儿能当成兵,全靠你了,在此谢你了。”父亲一仰脖,一杯酒一口干了。
“林子能当成兵,也亏了村长帮忙,我一个人不行的。乡长在外县有一亲戚,想把户口转到我们村,占我们村一个指标,村长挡着,把这指标给了林子。”
父亲“啊”了一声,笑便僵在脸上,但片刻,又说:“来,喝酒。”
父亲的声音一下没了筋骨、软绵绵的。父亲刚才兴奋得发红的脸也犹如门墙下的枯草,蔫蔫的。
外面开始下雪了。
吃完酒,父亲又出去了,母亲和我没在意,都没问父亲到哪里去。到吃晚饭时,我四处喊父亲,却没人应。母亲也慌了。后来,母亲说:“他是不是给村长摸乌鱼去了?”我跑到湖边,见岸上放着父亲的衣服,湖上却没父亲的影子。后来在离我们村二十几里的一个山脚下找到了父亲。父亲的身子已变得僵硬。
三天后,我穿着绿军装登上了火车。
雪纷纷扬扬下,满世界一片耀眼的白。
父亲的信
文/孙盛起
一位在土地上劳作一生的父亲,一位勤劳朴实、甚至连信也要求别人代写的农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在外工作的儿子的关心和爱护。
和前几次一样,李星把父亲的来信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
来这个远离家乡的小城工作已经快一年了,这期间,月月都会接到父亲的来信,偶尔一个月能接到两封。不过,所有的信,他只看过三封——前三封。
起初,他是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父亲的来信的。毕竟父亲一个人在乡下料理那一亩三分地,孤苦伶仃又体弱多病,让他放心不下。第一封信他在收发室里就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父亲不识字,一看就知道信是让邻居只上了三年小学就回家放羊的周二狗写的:
“儿子:你身体好吗?工作好吗?别担心我,我的身体还好,日子也还过得去。记住,别睡得太晚,别和别人打架,别和头儿顶嘴。还有,晚上起夜要披上衣服,别着凉了。爹说过了,要是你在外面惹了祸,爹就打断你的腿。父字。”
这封信对他这个中专生来看,实在是短而无味,因此刚拿到信时的兴奋转瞬之间就化为失望。尽管他并没指望一辈子和黄土打交道的父亲能说出什么优雅的字句,但这封信也太过生硬,仿佛无话找话,让他丝毫感觉不到体贴和温暖。不过,他还是立刻写了回信(信中故意用了一些周二狗肯定不认识的字词),向父亲说了一些小城和自己的工作情况。毕竟父亲省吃俭用供自己读完了中专,他也因此才有了这份工作,对这一点他是十分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