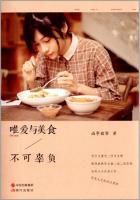我离开家前往邻市的火车站时,稠密的牛毛雨搅拌着城市空气里的沸扬尘土,零零散散地散落在沿途的路面上。呼啸而过的车轮,缓步或快步路过的脚步,从漫天上继续飘落的雨时刻在改变着路面上绘着复杂笔调的雨景图。雨水淋湿了那棵在我家门前安居了十几个岁月的槐树。
看着天空里的阴沉,乌云总在倾盆暴雨来临的那一刻,占据了天空舞台的主角位置,却将泪水遗留在大地,润湿了幸福与艰辛的人心,渗透进大地的根。
我是南方人,虽然的绵雨天再一些唯美主义者眼里颇具几分浪漫色彩,青天色的江南小镇,情似轻盈流淌溪水边的小家碧玉女子,依山傍水的千年楼台,沿着楼台溪边的绿水一直流向不知名的远处蜿蜒地段。而现实的南国小镇终归与繁华都市并无两样,只是人与车的数量的增或减。
虽然生活在南方,我缺始终弄不清楚自己是北方还是南方人。因为南北国都在下雪,只是它们的形态不同,一个淅沥得轻盈,另一个飘落得厚重。两者都是我的最爱,终也无法割舍。我喜欢吃北方的水饺,亦喜欢吃着南方的玉米面,只是北方那种豪爽的热辣让我稍微无法忍受。
因此时常听到人们说,南方人习惯在轻盈平稳的生活里走着碎步,北方人却喜欢在豪情的刺激山路上跨步。但我始终是南方人,脑海中关于南方的记忆多于北方。虽然很向往北方纯白的雪花,至今却还没有勇气,或者说还没机会与它共舞一场。
不知道北国那漫天飘絮的雪是否和课本上余秋雨先生笔下的阳光雪一样。天与地之间只回荡着《渭城曲》:“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年前的秋天,我静坐在高三的教室,看着课桌上一本本如雪花般厚重的复习资料,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习题,我需要做的只是不停地在上面提笔书写着,不知道该写多少久,月微笑,阳灿烂地微笑里都有我在那里书写的身影。
事实上与我同坐在教室里的其他同学也有同样的迷茫,唯一知道的是明年的六月天便是结束这种生活的时日,也是另一个人生开端的诞生之日。于是,在那个学期寒冷的冬天,我没有感觉到寒风冷雨的侵袭,拼命掩饰着不安分的心,做英语,数学习题,尽管它们并不青睐于我。
而第一年的高考我却落榜了,而且输得很惨,经一位友人的介绍,他的学校可以收容一批高考失意者。那时的我正沉浸在后高考时代的落榜惊恐不安与对大学生活的无比向往中,只想着如何收拾这场由自己造成的残局,最终跟随友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虽然那里还不算北国的区域,仅是距离自己家乡两千多公里路途中的一个外省小城。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一次行程让我这个终日只看到复习资料上密密麻麻字迹的人终也能亲眼目睹书本之外是另一个世界,稻田,高山,草原,农家。我好奇地看着,满心的疑问,一节开动的火车头竟能让二十多节车厢从容平稳地再铁轨上奔跑。带着有节奏的咔嚓声,似一位长者在低诉岁月里那些轻重的故事。
我走到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只见脚下是一条时隐时现的缝隙,若干的螺母整齐排列在上面,伴随着晃动的起伏却纹丝不动,它们若动摇了,又该有多少场梦境在这漫长的轨迹上彻底破灭。
透过厚重的车厢玻璃,外面沿途的景在视线中飞快后退着,似在流年里奔走的日子,无法仔细凝望某个聚点,匆匆地被时光带过,铁轨成了一条无终点的银色铁条,承载着我以及几十节车厢里的人们向着漫漫前方里的目的地奔进。火车的车厢设计简单实用,空气中透着微寒的干燥,但是漂浮着灰尘的颗粒。阳光从对面的高山斜射进来,辉映着那一张张疲惫与精神的脸。发丝里的肮脏与干净并重在这小小的空间,车厢里的尘埃附着过道上来回走动的人身,在阳光投影中调皮地荡来荡去。
月光从沉睡的建筑物的缝隙里照过来,仿佛是夜精灵在空气中游荡。火车在夜里疾驰,我靠在座位的一处玻璃窗上与这夜一同沉沉睡去,额头伴着有节奏的晃动与呼吸对话。
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它像一个神秘的怪兽一样蹲踞在那里,给我一种神圣伟大的敬畏感,每每火车拖着长啸的汽笛经过时,我总会想到在它身后远远地跟随着一群孩童,那里也有我幸福的身影。这火车,这铁轨从故乡的起点一直通向远方的目的地。
铁轨穿过繁华与寂寞的城市,穿过无数山岭与隧道,经过平原的绿野,漆黑的夜晚,我看着青春的时光缓慢地绕过岁月的山头。只是还没来得及在那里与它们亲密接触时,却很突然地返回了高三。或许在现实面前我还没资格做一个流浪的艺术家,就像我还不够了解江南的绵雨与北国的绒雪是不同的概念。
第一次走出故乡,我在漫漫的沿途中,担忧地看着窗外世界的瞬息变化,以至于去到新环境的校园,感觉那里终不是我所眷恋的地方,尽管曾一度梦想在这陌生的校园起航,于我却如羞愧者般再次乘上了返程的列车。心里却在自责,还带着那么一丝骨气,通出故乡的铁轨所带给我的没有梦想的期盼,却遗留下异乡的陌生遭遇与自嘲的内心,还有无缘无故被浪费了的钱财。看着光明和黑暗掠过我的额头,想起艰辛的母亲,给予我无私的爱与关怀,那光阴却在一天天无情地剥夺着她有限的年月,繁杂忙碌的日常生活压在她并不厚实的肩膀。于我却没有能力替母亲分担一些琐碎,还在毫无知觉中为她增加负担。
高四的那段日子,我继续任重道远地行走在青春的边缘,与密麻的复习题打交道,紧张而平静的内心在时光中荡漾。在母校中学里,时常会看到那些艺术生的身影,想着他们的心里一定有着非凡的梦想,为了踏上伸出故乡的轨迹,在高考前他们不得不日日月月在画室里执笔重复那些僵硬的石膏画,一次次地将调制好的水彩与油墨重新调配制,擦拭又绘着不同神情的人物像,直到符合考试的要求。那些亮丽的颜色在眼睛里失去了光泽。
我只希望那些怀揣崇高梦想的艺术生们在六月天过后都能踏上伸出故乡的轨迹,不要连做流浪艺术家的资格都没有。
同年的九月,我再次走过出故乡,同样的轨迹,不同的路线,只是这一次承载我的梦想的不是列车,而是笨重而高大的长途汽车。在离开故乡的那个夜晚,我看着汽车沿着高速路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光明与黑色的分界线上,那些逝去的年华,那些停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却永远弥留在始发地——故乡。
夜幕降临以后,长途车上的人们都在疲惫的行程中沉沉睡去,繁世的喧哗在此时便也褪去了它华丽的外衣。只是当深夜的汽车经过灯火通明的城市,我不能入睡。会梦到第一次踏在伸出故乡的轨迹里,我不能在远方目的地找到自己想要的愿景。
清晨醒来,我的第二次求学轨迹已到终点,那里的阳光与故乡的一样地灿烂,草叶上还淌着羞涩的露珠,那时轨迹遗留下的泪,不曾伤痛,却铭记冒芽时激动茫然的心情。
伸出故乡的轨迹,铺到了目的地,铺进了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