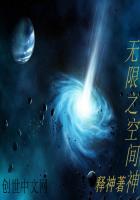瓦拉纳西的这家四星级酒店坐落在市中心的一个热闹地段,隔着院墙,可以看到大街上挤塞的人流。男人们的头上戴着花冠,成群结队的少女们则披着鲜艳的纱巾,人人脸上都流露着南亚次大陆人特有的微笑,感觉印度真是一个太容易满足的民族。这一天是印度回教的节日,远处的街心广场上,一群年轻人手拿木棒,正表演着什么打斗的节目,以致一开始我们以为发生了骚乱。
晚饭十分丰盛,这是我们进入印度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餐饭,不仅有各种甜点,还有从英国来的厨子为客人们当场烹饪我叫不出名来的蛋饼和小香肠之类。很想到大街上看看印度人怎样过他们的传统节日,但我们一开始就被警告,千万不要单个走上街头,以免发生不测。不得不捂着鼓胀胀的肚子回到花团锦簇的酒店,在大堂的沙发上呆呆地坐下,看一批批刚刚下榻的西方游客拖着硕大的旅行箱从我们面前鱼贯而过。这是一星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西方人,同我们一样,他们来瓦拉纳西也是为了朝圣,只是朝圣的内容有所不同,我们是因为佛教,他们是为了恒河,虽然恒河同样有着释迦牟尼的气息,同样充满了佛教的气氛。打开佛经,几乎处处都有“恒河沙劫”字样,佛将生命的无始轮回总是以恒河沙劫来作比喻,可见恒河对这位伟大哲人终身的影响。
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仍然是美伦美奂的场景,仍然是富足得让人叹羡的生活,但却不是我们这些天来所看到的真实的印度。“睡觉,”老王说。临睡前,老王特别地将一条耐克游泳裤放进随行的背包里,准备第二天去恒河沐浴。似乎刚睡下不久,床头的铃声响了,我们知道,又是一个黎明到来。匆匆地穿衣,收拾行李,下到楼下大堂,把行李塞进大巴,一行人开始向恒河进发。
天下着雨,这是我们进入印度以来的第一场雨。透过大巴的窗户,可以看到路灯昏暗的街道上三五成群的乞丐赤着脚在泥泞里行走,街道两旁的屋檐下睡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牛在街市无所顾忌的走着,在垃圾堆中寻找着食物。导游巴哈杜尔通过翻译开始向我们介绍他们的母亲河:恒河被称为印度最神圣的河流,印度人认为,人于其一生中必须在恒河沐浴一次,人若有幸死在恒河,则可免受轮回之苦,直接升天。翻译又告诫我们,如果看到在焚烧死人,千万不要拍照。印度人认为,那在烈火中焚化的生命正在升天,而相机的闪光灯会摄走他的灵魂。团长又特别提醒说,如果拍照,那是非要出人命的。
雨越下越大,而等到我们来到恒河岸边,已经是滂沱大雨了。天还没有亮,但透过密集的雨幕,隐隐看到一条微白的水流横亘在夜的幕布下,沿岸的吊楼下到处都睡着无家可归者,空气中弥漫着被污染的恒河水难闻的臭气,夹杂着浓烈的人气。有人不断地叫着:“小心,别踩了人。”还有人叫着:“小心地雷!”但这时已顾不得许多了,大家只是一个跟着一个,在暗淡的手机荧光下摸索着前行。天渐渐地亮起来,恒河横无际涯地沿着城市像一条刷把直拖到远处,河岸边杂乱地停泊着无数条木船。雨仍然猛烈地下着,老天爷似乎存心要与我们这批来自远方的游客过招,风一阵紧似一阵,夹着雨点,打在我们身上,衣着不备的我们开始感觉进入印度以来的第一次逼人的寒冷。大家在法师们的带领下双手合十,念起佛号,一声一声,此起彼伏。雨依然无休止无节制地下着,导游巴哈杜尔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一件件地脱去衣服,我们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巴哈杜尔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接着就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我看了看老王,老王低着头念着佛号,对眼前的一切完全无动于衷,只可惜了那条被他特意塞进背包中的耐克牌游泳裤。
巴哈杜尔终于结束了他神圣的沐浴,但我们却被告之,由于瓦拉纳西市政府近日对每只游船增加了税收,船工们从今天实施罢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无缘乘船游览恒河,更无缘去对岸采集被当作圣物的金刚沙。天光大亮,雨也住了,恒河上下,到处都是人,黄皮肤的人,白皮肤的人,也有黑皮肤的人,无数的人跳进河水里,他们全然不顾寒冷,全然不顾那被污染而发黑的河水所散发的阵阵臭气,将身体完全地浸到水里。小贩们在岸边兜售着供人们提取圣水的塑料壶,可怜的卖花孩子赤着小脚,托着花盘依次向人们走来,有人用随身带来的水杯舀起漆黑的河水大口地喝下去。有同伴激动地叫着,我终于看到恒河了,啊,啊!
受到同伴的感染,我开始认真品读起这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品读着这条神圣的河流。在河的对岸,是一片白亮的沙滩,古老的瓦拉纳西就像一个伟岸的圣人,高高踞守于危岩之上,审视着这条让无数人向往的永恒的河流。然而面对这条漆黑的河流以及河岸边成群的流浪汉,我却丝毫也激不起神圣和联想。我不知怎么竟想起我故乡的青通河,也是这样一条横贯东西的河流,也有一座踞守在河岸的城市,我的生命就降生在那古老的街道,比起恒河,故乡那条浑黄的河水以及那白色沙滩会让我生起更多亲切的回忆。这一刻,我开始想念它了。每一条河都有它特定的历史,都有它让人生起充满神圣的文化和传说。那是超越历史,更超越现实的,那是生活在苦难现实中的人们所必须的精神传承。恒河是恒河信仰者的故乡,青通河则是我童年的天堂。恒河于我是短暂的,青通河则是永远的。我真正的母亲河,她将永远地留驻于我的生命之中,并伴随我的生命流程,一直流到看不见的远方。
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焚烧死者的仪式。
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