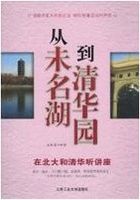两个月前我们曾来到这里。当时正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雪,这个春天第一场雪。似乎是在骤然之间,雪覆盖了这里的一切,河滩,河滩上的芦苇,河中央裸露的滩渚,当然还有河岸的村庄和树木。在雪的作用下,天底下的一切都显现出一派静穆,就像日本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画。与川端康成同处一个时代的东山魁夷总是习惯用飘舞的雪片来表现自然的宁静,读他的画,似乎真能感受到静止的画面上那动感的雪片落在树木上的沙沙之声。正是这动感的雪片,让人感受到画面的宁静。同川端康成一样,东山魁夷深受佛教的影响,他们都喜欢用笔来展现天地之源的生命之美,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个用文字,一个用色彩。
两个月过去,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同样的画面,只是色彩有了极大的变化。雨时断时续,是老杜诗中的那种江南杏花雨。这杏花江南的意境还原了大唐时代的风物和场景,只是,无论是村路还是这河滩上,都没有牧童的短笛,甚至没有一个人影。从很远的河岸对面,有村妇在洗濯,偶尔的棒槌之声以及她们交谈时不甚清晰的江南方言,像这雨滴,零零落落地打在脸上,感觉愈发清冷,愈发静谧。
我们走在河滩上,走在湿滑而光亮的卵石上。脚下的每一颗卵石都有着特别的形状特别的花纹,这刺激了我们原本泯灭的童心。我们捡拾着我们认为好看的卵石,直到行囊不堪重负。这一刻,我们的心情被这春雨浇灌得鼓胀满实,就像一粒等待爆芽的种子。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卵石一走进家门就会被弃之一隅,直到很久以后,妻子在打扫居室时才重新发现它们,于是,它们中间的一些被用作腌菜的压石,一些被当作垃圾扔掉。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当下一刻愉悦而透脱的心境。
河岸上有一条船。我熟悉这条船,几年前,我来这里拍一个关于我的小说的专题片,编导曾找来当地的一个熟人,让他载着我们从河的这岸到河的彼岸。船还在这里,当时的场景也历历在目,只是,再无法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时光已逝,留下的,就是无法复制的记忆。
关于河岸,我不得不再说几句。这常常被当作佛教隐喻的河岸曾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小说中。在长篇小说《红兜肚》中,当朱子尚背着他唯一的孙子,从河东乘渡前往河西寺庙烧香时,恰遇从河东往河西的应机和尚。和尚问他,二先生是要去河东看戏吗?船夫说,二先生明明是从河东往河西,和尚怎么看不见呢?和尚说,世上本没有东,也没有西,所谓东西,不过是人的妄想执着。只这一句,朱子尚悟了,也把一切都放下了。所以我要说,被我们装进行囊的这些卵石,其实并无好或不好,所谓好或不好,不过是我们一时的喜好。此一刻好的,等进了家门,便成了不好的了。想起近一些时因一些流言而受伤的自尊,不亦如此吗?人又何必为本有本无的流言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