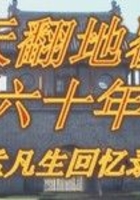计程船从潟湖减速转进一条狭窄的运河,驶了一小段后,便停靠在奇皮亚尼客栈前。在这间岛上小客栈门前等我的达里欧(Dario)先生,带我走过矮小的门厅,上了一道铺着地毯的木梯,穿过一条照明柔和的狭窄走廊,来到楼上我的客房。客栈的接待主任达里欧,数十年前便已在这里工作。他见过许多名人来来去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与菲利普亲王、黛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季斯卡总统(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其他在这住过的名人显贵。
厄内斯特·海明威也待过这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年。他在这住了整个冬天,写作,喝酒。“他是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当时是位年轻侍者达里欧回忆着。“他和妻子一起来这,但她很快又离开,因为不想打扰他写作。——我们基本上维持着他那时的房间布置。”他帮我打开写着“圣弗斯卡”(S。Fosca)的门时保证到。
一间大卧室,两张简单的床,旁边有两个床头柜。两床间有条宽大的通道,通向一个小客厅与工作间。阳台门边有张小巧的写字桌搁在一角,壁炉前有两个白色沙发椅。这个家居式房间中央的小桌上,一束花插在一个绿色慕拉诺玻璃制成的大腹花瓶中。在海明威床上过了梦幻般的一夜后,我隔天早上便明白这个小套房为什么叫做“圣弗斯卡”:因为从这可以越过奇皮亚尼客栈的花园看到圣弗斯卡老教堂。
在托切罗这威尼斯潟湖中的宁静小岛上,数十年来并无任何改变,除了在这不断开张的几个花园酒馆外,甚至可说数百年来没有变化。不过,全世界美食家的主要目标便是“奇皮亚尼客栈”。
搭乘一般公共汽船从威尼斯前来的人,由于回程要等候很久,往往被迫来趟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漫步,印象深刻不是因为在那可以见到的东西,还因为那里见不到的东西。因为托切罗今天只有数十位居民在这耕作捕鱼,但千年以前却是一座强大的贸易城市,密布着屋舍、教堂、修院和宫殿,比威尼斯还要富有,更具影响力。但在十四世纪及十五世纪间,人口萎缩,原因至今不明。有人归咎于当时肆虐岛屿的可怕自然灾害,其他人认为沼泽地带的蚊群散播疟疾,扼杀并驱走住民。威尼斯后来从空置颓圮的宫殿搬走搭建他们自己华丽建筑所需的珍贵建材。
从前停靠战船与商船之处,今天的公共汽船十二号在这上下游客与威尼斯的学子。一条介于圈围起来的菜园和小运河间的小路,从停靠站歪斜的老木屋通往黄金岁月时的最后见证:两栋低矮的宫殿,其中一间是岛上博物馆,还有两座古老的教堂。其中一座,圣母玛丽亚升天大教堂(Santa Maria Assunta)在公元六九三年便已奠基,公元八六四年重建,后来又再大肆更动。今天的建筑样式是在九世纪至十一世纪间建成。圣母玛丽亚升天大教堂是潟湖中最老的教堂,以其展示圣母与十二门徒的拜占庭式镶嵌作品闻名于世。另一座教堂,圣弗斯卡建于十二世纪,供奉拉文纳的一名殉教女子。这些老建筑围绕着的小广场上,现在长着杂草。三只猫慵懒地躺在秋日的阳光下,蝾螈无声无息地爬过断垣残壁。
公元四五二年,蛮族侵入维尼先的海岸地带。他们占领并焚毁阿奎勒亚(Aquileja)。亚提奴(Altinum)和其他地方的住民为了躲避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大军,在海岸附近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处,在五至七世纪于托切罗安顿下来。公元六三八年,主教把大教堂与圣物从濒临险境的亚提奴移至托切罗。
约翰·罗斯金在他的《威尼斯的石头》中给了该岛的访客理由充分的建议,在落日时分登上钟楼,欣赏绵延到“这片大海沼泽野生荒地”外的风光,那是罗斯金对这潟湖的称呼。如果面向东北的话,可以在地平线见到山峦;而在东边,可以辨识出亚德里亚海。“之后,远眺南方,”这位英国作家建议。
在潟湖宽阔的支流那一端,汇流处深沉的大海中冒出许多塔楼,散落在密集的宫殿之间,色调阴暗,一道不规则的长线条搅乱了南方的天空。
母与女——你见到她们俩都寡居着——托切罗与威尼斯。
一千三百年前,这片灰蒙的沼泽地带正是今天这幅模样,紫色的山峦一样在傍晚的远方绽放光芒。但在地平线处,奇特的火光和落日的光线混合一起,人类哀怨的声音掺进了沙滩上波浪呢喃的涟漪。火焰从亚提奴的废墟中窜起,哀怨的声音来自那里的人群,他们就像过去的以色列在大海的小径上躲避着刀剑。
牲畜在他们所离开的城市所在吃草休憩。今天破晓时,他们建起的城市大路上,已无镰刀的踪影,一捆捆柔软的草现在在夜里的空气中散发出香味,是唯一在弥漫在他们礼拜上帝的神殿中的香气。我们下到了那块小小的草地。
约翰·罗斯金之后百年,在钟楼上见到的风光几乎还是一模一样——除了几家罗斯金做梦也想不到的新餐馆;但他年轻的妻子艾菲却一定会想品尝的。在温暖的十月太阳下,我在中午时分踏入“奇皮亚尼客栈”餐厅花园中宽大的石子路。因为,不只古老建筑艺术的遗迹让托切罗令人怀念,其厨艺也吸引许多游客来到这座潟湖小岛上。知道在这个远近驰名的客栈中可以吃得相当实惠,令人开心,我找了一张少数还空着的小桌坐了下来,后方是有着绿色百叶窗的低矮农家,前面是那两座老教堂,周遭是花坛和菜圃,还有许多心情愉快、大半来自外国的客人与一群手脚灵活、轻松自在的侍者,轻快的步伐在石子地上发出柔和的嚓嚓声。花园中央还有一个古老的汲水井,海明威当时曾和他的朋友仇塞波·奇皮亚尼(Guiseppe Cipriani)在前面照过相。我自然点了一份马丁尼,看着面前的老照片。
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仇塞波·奇皮亚尼是“哈利酒吧”既成功又谦虚的开店老板,他常常乘着他的划舟经过托切罗,沉迷于这个近乎荒凉的岛屿的那份幽静。尽管奇皮亚尼当时还不算富有,却已下定决心,有天要在托切罗开家乡村客栈,而不管其他人把他当成疯子。
说来也巧,一九三八年,托切罗一间半塌的小馆子准备廉价出售。奇皮亚尼立刻买下。他对房子里外稍事修整一番,由于岛上还没有电,便弄来一套应急的电力装置,雇了一对娴熟料理鱼鲜的夫妻帮厨。由于奇皮亚尼在“哈利酒吧”担任厨子与调酒师的大名远播,不久后,第一批客人便搭乘摩托船来到这个新开张的美味之岛。
要是与世无争的奇皮亚尼认为可以在这个田园般的荒岛上,安然无恙挨过法西斯时代的话,那他就错了。“奇皮亚尼客栈”不只是找寻浪漫荒僻之处的小情侣热于前来的会面地点,也吸引了像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这样的政治人物。一九四二年夏天,纳粹的宣传部部长在这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举行秘密会谈;奇皮亚尼只能怒不出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客栈又再接待令人愉快的客人,他们在客栈的六个小房间中过夜,在花园中快乐享用着威尼斯菜。但今天在这最常被谈及的客人,便是厄内斯特·海明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那对夫妻住进客栈。海明威立刻考察了附近的环境,满意地表示这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地区相当适合打猎和渔钓。
他妻子玛丽离开后,海明威立刻投入工作。每当他一早解决掉十几只沼泽中的鸟禽后,他便盥洗一番,兴高采烈享用着奇皮亚尼为他准备的丰富中餐。有时饭后可以见到他在零度的气温下,在户外和当地人打拳。但每晚十点左右,他就回到房间写作,这点达里欧先生还记得清清楚楚。写作时,作家一般会点好几瓶“阿玛弘”(Amarone),那是一种浓烈的维内托地区(Veneto)红酒。一晚上,他会喝到涓滴不剩——至于多少瓶,达里欧先生就记不清楚了。
幽静的托切罗岛上,大部分的样貌大概和厄内斯特·海明威数十年前离开时差不多。我一打开他楼上套房中绿色的阳台门时,缤纷的花圃、一簇簇的色拉叶和紫红色的石榴便从花园迎面扑来,两座老教堂隐身树后,不动如山。草地和岛上少数住民耕种的田野,在右侧蔓延开来。潟湖的水在那后面闪烁着,而一群鸭刚从那嘎嘎飞起。吓飞它们的不是猎人,只是一扇无意间关上的窗子。
在房间老壁炉的书架上,这位在这住过、写过与饮过酒的作家的一部作品也搁在许多其他作家的书中。那是一本关于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