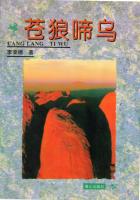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甜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地上有红色的白松的足迹,一直通到浴室里。
爱情底片
我用尽力气吐出一口气上了秤,指针停止摆动后依然停在“50”这个该死的数字上。
窗外夜色正好,有微风不时吹过,一丝泡桐花的甜香进入宽大的客厅,我拧着眉望着脚下的秤,真想把它拆散了扔掉,好抗拒节食加运动减肥20天却一点进展都没有的事实。白松轻轻拍拍我的肩,脸上是宽容的微笑。
我和白松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应该算我的半个父亲,但我们现在是婚姻关系。他把我从福利院中一大群孩子中挑选出来资助,他把我带进模特圈,让我成了他公司最耀眼的首席名模,他太太死后我们结了婚。
可是,并不是我没有自信,我只是经常弄不清,在他心中,我究竟是什么位置。
有个朋友说,想看一个人对你的态度,就给他一个相机,如果他拍出来的是漂亮的你,那他对你是珍重的;如果他拍出来的你很顽皮,那他一定会征服你;如果他擅长抓拍你美丽又可爱的某个瞬间,那么,他是你的亲人或者如亲人般了解你。
衣帽间的门上,贴满白松为我拍的宝丽来照片。照片中的我,或美丽或端庄或调皮,于是,我想白松是真爱我的。
但如果他真的爱我,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女人来往?
公司里每两个月会有一次小型选秀见面活动,一些从外地远道而来的漂亮女孩们等着被他单独召见。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女孩会签下合同,更多被他召见过的女孩后来就不出现了,连资料都消失。
我总在那些白松不在家的夜里胡乱想着他和那些女孩之间的事情,想着他们是否会上床以及他们在床上的旖旎。胡思乱想的结果每次都一样,我安慰自己她们是真的离去了,而不是做了他的地下情人,刻意躲避着我。也许白松打发了她们一些钱,也许他的魅力已经不够用了,毕竟他已不再年轻。
让我幸福
出了门,我和他都带着墨镜,宾馆门口,我们如明星一样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我们的生活宛若云端,高不可及。
“你该减肥了。”刚在餐厅坐下白松就小声在我耳边说。
我低头看了看箍在身上绷紧的外套,是该减肥了,上个月还很合身的,可手臂和腰部都绷得厉害。
餐厅里,每张桌子上都有支蜡烛,不甚明亮的光照过我们的身体,在背后的墙上投射成巨大的黑影,烛光一扭,那影子就动起来。
白松点的牛排只有三成熟,还记得刚认识他时他吃六成熟的,最近越吃越生了。坚硬的刀叉在白色的瓷盘上划过咯吱咯吱的声音后,滴着血的肉就被白松送进了嘴里,那一刻我有些恍惚,他的牙似乎是红色的。他吃得很快,也许真的饿了,最后还伸出舌把唇边的一滴血舔干净。
我的胃在抽搐,嘴里忽然涌起一股辛辣,最近胃口不好,想吐,什么也吃不下。不知道是因为影子还是因为那几乎是生的牛排,我第一次感觉餐厅里有鬼魅的气氛。
夜生活从十点半正式拉开序幕,各种各样的社交派对和演出,让人眼花缭乱。
跟白松结婚后,他只在晚上才出门,而且每次都是一身全黑的套装,搭配他日渐高耸的颧骨和比我还白的皮肤,有些像僵尸伯爵,不过更适合时下另类诡异的潮流。他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总有些觊觎时尚圈的男女围在他身边谄媚,像摇尾巴的狗。
不过,我没有白松那么好的精力,他几乎每天都是天将明才回家,而我,最多撑到两点多就要回家睡觉,而且一觉睡到大天亮,中途从来不会醒。
我遇到了一个很久不见的女友欣欣,她告诉我,白松的两任太太都是患厌食症死的。厌食症,是模特的职业病,我听过没往心里去。却不想,白松的目光在欣欣身上扫了扫。
照例,一点半我就回去了。
白松曾经说过,他只要最好的,他是个完美主义者。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刚结婚,还在巴厘岛度蜜月,他当时用手捧着我的下巴,望着我,黑白分明的眼睛,如引人入胜的棋局。最好的,属于他的我应该也是。
衣帽间,所有女孩进入这衣帽间都会惊声尖叫,满满的一线品牌经典款,光彩照人如阿里巴巴的山洞。我的女友都来看过这里,但她们即便喜欢上了这里的衣服也穿不好,因为每件的码都是最小的。白松对身材的要求近乎严苛,只有极瘦才更上镜,这也是他公司最有竞争力的原因。
白松结过婚,而且不止一次,前两任太太都是他一手捧红的模特。那个夜我永远都记得,他和第一任太太蒙娜参加慈善嘉年华舞会,开场的第一支舞就是他们跳的。我作为被他资助的学生,被安排和他们一桌。
蒙娜姐一袭月白色缎质长裙,美如仙子,他着午夜深蓝的爱马仕套装,贵族般雍容。一个华丽转身,蒙娜姐望着我笑了一下,那个瞬间她微笑的美深深映在我脑海中。如果有一天能幸福如她,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
我知道,白松有他的难处,表面上风光的经纪公司,虽然生意貌似热闹,赚的钱却很有限。被请去做电视节目上杂志,人家给的车马费往往不够他为了出镜添置的衣服钱。算来算去总是亏,按我们现有的状况,早就入不敷出,可他和我在一起时依然点最好的鱼子酱,最香醇的红酒。他说过,既然做了夫妻,就要让我一辈子幸福。
有夫如斯,女人没有理由不感动。
僵尸伯爵
但那个夜实在太闷热了,我做了噩梦。
梦里,白松脸色鬼魅般惨白,他撕掉我所有的照片说要和我离婚,他说我太胖了,根本不配再做首席模特。我哭喊着跪在他面前,求他再给我一段时间减肥。他忽然回过头来,眼里是前所未见的阴鸷,他说他来帮我减肥。
我愣愣地点了点头,他就把我揽进怀里,那怀抱冰凉,全然没有人类的温度。
白松神秘地笑了一下,露出两枚血红的尖牙,宛如传说中的吸血鬼复活。但我被那个笑迷惑了,直到他对准我脖颈上的血管咬下去,直到鲜血染红了我白色的睡裙,我才意识到那是致命的危险,不过,我已经不能动弹了,我只能任由滚烫的血溪流般淌出,白松在那些热血的滋润下,脸色渐渐恢复光泽。
那个梦太恐怖,我汗透衣襟被惊醒,全身无力地坐了好久。我告诉自己,只是个梦而已,不要太担心。渴了,床头柜上的瓶装水又正好喝完,我打着赤脚抱着双臂朝厨房走去。
平日里我不进厨房,虽然里面用具齐全,但我们从来不在这里做饭,冰箱几乎只是摆设。但那晚,厨房里有微弱的光,是冰箱门开启后里面的灯光。
我的脚步寂静无声,角落里却有大口吞咽的声音,那么响,像行走沙漠的人发现了一口井。凌晨四点半,是谁?
我并不是胆小的女人,我抄起一把菜刀,小心地挪过去,倘若是个小偷,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一步,两步,三步,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头,凌乱的头发,白得像死人一样的皮肤,高耸的颧骨,嘴角却有着红得鲜艳的一抹。是白松,他正端着一杯红色的液体啜饮,整个人显得疲倦不堪。
“老公,你在喝什么?”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我看不到酒瓶也没闻到酒气。
他显然很吃惊,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却反问我:“你怎么起来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甜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地上有红色的白松的足迹,一直通到浴室里。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径自去了浴室,开了灯。
天!我看见了什么!赤身裸体的欣欣躺在浴缸里,她的两只手都被割了腕,刀口很深,白色的筋脉和红色的皮肉一起翻开来,伤口下是一个大大的瓶子,盛接着伤口里滴落的血。那血不知流淌了多久,很久才落下一滴。
内脏一阵翻江倒海,我再也忍不住干呕了起来。“她为什么会在我们家里?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这个魔鬼!变态!”我失控地冲白松大声吼着,声音在空旷的楼里回荡。
黑暗中的白松冷静得像个魔王:“亲爱的,我有病。”他走过来,酒杯里的血已经被他饮尽,他的眼里似乎恢复了些许光彩。他说:“原谅我不能告诉你究竟是什么病,但请相信,我还是个正常人。”
“可你都已经杀人了,你还说自己是正常人?”我连声音都打着寒战,我看见了他的牙,尖锐的长长的两枚,红得发黑。我惊慌失措地试图躲过他张开的手,他的怀抱。
“相信我,这么做,都只是为了能继续和你在一起。”他的声音柔和无比,依然像他第一次对我示爱时那么柔软,只是散发着血腥气。“不信你来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抽水马桶走去,他要干什么?我不明白,这个晚上给我的刺激已经够大了,我的脑子转不过来。
红色的!我看见了,他的尿竟然是红色的!我一步一个踉跄地走到马桶前,揉了揉眼睛,真的,白松真的病了,整个马桶里的水都被他红色的尿液染红。
“是绝症吗?你为什么瞒着我?我们可以去找最好的医生,我们一定会治好的。”我的心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揪住了一样,疼得厉害。这个从少女时代我就开始深深爱慕的男人,我不想失去他。
白松笑了笑,有些虚弱:“不用担心,亲爱的,我喝过血后就会感觉又充满了力量。”他搂住了我,我没有再拒绝,因为我不能确定他究竟还能给我多少个拥抱,哪怕他的怀抱冰冷,我也闭上眼睛承受。
他说,他喝过她们的血。
她们?是那些在见面会后和他单独会见过的又消失的女孩吗?我曾经以为他只想和她们上床的,原来不是,他只是为了治病,这么想着,我的心好受了些。
那天,我们在第一缕晨曦到来之前相拥回到了床上,我们关严双层的窗帘,整栋楼漆黑得像个巨大的棺材。
厌食症
那个晚上之后,我的脑子明显就乱了起来。在独处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回想起那个夜晚,那些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她们?具体是多少,十个?二十个?
我再也不能沉静地入睡,我开始整夜地失眠,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白松却睡得香甜,睡前他喝过血。
从他断断续续的梦话中,我知道了一些细节:在我曾经睡得香甜不知觉醒的深夜里,他悄无声息地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回来,她被他灌醉了,或者下了药,他把她放进浴缸,剥干净她的衣服,冲干净她的身体,然后像一个真正的吸血鬼那样,俯身吻她的脖子,让血牙刺破她的血管,然后拼命地吮吸……
最后,他会把厨房整理干净,把喝不完的血放进红酒瓶里储存起来,把被榨干最后一滴血的尸体装进大号旅行箱里,开车出去,把箱子扔进废弃发臭的老护城河里。那条肮脏的河,已经十年没有清过底,不会有人发现他的秘密。
我在白松身边越躺越害怕,他已经不是个正常的人了。
可我毕竟爱他啊,他给了我一切,我怎么能在他病的时候离开他?我的内心纠结着,我还在为体重担心。我必须减肥,只有形象更好,才能为白松赚更多的钱,治病是需要花钱的,尤其是这种罕见的病。
我身高176厘米,作为模特,体重应该比50公斤还要少一点才行。有时实在忍不住,我会胡乱吃进去一大堆东西,然后抠着喉咙再吐出来。现在,我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程度,条件反射般,胃拒绝容纳任何东西。
我去看了医生,确诊为神经性厌食症。医生的处方是让我尽量吃东西,还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会把自己活活饿死。
镜子里,我的眼睛暗淡无光,头发也像枯草一样,卸了妆会发现因为缺乏脂肪眼角嘴角生了许多细纹。我不敢告诉医生的是,已经两个月没有来例假了。可为什么该死的秤还是指着“50”,衣橱里的衣服都还是紧。
我歇斯底里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忽然想起来,如果是真的看过病,白松应该也有张处方。
蒙蔽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文件夹,那里面,有着白松所有的秘密。
看过最上面的几份文件和票据后我终于知道了,白松前两任太太的死,都给他带来了八百万的保险金。他用这些钱,去国外做五十万一次的顶级抗衰护理。未免让人唏嘘,他太太的命换来的钱,成了他支付青春的费用。
在文件的最下面,是一张沾染了血渍的处方单,上面的字迹很清晰,太过密集的抗衰疗程影响到了身体,白松患上了卟啉症。
我在网上找到了答案。卟啉症,一种罕见的疾病,患者可能会有红色的骨骼和尿液,还有黑褐色的牙齿。他们只能生活在黑暗中,阳光的照射会引起皮肤溃烂,甚至变形。需要补充血液增加血色素。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该病患者的悲惨命运被怀疑是吸血鬼故事的起源。但是,饮血只是传说中的秘方,并不能真的治愈。
我忽然想起,白松给我也买过保险。该死!
这个家现在看起来疑点重重,最可疑的就是满柜的漂亮衣服,为什么会越穿越小?我在衣帽间疯狂寻找着,企图发现一点端倪。最终发现每一件都有被修改的痕迹,虽然被掩饰得很好,但少许线头暴露了秘密。
我举起那个该死的秤,拼命砸在了地上。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产生巨大的回响,还有散落的零件跳跃了几下才停。秤的残件中有一个不和谐的颜色,指针附近,有个东西在闪光。蹲下来看,是我丢失已久的水晶小胸针,别在指针的弹簧上,被卡住的地方正好是刻度50的方向。秤显然被动过手脚。
衣服和秤都是他的凶器。还有他买来给我吃的“维生素片”,现在看来也可能是让我每夜安睡的秘密,原来他一直都别有用心。
他怎么可能会真的爱我?一个愿意用无数女孩的鲜血填补自己病态的人,一个只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会真心爱我?白松对我的好都是假的!
被蒙蔽的真相唤醒了愤怒,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噬咬爱情
早上十一点半,白松睡得最沉的时刻,我轻手轻脚下了床。
我扯下了楼里所有的窗帘,是的,是扯,短时间内,拉不上了。然后我跑出去,把大门反锁。
刺眼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我在窗外看他像一个真正的吸血鬼那样恐惧地尖叫着躲避光线,他的皮肤上很快就起了一颗颗透明的水泡,耳朵和鼻子像即将融化的蜡烛一样变了形,牙床上只剩下红红的牙根,那尖锐的血牙再也伤害不了任何人了。
我恨恨地想,他没有真爱过我,他只是利用我赚取保险金,他罪有应得。
可是,为什么我会在这明媚的阳光下痛哭失声?
也许,当真爱上一个人时,就赋予了他伤害自己的权利。
也许是因为那利齿的啃噬中既有切肤的疼痛也有奉献的快乐,而人类的灵魂一向是最耽溺在矛盾与迷惑之中。
我的泪落到嘴角,滚烫。爱情就像是白松每夜渴求的鲜血,我却没有长出血牙来狠咬爱情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