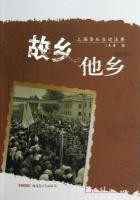土家烧烤
在我的故乡那个土家山寨,木柴除了烧火做饭之外,再就是用于烤火取暖。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备有大大的火屋,他们选择靠墙的一方,用三块长长的条石一围,再用泥土压紧,就便形成了一个距形的“火塘”,我们叫它“火坑”。
土家人的“火坑”,既是全家人生火取暖的地方,也是用于来客烧水泡茶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烧烤”食物的地方。
冬日里,大雪封山,什么事也干不了,全家人就一起围着“火坑”,一边取暖,一边拉着家常,打发寂寞的日子。“火坑”中柴火烧得旺旺的,吊在柴火中央的炊壶“扑哧扑哧”地冒着热气,男人们不时地涮了茶罐,就着新鲜的开水,一遍又一遍地泡着罐罐茶,将一罐浓酽的苦茶喝得有滋有味;女人们坐在靠窗的地方,借着窗外的雪光,不停地做着农忙时遗忘的针线;喜烟的人们不紧不慢地裹好了山烟,将长长的烟锅伸入火中,连火带灰地只一刨,白雾般的浓烟就从口中徐徐地喷了出来……。火小了的时侯,自然是忘不了再添上一两块薪柴。就这样暖暖地坐着聊着,坐困了,聊困了,有茶有烟;坐饿了,聊饿了,“火坑”里有着香喷喷的烧烤。三餐并着两餐开,倒是省去了雪天里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土家“火坑”里的烧烤,大多是一些红苕、洋芋之类的食物,尤其是以红苕为最多。这些山里生产的平凡了不能再平凡的粗粮,倘若要来将它烧烤得有滋有味、有模有样,不论是从食物形状、品种的选择上,还是从烧烤的技法上,都还必须得有一番讲究。烧烤的食物太大、太圆,往往外面烤焦了,里面还是夹生半熟;烧烤的食物若太小,还未等你回过神来,就已变成了焦碳。单从食物的形状来看,自然是以不大不小的条状物为最好。洋芋烧烤过后格外地香,红苕烧烤过后特别地甜。沙坡地的红苕性干,烧烤过后吃起来有着一股栗子般的味道;平地里的红苕水气重,烧烤过后吃起来就象秋天打霜后的柿子一样甜软。同为红苕,就因生长的泥土不同,烧烤出来后,便可吃出两种不同的味道来。山里的烧烤就是这样的一些粗粮,想吃了,只要把孩子往深深的“苕坑”里一放,立马就可以捡上来一筐,现烤现吃,真是方便得很,随意得很。
土家烧烤的火,既不是熊熊燃烧的明火,也不是烧得红彤彤的碳火,而是一种热灰中夹杂着细小木碳的“灰火”。烧烤之前,得先以“火坑”中的火堆为中心刨一个半圆形的沟,然后依次将食物埋入沟中,再用火堆中烧残的灰火加以覆盖,静心等候。待正面熟软后进行打翻,以新的灰火重新加以覆盖,如此几遍,待食物正反两面全部熟软后,便可从灰火里刨起进行食用了。灰火的好处在于即便是误了时间,也不致于将食物烧成焦碳。这样烧烤出来的食物,不仅皮好剥,而且剥掉外皮,里面还有一层焦黄的锅巴,撕掉一块,热气腾腾,送咀里一嚼,喷香喷香!虽然,后来我在城里也吃过街头瓮缸里用煤碳或木碳烧烤出来的诸如红苕之类的食物,可总觉得不及家乡用灰火烧烤出来的食物地道,一想起家乡里用灰火烧烤出的食物来,就时常禁不住要流口水。
当然,土家烧烤的品种也不全是光红苕、洋芋之类,譬如冬腊月里杀了年猪,火屋的房梁上挂着有薰好的香肠,时逢家里的长辈或男人又好喝两口,女人也会拿刀割下两节,放在火里烧烤好了,拿给长辈或男人下酒。香肠的烧烤不同于薯类,必须得先洗净用厚厚的火纸层层裹了,再放入灰火中去烧,直到烧得外层的火纸成灰,里层的火纸焦黄变脆,香肠“汩汩”地冒油,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后,方可刨起食用。自然,烧烤的香肠比起水煮的香肠来,香气要浓郁得多,味道要绵长得多。烧烤香肠万万不可乱翻,翻烂了火纸,染了灰尘,经过水洗之后,其香气和味道可就要大打折扣了。烧烤香肠乱翻为大忌!
因为要烤火取暖,冬天,便成为了土家山寨盛产烧烤的季节。那么夏天呢?
其实,夏天的土家山寨,烧烤也还是有的,只不过换了一种烧烤方式。那就是待山上的包谷灌满了浆,嫩嫩地扳了回来,撕掉外壳,做饭的时候,伸入灶膛,旋转着加以烧烤。烧烤包谷不能性急,急了往往外糊内不熟。必须将包谷与火保持一定距离,眼睛盯着包谷粒一点一点地由乳白变为焦黄,不失时机地加以旋转,来不得丝毫的怠慢。这样烧烤出来的包谷,扭下来丢入口中一嚼,满嘴清香!
火,对于土家人来说,真是个好东西!那些在山外人看来极不起眼的粗粮,经火一烧烤,立马就变成了精致的美味!
土家开放在肚里的花
我说的是紫藤,一种让花鸟画家见了就爱不释手的花。藤干蜿蜒盘桓,遒劲有力,形如巨蟒。藤蔓无拘无束,相互缠绕,汪洋恣肆,不时还有新生的嫩藤探出头脸,在攀附的树枝上一个劲地打着卷。长长的叶柄上,小巧玲珑的藤叶,对称而整齐地一字排开,柔婉而舒展,微风一吹,便如旗般地翻飞招摇。层层叠叠的藤叶掩映之中,淡紫色的花,紫中带蓝,一咕嘟接着一咕嘟垂挂期间,似有无数紫色的风铃,在绿色的窗前轻轻摇响,艳得炫目,美得惊心,让人一见,便顿生喜爱。
这就是紫藤。我山里的老家,那个土家聚居地山野中的一种常见的野生植物。
其实,紫藤只不过是它的学名。而在我山里的老家,或许是因为它天生喜欢攀附缠绕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我老家的人们看物太过实在的缘故,总之,老家的人们总是一直习惯地把那文人眼中雅致的紫藤,形象地俗称为“绞藤”。至于那艳丽的紫藤花,也就理所当然地也被称之为“绞藤花”了。
大凡这世上的植物,只要是可以用来食用的,大多都是以吃根、吃梗、吃叶、吃果为主,吃花的总是极少极少,而善于吃花的人们,便就更是少而又少了。在我山里老家人的眼里,紫藤花,就是这样一种可以用来食用的特殊的花,一种可以开在土家人肚里的花。
虽说,山里的紫藤不在少数,但生得粗壮、且年代久远又长成了一定规模的却并不常见。偏我老家的附近就生有这么一蓬。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时从地上生长出来的蔸干,最粗的就已有人们的小腿那么粗,四下展开的藤蔓,横竖爬满了五棵直径盈尺的大树。那些随意生长的藤条,横着的、竖着的、斜着的、环着的,上下牵扯,左右环绕,密密麻麻将五棵大树连为一体。人需上树,攀着藤条,几下就可一直爬到树顶。小时候,小伙伴相邀一起外出打猪草,总爱偷跑到那紫藤树上去疯玩一番。
对于小孩子们来说,那粗壮而柔软的紫藤,正是大自然赐予山里孩子的天然秋千呢!
每年三四月,紫藤花开,藤蔓间挂满了成串成串的紫色花团,远远望去,灿若云霞。而这时正是孩子们最为高兴的时节,大伙全都一个个有理由打着去采“绞藤花”的旗号,提着提篮爬到那紫藤树上,一边采花,一边嬉闹。且一玩就是大半天,不见大人催叫绝不回家。
那些艳丽的紫藤花,被采回家里之后,母亲先是将花放入一个大木盆里,用清水细细地淘了,然后便架起大火,将满锅的开水烧得直至冒出鸡蛋大的气泡,再才将满筲箕的紫藤花,利落地往锅里一倒。看着那紫藤花在锅里旋转着打着翻,母亲只是拿着锅铲在锅里上下左右撩拨了几下,随后就又赶紧用筲箕将那逐渐变怏的花,快速地给捞了起来。那花一起锅,屋子的里里外外,便顿时就弥漫起一股好闻的紫藤花的清香。
我不知道,北方人吃榆钱是否也有这一吃法。那些经开水煮过的紫藤花,被滤干了水汽,后来被摊在一个宽大的簸箕里,母亲端出包谷面来,将面和花均匀地搅合在一起,再撒上盐,拌上作料,然后就开始一锅铲一锅铲地往一个硕大的瓦坛里倒。一路压,一路装。末了,还要在坛里塞上几层翠绿的梧桐叶和几把枯黄的稻草,最后才将瓦坛倒扑在一个盛了水的瓦钵上。待过了些时日,坛子里的紫藤花已微微发酸,再掏出来,用油或夹着腊肉炒了,吃起来喷香喷香!这便就是土家人独具一格的特色菜——“鲊绞藤花”。据说,食用紫藤花,还可以用来解毒、治疗腹泻呢!
紫藤,文人喜欢它,是因为它艳丽而极富情致!
紫藤,土家人喜欢它,却是因为它质朴而又实在!
土家罐罐茶
中国人的民族特征是崇尚自然、朴实谦和、不重形式。体现在饮茶上亦是如此,而山里老家的土家罐罐茶就更是如此了,泡饮起来总是显得是那么地自然与朴实。不像日本茶道,饮上一口茶,还需具有那么严格的仪式,带有那么浓厚的宗教色彩。
土家族是好客的民族。即便是荒山野岭,有人打门前路过,不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相互一招呼,主人便都会热情地挽留客人歇上一会,喝了茶后再走。
土家人饮茶,说不讲究也真不算讲究,瓷杯瓦罐的,普普通通,甚至有的茶罐盖还是一只断柄的铜勺,或一只破损的碗底,就论其茶具,说讲究也还真的讲究不到那儿去;但倘若要说完全不讲究那也是假,一罐浓酽的罐罐茶泡出来,要让它香气扑鼻,或多或少还是有着它自己那么一点讲究的。
或许是因为山里的寒气太重,土家人再窄的房屋也都会有宽大的火屋。尤其是冬天,客人一来,迎进火屋,然后架起熊熊大火,用一把烧得黢黑的铜炊壶打来清澈的山泉,往火塘中央特制的铁钩上一挂,烧水泡茶的架势一拉开,茶还未喝,客人的心里倒就先暖和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