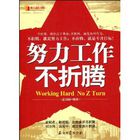最初的几天隔三差五地有人来,母亲就让我在家待着,一边和母亲唠叨家事,一边等人来。母亲说近几年家里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奶奶去世的时候,有很多同村人找咱家麻烦,我的那个大伯外表像人,其实是鬼,借办丧事故意刁难;奶奶98年7月去世,因为坟地要路过很多人的玉米地,我的一位大伯坚持要让我父亲挨门挨户地给人家说情、下跪;最多的说起我们家和邻居杨桂新家的宅基地冲突,持续多年,杨桂新是我爷爷的亲侄子,为了房基地的事情,有两次趁无人时候殴打我母亲,还有一次伙同其两个儿子,趁我小弟挑水没有防备之际突然袭击,致使小弟身体受伤,精神受到一定刺激;至今还吵闹不休,无理取闹。母亲还说,队里分得几棵白杨树和苹果树,竟然有人将硫酸涂在树干,埋在树根。这些很小的事情,却使我异常愤怒。这不是第一次听到。早在我未出生之前,这种窝里斗就异常频繁。仿佛是这个村庄的一种传统。我出生乃至稍明世事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和经历过了。我不能无视父母的屈辱,但我又是无力的。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村庄的对手。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因此,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人是恶的”的思想就很深刻地嵌入了我的骨头和灵魂。
该做饭了,妻子和母亲一起动手。手虽然在忙活着,但母亲的嘴却不闲。过一会儿就说,那个谁谁谁还没来看你呢。我说,不来才好呢!为什么要他们来看?妻子从我的话中听出了我对这个村庄的厌恶,随口说了一句这地方人真坏!我说我早就受够了,要不是父母亲和兄弟还在这儿生存,我一辈子都不愿回来。不是东家打西家,兄弟骂哥哥,就是张三李四因为一株麦苗,一块石头、一块干地皮吵架,实在不可开交甩开膀子就打。穷得叮当响,就知道窝里斗。正说着,一位还算不错的堂哥来了,我招呼着坐下,递上烟卷,点着,漫无边际地重复那些说了几十遍的套话。
几天后的下午,没事了,就一个人转过自己家的坡岭,到爷爷奶奶和我们居住过的旧村庄里走走,看望一下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村庄还是原来的模样,层叠的石板沿坡而上,两边错落的石头房屋大都衰败了,黑黑屋檐上悬着一条条凝成绳状的灰垢。偶尔有几声鸡鸣,几声老年人喊打野狗的苍白吆喝声。走进一家家门,黑黑的屋子让人压抑。
与坐在炕边上的老人攀谈,都说,哎呀平子,好几年不见回来了,这会儿在部队上干啥呢?我照实告诉他们。老人会唉的一声,说你那个大伯不在(去世)了,是前年春天的事儿;那个大娘死的可好过了,没打针也没吃药,睡着觉儿就过去了……下一个该轮到谁谁了,再一个就是谁谁,再下一个就是俺了。好像老人们的死都是按照一定次序来的似的。我不好说些什么,只是告慰老人您多保重身体,有病就要花钱去治,不要硬挺着。老人会再唉的一声说,哪儿有钱呢?打盐的钱都上愁!
离开一家,到另一家,路过爷爷奶奶居住过的院子,门板还是童年的那幅,台阶还是我不知踩过多少次的那些,如今他们都静静地躺在那里,身边长满茅草,身上覆着厚厚的枯叶和泥土。春夏茂盛的野草只留下躯干,在院子回旋的风中摇头晃脑。因为久无人居住,使我不自觉地感到阴森。记得童年常在这小道上呼啸往来,嬉闹打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所有哭声和笑声几乎都遗落在这里了,或许就在那稀疏的石头墙缝里,只是时间太久远了,它们喑哑无声,已经沉淀成石头的一部分了。
3.我们的早晨
被冬天稀释了的阳光爬上窗棂,一夜北风此刻消停,去年的丝瓜藤蔓悬在房檐,干枯得纹丝不动。院子里的苹果树裸着一身黑色。母亲将剥了几层皮的白菜放在刀板上切成条状,洗了,又随手抄在只放了一点油的小锅里,一声爆响,饱含水分的白菜就把滚油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随着熊熊燃烧的柴禾,水煮白菜的清淡味道在我们家飘起。
早饭是雷打不动的小米粥就土豆、白菜,小米是自己家种的,白菜土豆也是自己家种的——这我早就熟悉,它们的味道一生我都记得。这次回家,我总是嫌母亲炒土豆、白菜时放油太少,吃起来没有味道。母亲说:俺小那会儿连白菜、土豆都很少见,有的糠窝头吃就很不错了。省油不就是省钱吗?以后还要给你和继平(弟弟的名字)盖房子,不省怎么行?
我对母亲说:省省省,身体重要还是钱重要?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俺就这样过来了,吃好吃坏都不要紧,只要吃饱就行。
2000年后,家里状况有些好转,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不用再吃掺了玉米面的面条儿和馒头了。我和妻子回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让小弟骑上车子,到10多华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买回1斤青椒、2斤猪肉,12斤包菜和3斤豆腐。
母亲说,你和媳妇难得回家一次,家里没有什么好吃,咱奢侈点儿就奢侈点儿吧。你媳妇又怀了孩子,大人吃好孩子才能长好。别像你刚生下时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一个月从头到脚蜕了三层皮。
我说我在外边什么都吃过,主要是你和俺爹,恁都上了年纪,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母亲说:俺不委屈自己啊,这不,玉米面都不吃了。去年天旱,种的土豆不长,到8月是才收了不到两篮子的土豆,昨天吃的那土豆是从你大姨家背来的,买就买点儿吧,再说也快过年了。
房后的斜坡上,堆着朽干了的粗大木棒,父亲一根根掀起来,扔到厨房门上。木棒上沾满了泥土,有的长出了白白的菌苔,像扇子一般,层层叠叠的。有的多半被湿土掩埋了很久,经父亲一掀一扔,泥土干脆地掉了。
父亲从斜坡上下来,走在屋门,伸手拿起斧头,走到那堆粗大木棒跟前,找一个厚而平坦的木墩子,开始一块块儿解劈。——劈柴有些讲究。在家时,我学过这门手艺,当然跟着父亲。起初,每根木棒的纹路都纵横交错,不知道先从哪儿下手。父亲说,这还要看是什么木头,如果是柿木,朽了就成了软绵绵的渣子了,斧子劈哪里都可以。枣木、棌木和栗木很硬,一般舍不得用做柴烧,你看咱家的面板就是枣木做的,几十年不坏,即使刀剁万遍,也还是光光的。
松木有油,湿着的时候很好劈,最好先用锯子锯成一段儿一段儿的,往地上一墩,斧头一劈,它们就开了。最难劈的就是有长节子的木棒了,纹理扭曲,劈几斧子也还是分不开。
渐渐地,阳光有了一些暖意,母亲催促弟媳妇把孩子夜里尿湿的尿布拿出来晾晒,该洗的放在铁皮做的大盆里,先用水泡上,洗了晾了,孩子很快就可以用了。弟媳妇站起身来,把怀里的小侄女儿递给弟弟,转身,甩打着后跟儿磨得失去平衡的皮鞋,走下母亲院子,到自个儿家里收拾去了。
我怀孕的妻子走过来,母亲说,没事儿就多睡一会儿。妻子说,早上空气好,勤走动着孩子好生,说着话儿,抬步走到母亲屋里,舀水洗漱后,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就到院外面的土路上溜达去了。
母亲对我说,你快去跟着,咱这里路陡,千万不要摔了。
我应声而去。听到我的脚步声,妻子扭过身子,看着我说:这早晨真安静。
我看到,向阳地方的草儿开始发芽了,灰雀就像擦着头顶在飞。
父亲走到石头砌起的羊圈门口,将两只绵羊牵出来,浑身洁白的羊一跑出圈门,就撒开四踢,冲向院子。母亲说,饭好了,吃饭吧。弟弟走进房门,搬出小桌子,放在屋子的空地上,又从碗橱里取出6个瓷碗,送到母亲面前。
4.回家
又三年过去了。2004年冬天,我和妻子带着三岁的儿子杨锐东,再次从巴丹吉林沙漠出发,回南太行乡村老家。再从北京上车,出了京都,车窗外的冬麦显得安静,浅绿的身子伏在黄土上面。儿子在车厢里胡乱走动,那么多人,他并不陌生。我跟在后面,像一个护卫。妻子和对面的一位女士聊天。一站,又一站。车过邢台,我把行礼提前放在车厢门口,妻子给儿子穿好衣服。车门打开的瞬间,我就嗅到了浓重的煤渣、灰尘、汽油和铁屑气息。它们过熟悉了,在家乡的很长时间,我就被它们浸润、包围、容纳。即使离开了多年,我依旧能够从这种气息当中,嗅出最为熟稔的部分。
这是冀南小城沙河,它的天空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灰暗。站在人迹稀少的月台上,看见西边隐约的山峦——我的家就在它们之间,在它们最为偏远的一处:微渺、卑琐。村庄的周围,大片树木与蒿草里面,掺杂着石头、腐骨、炊烟,以及人、牲畜的叫喊。
夜晚到家,放下东西,刚说了几句话,母亲说烧一锅开水,让我和妻子洗脚。灶台在院子东墙根,由细木头支起,上面覆了一层黄泥和油毡。母亲从一边的柴堆里抱柴,灯光从窗玻璃投射出来,干硬的院子地面上还有着风吹的痕迹。对面的村庄也在忙碌,我听见了他们孩子的哭、大人的喊。
屋里灯光昏黄,面孔模糊。煤球火炉上,暗红色的米粥已经熟了。我们的儿子一刻不闲,在他祖父祖母的炕上,手里拿着一颗啃食半天的苹果。我出门,替娘填柴烧火。柴火很旺,不断发出噼噼啵啵的响声,火苗似乎一张张舌头,从我脸颊一侧,呼呼向上。不一会儿,水在里面就开始骚动了,它们咝咝响着。母亲说,再放两根干柴就要开了。我嗯了一声,找了一根两米长的干苹果树枝,握住两端,放在膝盖上,像拉弓一样,把它折断。
母亲、弟弟和我们一家三口,围坐着吃饭。摆在面前的是:土豆丝、炒白菜、切开的火腿、鸡蛋、馒头和一小碟咸菜。儿子不安生,和弟弟的小女儿甜甜一起,争抢印花的木碗,或因为一颗煮熟的豆子,用勺子和筷子相互击打。母亲放下碗筷,替我们看管。我知道母亲不能吃凉了的饭菜,就说,你吃饭,我看着他们。母亲说,我看我看,一会儿就好了。我坚持,母亲也坚持。我只好几口吃掉馒头,喝完米汤,替母亲看两个孩子,让母亲吃饭。
收拾了碗筷,窗外暮色凝重。对面的村庄相继进入睡眠,灯光接连熄灭。
我走到院墙东边,掀开锅盖,一股热烈的蒸汽蓬勃而起。灶里的火焰明明灭灭,舀了开水,端了盆子,从一边小路上,走到我十二岁那年父母亲就给我盖好的房子里,仅仅1分钟或更短时间,滚烫的开水竟然不再烫手了,它们的热量已经在短暂的途中,被冬天的冷没收了。
再回到母亲房间,儿子和侄女儿仍在嬉闹,穿着脏鞋,在爷爷奶奶的炕上奔跑。弟媳刷碗筷,母亲坐在炕沿。
妻子坐在母亲身边,拿着一本黑皮包装的《新旧约全书》,一边念着诗篇,一边停下来给母亲讲解。她说到摩西、撒旦、耶路撒冷、海地、埃及、100只羊、约伯的花园。弟弟坐在凳子上,正在修一把要很久时间才能打开的铜锁。他的手指足有8寸长,满是皱纹和裂口。
我在桌子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桌子靠墙的一面是镜子:一只柳条篮子里竖着一丛带着绿叶的红花,一边写着“万寿无疆”。再向上,是一张山水画:青山、江水、柳枝、桃花和在空中静止飞行的鸟儿。再一张:牧羊的耶稣手持权杖,在河边的青草上,以远处的黄色山脉为背景,借助下面的一行字说:“义人哪!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一节)。基督画像左侧,是镜框,里面存放着2岁、挎枪、扛摄像机、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列兵和抱着儿子、军官的我;19、33、48、55岁的母亲,还有坐在我们中间的父亲、石家庄和少林寺的弟弟、满月时的儿子和侄女儿;猝亡的大舅和祖父;因肿瘤而去的奶奶;正襟危坐的大姨、站在一边的小姨……无色的镜面上好像有灰,极为细腻的,落了一层。
过往的都是灰尘。我突然感叹。1小时后,两个孩子睡了,母亲把他们安放在被窝里,睡姿舒坦。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母亲站起身来,倒开水洗手,又到里屋端来一只面盆,放在煤火台上。
我说明天再和吧。母亲说,明早就没馒头吃了。说着,就倒了面粉,掺了水,和起面来。
夜色愈加深重,外面有风,呼啦拉地吹过房顶和院落。到处都是风和草木摩擦的声音。整个村庄在夜晚深陷。一个人在寂寥的院落中站一会儿,四面的寒冷匍匐而来。相邻的鸡们、羊们已然睡熟。
回到房间,母亲已和好了面,洗了手,在火苗上烤。大家都有些困了,妻子困了,蜷缩在母亲的炕上睡着了。弟媳抱着睡醒的侄女儿,在膝盖上拍。——我抓过母亲的手,看到一对修长的手掌,上面爬满了皱纹、黑皮、白茧、冻伤和刀伤。我叹了口气。儿子在梦中嘬了嘬嘴巴,小嘴吧嗒吧嗒,在静静的乡村深夜,格外响亮。
母亲说,不早了,睡吧。我们说好。妻子抱了儿子,我提了水壶。出门是黑,一堵墙似的。风依旧在吹,嗦嗦的树叶贴着地面疾飞。回到自己的房间,热热的火炉吐着蓝色的火苗,在我们房间,在乡村深夜,安静着,把自己点燃。
5.旧居的温暖
清晨,朝阳从门框上方的窗棂照进来,淡红色的。墙上的花草年画、美女头像、以及悬悬欲掉的黑色灰尘纹丝不动。妻子和儿子仍在熟睡,他们呼吸均匀、甜蜜、节奏。我将手臂伸出被窝,寒冷迅速围困。我打了一个哆嗦,穿好衣服。就我又看见了那些搁置多年的家具:松木花纹的、浅黄色的家具,有的已经拱翘和弯曲了,但并不影响整体。它们呆在那里,在长久的安静、白天偶尔的日光和夜晚奔窜的鼠群之间,以及浮尘、蛛网和安静的覆盖下,已经有15年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