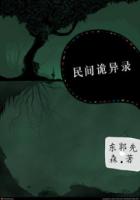父亲说:“九黎族没有英雄,尤族也没有,冥水两岸,没有英雄。英雄在一个死去的世界中,英雄在不冥河上……”
“那尤呢?”我问。
“尤族的胜利靠的是被魔法召唤的蛟蝶,如今的世道,谁拥有了蛟蝶,谁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一提起尤族,我的心里就难过起来。父亲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父亲说一个部落的衰亡,自有它的过程和必然,九黎族出了这么个窝囊的头人,它的灭忘也是情理之中。生死本无界定,生是死之初,死亦是生之初,九黎族的昌盛,是数以万计的白骨堆成,可现在,九黎族到了末日,那些死去的生命,那些不冥河上飘浮的灵光,已经没了价值。同样,尤族也逃不过这个宿命,尤的模样不禁使父亲想起早已做古的先人,冥冥之中,父亲觉得尤的前世是九黎族的某位先辈,因为唤醒蛟蝶所需的魔法源自九黎族,且需修行千年才能完成,难道——紫衣人不过是九黎族的另一个影子?
如果这是真的,那父亲的生命,似乎已走到了尽头。那我的宿命在哪儿?石穴中?冥水上?黑暗来临,冷风从岩石的每一道缝隙间吹进来,我抖索着身子,抵抗着无眠的折磨。
“来,我教你一个法子,可以不冷。”父亲从岩石上跳下来,手握着剑。
“唉,看来,我来日也不多了……这是一套剑法,叫‘青冥三式’,你学会了它,再带上这把青铜剑,大概可以逃出这个石窟……我以前教过你一些功法心得,本着你良好的武功天份,用不了几天你就能熟练于心的,至于以后嘛,只能听命于上苍了……”
我点点头。
“记着,我死后,我的魂魄就游荡于冥水两岸,只有遇到你的母亲,我才会重生……”
“母亲?”
“对,她是龙蝶的后裔,你也是,你的魂魄,同样会使一个亡灵重生的,其实我很想化成一只龙蝶,可是……可这是不可能的。”
“龙蝶?”
“是啊,传说是上古时一位至情至善的女巫徇情而生的。或许,它是惟一可以战胜蛟蝶的神物……假如它能让所有死去的将士重生,那么,九黎族就得救了。”
此时,我想起了羽,我死后的化身,能使她重生于冥水之畔吗?
“那,假如羽死后,也……”
“传说中的龙蝶是雌雄同体的,可能后来有了变化,爸爸没有亲眼见过,但据我所知,就像你和羽,同属蝶宗,只要找到另一半,就可以重生,否则,只能是永远的一半,一个重生了,然后让另一半重生,如此反复,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那它是怎样……”
“儿子,即使我再活上千年,也只能依据我的经历来推测死后的世界,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知晓……”
父亲说完,一个团身,剑气直射,这是“青冥三式”的第一式:羽化重生。
头人的水狱距石穴不过二十步之遥,由两个兵士把守,狱前燃着两只火把。当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钻心的嚎叫声惊醒,同时,我听到父亲平静的呼吸声,父亲不以为然的姿态让我有了某种依靠,可头人的声音绝非一般的疼痛所致,随后,嚎声停止了,接着,我听到头人喊:“妈呀——妈呀——饶了我吧——”
第二天是个晴天。
阳光透过石窗,在岩壁上留下一块块方形的光斑,我拿起青铜剑,让剑锋划过光柱,折射的反光在寂寞中点缀着涂满了血迹的石壁。
“头人快不行了。”父亲突然说。
“怎么了?”我放下长剑,坐到父亲身边。
“一会你就知道了。”
果不其然,太阳当头的光景,头人被带了出来,他的下身裸露着,从脚掌到小腹趴满了一种类似蚕尸状的东西。
“是九尾虫,”父亲说,“露在外面的是虫的尾巴,虫的身子钻在头人的骨髓里,它们吸干他的血,吞食他的皮肉,最后,只剩下一点毛发和牙齿,尤可真够狠的,居然使用这种方法……”
经过石穴时,头人看到了父亲,他猛地扑到门边,哭喊道:“巫师救我!巫师救我!我错了……我知道……救我……救……”两个士兵走上来拽他,我听到哧的一声,头人的衣袖被扯掉了。“瓦解了头人的意志,九黎族就完全屈服了,尤是做给我们看的。”父亲说。
不久,我和父亲也被带了出去。所有九黎族的俘虏中,只有我和我父亲的身体是干躁的,许多老臣和女人湿淋淋地走着,表情痛苦,可这痛苦却隐藏在一副漠然的躯壳里。我和他们相遇时,他们的目光并不与我相对,而是躲到一边,躲到秋色绵绵的山谷里。冷风吹来,荒草一个劲地舞着,女人的裙带和男人的衣袖顺着风的方向,组成一幅幅美丽的“归山岩画”。他们蜿蜒而上,他们绷紧着身体,他们的肉里,九尾虫恶毒的吸嗜耗尽了有限的元气。他们完全成了一具具麻木而凄惨的空壳。
村寨前,八具女人的尸体仍挂在那儿,它们屈辱地耷拉着,在阳光下诉说着九黎族末日的辉煌。
尤悠然自得地走到头人面前。
“怎么样,水里舒服吗?”尤笑着问。
头人沉默了一会,突然,身体轰然跪倒,抱着尤的腿说:“你放过我吧,九黎族愿意臣服于您……”
头人哆嗦着嘴唇,不停扭动着捆在背上的双臂。
“他们呢?”尤指了指俘虏们。
“他们?他们随你处置!”
尤不屑地笑了几声。
“看看你九黎族的女人吧——”在尤的暗示下,士兵从人堆里拉出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任由男人剥去衣裳,她木然立着,面如死灰。少女的裸体逼现出来,她的****在冷风里黯然无光,腿间莫明其妙地附着一团暗黄色的粘液。同族的男人们都垂下头,沉默的风里我抬起头,那一团恶心的粘物正在缓慢地蠕动着。
“被‘水淫’之术侵伤的人,不会再有生育能力,而男人嘛,你们的小宝贝从此要成为回忆了……”
尤族人一阵放纵的狂笑。
“九黎族不会有后代了!”尤也加入狂笑之中。
此时,我问父亲:“羽呢?”
而尤正朝我和父亲走来。尤笑着问:“巫师,我说的对吗?”
父亲默然不语。我知道,一个氏族的命运不是靠我或是我的父亲能够拯救的,一个生灵被另一个生灵吃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取代,一个部落被另一个部落吞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可当我站在那个注定要被吞掉的一方时,内心还是被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碾压着。
我发现,今天紫衣人没来。
我的羽也不在。
我觉得很冷。阳光下,这是一种异样的寒冷。冥水的呜咽,我听不到了。而羽和我的喃喃低语,始终在耳边呤唱。我想着我的羽。她逝去的体温,无时无刻不在攫走我的温热。
第三天上午,一场阴雨再次降临山谷。父亲似乎困倦了,歪在一块岩石上,眼睛半睁半闭,父亲冥想时就这个样子。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另有些伤感的语调缠绕着我。在我的生命中,父亲的形象始终占据我半个脑海,可现在,没有了,父亲成了一个失落的符号。
不时从穴顶洒落的石粉干扰着我练剑时的情绪,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一股无名的力量压迫着我,我的目光也如那石粉一般,飘扬而失去定向了。
“看着它,数到尺瑶山倒塌的时候,我会重生……”羽最后说,眼里已没了泪水。
尺瑶山的石缝间有数不清的蝶巢,它会倒塌吗?我坐在篝火旁边,一颗颗数着石珠,想着我的羽。现在,东方已露出一抹亮光,已经五百年了,羽化成的一只龙蝶,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得到?
那天,羽离开我不久便跳下山崖,她的素服和泪痕,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美丽。此后的四天,雨水一直未停,而我也沉沦在往事的回忆中。石穴外,那些窒闷的气息,让我在崩溃中体验着崩溃般的绝望。啊,羽的飘落,和这雨季一般绵长无期吗?
紫衣人向我们走来时,是第八天的清晨。
背阴的石壁上,开出了一朵雪白的刺心花。我将它摘下来,咬在嘴里,一边挽着父亲,忧郁地望着那块紫布飘然而至。紫衣人来到的那一刻,父亲佯装病倒,他干裂的嘴唇喃喃说道:“我……我……答应你……”
紫衣人哈哈大笑,命令士兵移开石锁。
我知道,自由的日子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