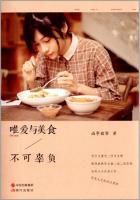小时候,我最关心的其实是猪的膀胱。在那个年月,猪膀胱不亚于现在的气球。屠夫总是对我特别恩惠,他剖开猪肚,取出猪内脏,就把完整的猪膀胱交给我。我将它洗干净后,拿出一根吸管,把猪膀胱像吹气球一样吹起来,然后和几个小伙伴一边拍一边跑。那时年少,一个猪膀胱便能让我们乐上一个上午。
最热闹的是中午,母亲把亲朋好友都请到了家里。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哪户人家杀猪,都要叫上亲朋好友好好地吃一顿。一整个上午,她都在为午饭而忙碌,她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紧紧地围着灶头转,她要用新鲜的猪肉做成各式各样的菜。
吃饭的时候,父亲频频地给屠夫敬酒。屠夫总是借着酒劲说一些自己的“丰功伟绩”,然后一群人笑成一团。他们的笑声荡漾在午后的阳光里,成为我经久不息的回忆。
吃完饭,母亲就把新鲜的猪肉腌起来,等到阳光好的时候,再拿出来挂晒。此时,已经是腊月中旬,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最初的珍惜和慎重
男孩子的年,总是和鞭炮绑在一起。腊月下旬,学校已经放假,长达半年的约束终于告一段落。不管成绩结果怎样,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脑子里不再有学校,不再有老师,也不再有课程。我们开始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各种各样的游戏。
过年的时候,鞭炮最受欢迎。我们拿着父母给的零用钱,频繁地出入商店。那些日子,鞭炮声就好像我们的影子,我们走过哪里,鞭炮声就响到哪里,街上、小河边、谷场上,到处是鞭炮声,到处是我们的欢笑。
儿时的我们,总是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玩鞭炮。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拿几个塑料瓶,到山坡上玩游击战。一队是“解放军”,另一队是“日本兵”。我们把鞭炮装进塑料瓶,把塑料瓶当成手榴弹,纷纷朝“敌营”扔去。鞭炮一爆炸,瓶子就成了绽放在空中的花朵。在一阵又一阵的惊叫声里,我们笑靥如花。
或者从家里拿来一根长长的铁管,把铁管插在斜坡上。此时,每个孩子都像是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鞭炮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我们把点燃的鞭炮扔进铁管里,然后迅速卧倒。随着沉闷的爆炸声,铁管口便冒出许多青烟,那场景像极了扔炮弹。
很快,我们就不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了。我们去商店里买来更大的鞭炮,相对来说,这种鞭炮要有威力得多,声音也响亮得多。我们一点燃鞭炮,就把它往铁管里扔。“砰”的一声,铁管口烟雾弥漫,空中纸屑飞扬。
那些年的寒假,山坡成了我们的后花园。若是不幸碰上几个大人,挨骂是在所难免的。如果碰上父母,那就远远不是挨骂那么简单了,屁股上多多少少得挨几下。尽管这样,我们却总是乐此不疲,游戏带给我们的刺激远远赛过父母的忠告和打骂。
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光。一来,大人们忙着过年,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二来,他们不想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打骂孩子。于是,我们就更“胆大包天”了。有时,大人也童心未泯,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这时候,我们的热情便格外高涨。
零花钱数量有限,很快就花完,实在没钱了,我们就跟在大人后面捡鞭炮,或者厚着脸皮向小伙伴们要。这时,我们分外珍惜手中的鞭炮,往往会想出最好玩的方法,才舍得让手中的鞭炮炸掉。现在想起来,这便是我们最初的珍惜和慎重。
年是一条绳子
年是一条绳子,把散落在各省各市的人往家里拢。那些匆忙在车站的脚步,奔走在月台的身影,无不受了年的召唤。为此,我们不惜几百人挤一个车厢,不惜凌晨起来排队,不惜带了被子在车站过夜。
故乡的一切都令我觉得那么亲切。故乡就像母亲,即使我经年不见,看到她的瞬间也不会有任何陌生。故乡曲折的小径,参差不齐的房子,错综复杂的高压线,都让我觉得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
离年越来越近,出门在外的人差不多都回家了。归来的人群让平时空旷的村庄显得充实和丰满。在小径上行走的人们,一如村庄奔腾的血液。
人们开始坐在操场上聊天、打麻将、打扑克。那一刻,熟悉的家乡话在我们耳边忙忙碌碌地穿梭着。我们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又那么心无城府,又那样俏皮可爱。在外打拼的日子,我们学会了伪装,学会了奉承,我们甚至忘记了怎样微笑,又怎么有机会那么心无城府,那么轻松俏皮。
在外忙碌的日子里,我们把家乡、亲朋好友都最小化在心里。然而过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切重新放大。我们想起了远方的朋友,想起了好久没有联系的亲戚。我们拜访每一个亲戚,每一位朋友。我们彼此倾诉一年里的工作、生活、情感。直到一年的最后,我们才了解彼此在一年里发生的事。而下一次再见面再倾诉,或许是下一次过年了。如果没有年,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彼此远去,到最后形同陌路。
我们和许多人吃饭,和许多人聊天,然后得知他们最近一年的得与失,好与坏。我们的心又渐渐靠近。
难忘元宵那片烛光
一直觉得,元宵是春节之后的另一个高潮。春节过后,人们开始走亲访友,或者外出工作,甚至开始忙于农活,过年的喜庆渐渐消散。然而,元宵的到来,让人们重拾喜庆的氛围。
对我来说,最兴奋的事就是挂灯笼。我家乡所在的南方,流行元宵节挂灯笼。至今,我依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热衷于挂灯笼,那天大早上从睡梦中醒来,一睁开眼,我便一心期待着,一刻不曾踏实。
因为心里有了期盼,所以元宵节的上午与下午对我来说尤其漫长。
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心简直快提到了嗓子眼,我囫囵地吞下晚饭,便在门口等待着,盼着母亲早点下令。
终于,母亲拎着两只灯笼向我走来了。我忙抢过灯笼,点燃早已准备好的两根蜡烛。然后,我从桌子旁搬来凳子,将灯笼高高挂在门口。
每当这时,母亲总会说:“呀,兔崽子会挂灯笼了,今年必定红红火火呀。”我简直乐开了怀。我终于明白,原来自己一天所期盼的,就是母亲的这句赞扬。
灯笼挂上后,家门口便全是红红的光晕,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火红的氛围。我突然发现,门口的挂花树、石头全被红光笼罩了。少时,我总这么想,要是一年到头都有这样的场景,该多好。
挂好自家的灯后,最重要的就是去庙里点蜡烛。那是一件盛事,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参加。路上全是人,他们无一不拿着香烛,满脸虔诚。我跟在母亲身后,几乎被人流推着走。如果碰上晴朗的夜晚,月光已洒满整个村子。走在路上的人,都被月光所笼罩。人们顶着月亮的光辉,熙熙攘攘地往庙里走。多年以后,那场景依然如同雕刻般印在我的脑海里。
等我到达的时候,庙里已经满是红光。在烛光的映衬下,每个人都红光满面,如同醉了酒的汉子。
我们点燃蜡烛,朝拜之后,便开始默默祈祷。
回来的路上,人们的脸上不再那么庄重。他们互拉家常,也有的开开玩笑,其乐融融。假若月光清朗,人们还会在户外的石凳上坐下,就着满村的红光促膝长谈。我总觉得,那是一次心灵交流的盛会。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时针常常已经指向九点。我上床入睡,灯笼的光芒却常常不期然地进入我的梦乡。
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依然难以忘怀那片烛光。它曾那样丰盈了我的童年,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呵护着我孤寂的心灵。
一圈又一圈盘旋的长龙
元宵真正的重头戏是迎龙灯,村里的能工巧匠已经摆开了阵势。他们选择了宽阔的场子,趁着慵懒的阳光,开始麻利地编织灯笼,或紧张忙碌,或吞云吐雾,或满脸正经,或嬉皮笑脸。但不管怎样,场子里的灯笼越来越多了。
这一切都是元宵节的铺垫。正月十五的晚上,全村人兴奋异常,人们早早地装好了灯笼,匆匆扒完晚饭,便急不可耐地到场子上集合。
不消一会儿,灯笼已经全部连接起来了。然后,人们麻利地插上蜡烛,迅速地点上。霎时候,一条火红的长龙呈现在场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与此同时,鞭炮声大作,场子上烟雾弥漫,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长龙缓缓地出发了。
我们一群小孩子跟在长龙后面,肩上扛着小小的灯笼。那种的心情不亚于参军入伍,只要身在队伍中,就感觉有了归属。一群人打打闹闹,开心地唱歌,一起对那些队伍之外的小朋友挤眉弄眼。
长龙上路了,公路上开始充斥着红光,路边的住户早已准备好鞭炮。龙头一到,鞭炮声就大作,一时间,空中烟雾弥漫,我们仿佛走进仙境里。
走了许久的公路,终于到了一块平整的地方,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我明白,他们要开始舞龙了。等我抬头看时,龙头已经快速飞奔起来,后面的也紧跟着旋转起来。此时,我们的眼前一片火红。过一会儿再细看,这条长龙已经开始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红色越来越晃眼,长龙舞得越来越快。到最后,有些人简直已经被甩得飞起来,一阵浩浩荡荡的鞭炮声和惊呼声过后,人们终于停止了奔跑。
到这个时候,迎灯笼的活动已经进行到一半,人们卸下肩上的家什,开始养精蓄锐。因为,等着他们的,是挨家挨户地转悠。人们开始换蜡烛,或者趁机吃点东西。我们这群孩子,也从激动中抽出身来到处撒野。
大家休息片刻,重新走进队伍。接着,我们开始挨家挨户地转。所到之处,鞭炮声不绝于耳。我只感觉到自己走进了一片烟海,大人们的背影和小伙伴们的笑脸都开始迷糊起来。
半夜,月亮高悬。我们终于回到村里的场子上,等着我们的,是丰盛的点心。末了,我们在月光下散去,各回各家,各入各梦。
散落在林荫道上的乡情
当季节的轮回再次停留在夏天,当岁月的磨盘再次旋转到端午,我心里那些遥远的回忆又慢慢升腾起来。
那时,生活并不是很宽裕,可是母亲从来不会因此而冷落了端午。
早很多天前,她就从山上采来粽叶,把青绿的粽叶放在阳光下晾晒。快到端午时,母亲把粽叶放在开水里煮泡,那青绿的粽叶转眼间就变成黄色的了。到端午的前些天,她便开始忙碌地包粽子。因为家里亲戚比较多,所以母亲往往要多包一些。
我的家乡流行“走端午”,就是在端午的前几天,人们拿着自家包的粽子走亲访友。母亲包好粽子后,“走端午”的事情就由我和父亲做。在头一天晚上,母亲已经用一个竹编的篮子装好粽子。第二天一早,我和父亲便趁着晨曦上路。
我家的亲朋好友分布很广,有些村子能坐车直接到达,有些村子则要走很多小路才能到,我更喜欢去那些需要走路才能到达的村子。
上午时分,我和父亲一起钻入林荫道里。路上,“走端午”的人很多,熙熙攘攘,有的用扁担挑着,有的用手拎,还有的用肩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