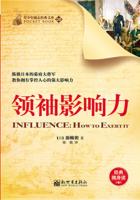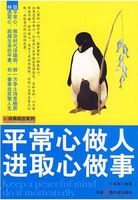1.天籁微语——泰戈尔《飞鸟集》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我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印度自古就有“诗的王国”之称,而泰戈尔的《飞鸟集》正是这个东方诗国里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三百余首清丽的小诗。白日和昼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
《飞鸟集》,我们只要一翻开它,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翅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境地里飞翔到美丽、天真的童话王国里去。人类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想像、对生命的思索和憧憬、对爱情的讴歌和哀叹,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被表达得那么缤纷多彩,那么意味深长。让我们由此而懂得,在一颗充满爱的心灵中,可以产生出何等美妙的思想。
他的诗集一如人人挚爱的大自然一样,焕发出神奇的魅力,处处充满着对丑恶的嘲讽、对自然的渴望、对天真孩童的慈爱、对崇高母性的颂扬、对人类和平的神往……泰戈尔是一个天使,又是自然和人类的儿童。他坚信“春天的花朵”。他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竭的”,他认为“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我存在乃是所谓生命的一个永久的奇迹”。至于文中对光明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对丑恶的鞭挞,更是精辟独到。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的孩子,我从夜的被单里向你伸出我的双手,母亲!”
他的诗在自私自利者面前“像一缕镇定而纯洁之光,会使他们愉悦而沉默”;而在博爱者面前,他的诗文又变成了和善的眼光,像傍晚夕阳一样的和平;凭着他一颗忠诚善良的爱心,他向一切殖民主义者宣言,“总有一颗星在指导我的生命通过不可预知的黑暗”。
整部书像原野上五彩缤纷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探出头来对你微笑,那颜色是那么灿烂,香味是那么芬芳,你尽可以做一只小蜜蜂,畅游在这片花的海洋,忙着啜饮其中一行就可以忘却世间的烦忧。每天都去欣赏那么一两首吧,你每天都会读到不同的内容,每天都会获得全新的启迪,而书中恰到好处的空白正是你思想的野马自由驰骋的疆场。就在这阅读与思索的过程中,你净化了自己的灵魂,也进一步完美了自己,你从中看到了浓缩凝练的自然、人生和社会。
诗的语言恬淡明丽、清新隽永,许多话就像天籁的微语、空谷的低吟,幽婉柔美如抒情的小夜曲,这无疑为诗集平添了一笔雅致的光彩。但对于作者自己来说已不算什么,因为泰戈尔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其文字的呼唤力、渗透力、感召力,语言的音乐美,至今使许多作曲家望尘莫及。
有一天,当你翻开《飞鸟集》,你会发现这本书像一幅奇妙的画卷,展示了爱与美、生与死、劳作和安乐、宗教与人道、理智与冷漠等一系列人生和社会问题,充满了最具东方色彩的比喻和哲理,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教给你的分辨善恶、识别美丑,以及热爱自然、享受生命的方法,将使你受益终生。
2.从“黑暗意识”中苏醒——翟永明《女人》
“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
呵,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
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痕迹地爱你,这秘密
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
在汉语诗歌中,女性意识的第一次伟大复苏是从翟永明的“黑暗意识”开始的。她以“黑夜意识”来指称自己对女性意识的深刻体悟:“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的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女诗人在开拓她的神话世界时,既与诞生的时刻相连,又与死亡的国度沟通,在这越来越模糊的分界线上,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是对自己的清醒认识。”
正是从组诗《女人》开始,“黑暗意识”的翟永明震动了诗坛,也开创了一个女性诗歌的时代。长诗《死亡的图案》《称之为一切》《颜色中的颜色》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诗歌,同时以清晰的印痕记录下了一个新的时代。她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女诗人。
组诗《女人》的创作为期一年,它的整体结构性是惊人的,似乎包含了一个诗人、一个女人生长的全过程,它完全以“个人的声音”对汉语诗歌传统进行了延续和伸展。《女人》具备了一种完整性,它是“一世界”。无论是在诗人表达的主题方面,还是诗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和她传达自己的语气、节奏和其他修辞方向上,它都成为了诗人自己的里程碑,也是当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介入了诸多诗学构想:从激情与活力方面理解的“青春性”,从完整和结构意识方面理解的“中年写作”,以及从经验的自我忠实出发而构想的“个人写作”和“女性诗歌”等等。这组诗与其说不是她最喜欢的,不如说是她最重要的起点——她一直寻找着,并也许在这首诗的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女人》组诗中,《母亲》一首是最具震撼力的诗篇,它几乎集中了诗人对于爱、死亡、生命成长等等主题的高度敏感性的把握。与母亲的交流还使翟永明的诗歌的写作在一开始就具备了历史感,她不再是将母爱处理成单纯的博爱或泛爱的普遍性主题,而是把这一主题和其他有关自我主体性联系在一起。从生与死的延续性角度重读《母亲》,在与母亲的交流集中了女性个人成长的所有秘密和痛苦,在从母亲身上寻求答案并破灭之后,意识到了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含有着轮回力量与延伸性的命运——正如女性在文化中的命运一样,女性通过自己的身体,从母亲到女儿,在身体的创伤中铭刻着历史全部存亡的处境:孤独的、纯粹性的爱,无法避免的诞生和分离的感觉,死亡的必然性与它作用在女儿身上的力量……
翟永明以她诗歌的声音方式引领我们达到这样一种倾听的态度:全神贯注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一种尊重的、平等的心理状态之上,理解她沉默的情感,理解她带着反诘的、质询的口气所隐含的自我批评意识,理解她敏锐果敢的判断……和翟永明一起思考和自省。阅读她,也重新展开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女人到底是“以反抗命运始,以包容命运终”,还是在黑暗中将个人的生命体验对抗所谓的女人命运。
3.溶解心灵的秘密——舒婷《舒婷诗集》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朦胧诗大潮中,女诗人舒婷始终站在风口浪尖,她的名字在诗坛已经家喻户晓,对其诗歌创作的评论文章数量之多也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她也是“今天”诗群中惟一一位有影响的女性诗人。但作为诗人,她似乎是永远地沉默了。她最终只是停留在一个“内心情感型”的女性诗人的形象上。
在舒婷的诗歌世界里,她创造了真、善、美,如果说诗歌是“生活溶解于心灵中的秘密”,那么舒婷善于表现的就正是那种“心灵秘密”,足见其真。她善于为自己的内在情感寻找恰当的外在对应物:大海的珠贝、搁浅的小船、双桅船、橡树和木棉……这些意象在舒婷的诗歌里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象征和隐喻手法的运用使得舒婷的诗歌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把诗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主观诗人偏重于表现自己的内在世界,客观诗人则擅长于再现外在世界。就其骨子内的气质来看,舒婷显然应该划归到主观诗人的行列。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内倾型的主观诗人,舒婷并未对现实闭上眼睛,一味沉浸在自我情感的世界里,而是将自我与时代结合起来,从时代的发展趋势提升自我的情感要求,以诗的方式呼唤人性的尊严。她的《致橡树》《神女峰》等作品,因为具备时代精神的高度而受到人们的赞誉。
在舒婷的诗歌世界里,善——主要表现在把个人的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眼泪。同其他朦胧诗人一样,舒婷把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作为其诗歌的思想内核,这一点同“五四”文学的主题内容是极为相似的。在舒婷的诗中,表现最多的是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人性情感的宣泄。她表达了失却自我的忧伤,大声呼唤真理和言论自由。社会正义、价值理性、人性自由、精神启蒙构成了舒婷诗歌世界的精神支点和情感依托,也构成其诗歌世界里善的主要内容。
在舒婷的诗歌世界里,美——表现在多个方面,从而形成舒婷诗歌的艺术个性。首先,从美学风格上看,舒婷诗歌既有“温柔敦厚”的古典美,又有“激扬奋发”的现代美,她的诗歌成功地熔古典美和现代美于一炉,就在这种融合中凸现出自己的风格,“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还休”。当年冰心笔下描写梦中诗神的句子又正好可用来形容舒婷诗歌的古典情调,她那女性特有的温柔而又忧伤的诗句总是给人以精神慰藉。舒婷的诗歌又有激扬奋发的一面,《致橡树》《神女峰》等诗歌表现出的现代女性意识和叛逆精神,使得舒婷的诗歌情怀从根本上有别于古典诗歌的闲情逸致或落寞闺怨,那个“迷惘”、“深思”、“沸腾”的抒情形象体现了舒婷诗歌中鲜明的时代感和现代精神,而那些激扬奋发的诗句又总是给人以思想启迪。
在她的诗集中,《致橡树》是一首体现了诗人完整人格的诗篇,它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批判意识和人生理想,同时也是面对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话语权威的第一次有力挑战。这首诗曾经鼓舞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至今还被无数的年轻人传诵,说它是来自男性“中心”社会“边缘”的第一声呐喊。《致橡树》强烈地体现了诗人对女性人格独立的愿望和一种乐观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