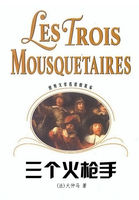“哦,我知道了。”波莉怪声怪气地说,“好吧,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和平女神’。我会回来的——如果能回来的话。不过我现在一定得走了。”她从小门钻进了隧道。椽子之间的黑暗地带几小时前还那么令人兴奋,那么富有冒险色彩,现在却变得普通平淡了。
我们需要回头讲讲安德鲁舅舅。他从阁楼上跌跌绊绊地跑下去时,那颗可怜的老心脏不停地怦怦乱跳。他拿着手帕在额头上不断地擦着汗。当进到楼下的卧室时,便立马把自己锁在里面。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衣柜里摸出一瓶酒和一个酒杯,这些东西经常被他藏在柜子里,免得被蕾蒂姨妈发现。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一杯大人喝的那种味道刺鼻的烈酒,一饮而尽,接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天呐,”他自言自语道,“吓死我了。该死!到这把年纪还碰上了这种事!”
又喝下一杯后,他换了件衣服。这种衣服你从没见过,不过我还记得。他戴上一副硬邦邦的闪着光的高领子,这种领子会使你不得不长时间地昂着下巴。接着,他又套上一件画着图案的白背心,并把金表链挂在前面。之后,他穿上了只有婚丧仪式才用的最好的衣服,拿出最好的高筒礼帽并拍打干净。他的梳妆桌上摆着一瓶花(蕾蒂姨妈放的),他摘下了一朵插在扣眼里,又在左边的小抽屉里翻出一块手帕(漂亮极了,现在很难买到),往上面喷了些香水。最后,他戴上了系着黑色粗绸带的眼镜,冲着镜子观赏起来。
如你所知,孩子们有种傻气,大人的傻气则表现在另一方面。此时,安德鲁舅舅开始犯起这种傻气了。女王不在这里,他很快便忘了刚才可怕的景象,开始对她的美貌想入非非。他不断地嘀咕着,“如此漂亮的贵妇人,先生,她是如此漂亮,一个绝世美人”。他不知不觉地忘了那个“绝世美人”是孩子们带回来的,而认为是自己的魔法把她从未知的世界里召唤来的。
“安德鲁,小伙子,”他一边照镜子一边自言自语,“保养得真不错,根本看不出年龄,先生,你貌比潘安啊!”
你看,这愚蠢的老家伙还在幻想女巫会爱上他,这或许是那两杯酒和漂亮衣服起的作用。可是,无论如何,他爱慕虚荣,犹如一只孔雀,这就是他成为魔法师的原因。他把门锁上,下了楼,让一个女佣去叫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许多仆人),然后望向客厅,正如他所愿,他在客厅里找到了正在修补垫子的蕾蒂姨妈。她正跪在铺在窗户旁边的垫子上。
“哦,蕾蒂娅,亲爱的,”安德鲁舅舅说,“我——我得出趟门。借我五英镑,有个很不错的古娘在等我。”(他总是把“姑娘”说成“古娘”。)
“别妄想了,亲爱的安德鲁,”蕾蒂姨妈连头也没抬,语气坚定且平静地说道,“我说过很多次了,绝对不会借钱给你的。”
“不要捣乱,亲爱的古娘,”安德鲁舅舅说,“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是不借会让我非常难堪。”
“安德鲁,”蕾蒂姨妈直愣愣地盯着他,“让我奇怪的是,你向我借钱居然不会感到羞耻。”
这些话包含着一段冗长而乏味的属于大人之间的往事。简单地说,安德鲁舅舅打着“为亲爱的蕾蒂打理财产”的旗号,却碌碌无为,只知道喝白兰地、抽雪茄,欠下一屁股债(蕾蒂姨妈曾多次为他付钱),这使得蕾蒂姨妈比三十年前穷了很多。
“亲爱的古娘,”安德鲁舅舅说,“你难以想象,我今天会有些特别的花费。我必须得招待客人,借给我吧,别再让我着急了。”
“你到底要接待谁,安德鲁?”蕾蒂姨妈问。
“哦,一个无比尊贵的客人。”
“尊贵的客人?什么东西!”蕾蒂姨妈说,“这个理由可没办法说服我。”
这时,门被撞开了。蕾蒂姨妈一回头,眼前的这个女巨人让她大吃一惊。女巨人身着华服,露着胳膊,目光如炬地站在门口。此人正是女巫。
7﹒在前门发生的事情
“我的奴仆,我的马车还要多久才能来?”女巫用雷霆一般的声音说道。安德鲁舅舅立刻哆嗦成了一团。女巫刚一出现,他照镜子时所产生的一切可笑念头顿时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蕾蒂姨妈连忙站起身来,走到了房子正中央。
“安德鲁,这个年轻的女人是什么人?我可以了解一下吗?”蕾蒂姨妈冷冰冰地问道。
“一个高贵的外国人——十分——十分重要的人物。”安德鲁舅舅结结巴巴地回答着。
“骗人!”蕾蒂姨妈转而对女巫说道,“你这个恬不知耻的荡妇,立刻滚出我的家,否则我就要报警了!”在她看来,女巫肯定是从马戏团里跑出来的,而且,女巫那裸露的肩膀是她不能容忍的。
“你是什么人?”简蒂丝说,“奴隶,跪下,不然我会毁灭你的。”
“女士,请不要在我的家中说粗话!”蕾蒂姨妈说。
瞬间,安德鲁舅舅似乎觉得女巫突然挺直了腰板,因而显得更加高大了。怒火中烧的简蒂丝,将手臂伸出,做了一个在恰恩将宫门摧毁时同样的动作,口中则念着灭绝咒。
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蕾蒂姨妈暗想,那些可怕的话应该也是英语,于是她说:
“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女人一定喝多了。喝醉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简蒂丝突然发现,她那种能把人变成灰烬的魔力在她的世界里那么真实强大,可在我们这里却毫无作用,对她来说这无疑可怕极了。不过她并没有心慌意乱、沮丧失望。她向前扑去,狠狠地抓住蕾蒂姨妈的脖子和膝盖,如同举一个轻巧的娃娃般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朝屋子另一头一扔。还没等蕾蒂姨妈落地,女佣(她觉得那天早上真是妙不可言,令人兴奋)探头进来说:“先生,你要的马车到了,请。”
“快给我带路,奴仆。”简蒂丝对安德鲁舅舅喊道。他口中念叨着“可怕的暴力行为——必须抗议”之类的话,但简蒂丝瞟了他一眼他便闭嘴了。女巫赶着他走出客厅,从房子里出来。迪格雷走下楼时,刚好看见这一幕。
“该死!”他说,“她要在伦敦胡作非为了。还带着安德鲁舅舅,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麻烦事。”
“哦,迪格雷少爷,”女佣叫道(她那天特别高兴),“我想凯特利小姐可能受伤了。”于是两人一起跑到客厅,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想,如果蕾蒂姨妈掉在地板上,或者就算掉在地毯上,也都会摔得粉身碎骨的,不过幸运的是她落在了垫子上。蕾蒂姨妈虽然上了年纪但却十分强壮;那个年代的姨妈们差不多都是这样。她吃了些提神药,静坐了一会儿,然后说只是摔肿了几处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没过多久,她就开始处理事情了。
“莎拉,”她对女佣说(这女人从未赶上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马上去警察局,就说有个危险的精神病人跑出来了。我自己去料理柯克夫人的午饭。”显然,柯克夫人就是迪格雷的母亲。
妈妈吃过午饭后,迪格雷和蕾蒂姨妈也吃完了。之后,迪格雷便开始苦苦思索。
问题是怎样把女巫弄回到她自己的世界,或者,想办法尽快将她从我们这儿赶走。无论如何,绝不可以让她在这幢房子里乱闯乱撞。不能让妈妈发现她。如果可以的话,不能让她在伦敦城里撒野。她“毁灭”蕾蒂姨妈的时候,迪格雷并不在场,可他曾目睹她摧毁恰恩的宫门;因此,他只知道她拥有惊人的魔力,并没发现自从到了我们的世界后,她的魔力已经消失了。他还知道她想要征服我们的世界。可以想象,她现在很可能正在捣毁白金汉宫或议会大厦;几乎能够肯定,不少的警察已经灰飞烟灭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那些戒指好像和磁铁差不多,”迪格雷想,“只要我碰到她,再去触摸黄戒指,我就能把她带到各个世界之间的树林中去。不知道她在那儿是否还会变得虚弱无力。是那地方对她不利么,还是从她的世界里被拖出来时她受到了惊吓?但我必须得去冒这个险。可是我应该到哪儿去找这个魔鬼?我想,不管我怎么说,蕾蒂姨妈都不会允许的;而且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便士。如果我满城地寻找,一定需要很多钱坐汽车和电车。话又说回来,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哪儿找。安德鲁舅舅是不是还跟她在一起?”
最后,似乎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候和祈祷安德鲁舅舅能和女巫一起回来。等到他们回来,他就立刻冲出去抓住女巫,趁她还来不及走进房子就戴上黄戒指。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像猫守老鼠洞一般监视着前门,寸步不离地守在岗位上。于是,他走进了餐室,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把脸“贴”在窗子上。这是一扇可以从里面望到外面的凸肚窗,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向前门的台阶,甚至是整条街道,任何走过前门的人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波莉现在在干什么呢?”迪格雷想。
第一个半小时在艰难的等待中慢吞吞地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迪格雷一直在琢磨着这个问题。不过你不必心急,我来告诉你。波莉回家晚了,吃饭也迟到了,鞋袜都是湿漉漉的。当被问及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时,她回答跟迪格雷·柯克出去了。再三追问下,她说脚是在一片树林中的一个水潭里弄湿的。问她树林在哪儿,波莉说不知道。又问是否在公园里,她回答说也许是在一个公园里。波莉的妈妈因而得出结论:波莉没有经过允许,就偷偷地跑到伦敦某个不知名的公园,跳到水坑里玩水。总之,妈妈说波莉实在太调皮了,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就禁止她和“那姓柯克的男孩”一起玩了。之后,她吃了一些残羹剩饭,就被妈妈赶到床上,起码两个小时后才能下床。诸如此类的事情在那时候是常见的。
因此,当迪格雷透过餐室的窗户向外看时,波莉不得不乖乖地躺在床上。两人都感觉此刻的时间是如此之慢!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处在波莉的位置上。她只要等到两个小时结束就大功告成了,可迪格雷呢,不到五分钟就要跑一趟,每次听到马车声、面包店送货车的声音或者肉铺伙计走过街角的声音,他就以为“她来了”,结果却是一场空。除了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谬误外,在其它时间里,只听见时钟嘀嘀嗒嗒地走着,时间变得异常的漫长难熬。头顶上,一只大苍蝇在玻璃附近嗡嗡地乱飞乱撞。这幢住宅在下午常常显得十分安静枯燥,而且,时不时会有一股淡淡的羊肉味。
在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它与后来某件重要的事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一位女士带着葡萄来探望迪格雷的妈妈。餐室的门开着,于是迪格雷便听到了蕾蒂姨妈和那位女士在大厅里的谈话。
“这些葡萄长得多可爱!”蕾蒂姨妈说道,“我想这些葡萄对她的身体会有好处的。唉,可怜的小玛贝尔!恐怕现在只有年轻的土地上长出的果子才对她的病症有效。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大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两人都压低了声音,说了什么迪格雷并没听见。
要是在几天前听到“年轻的土地”这个说法,他可能会认为蕾蒂姨妈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大人们说话一贯如此,这并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基本上也没多想。不过,他突然想起来,确实存在着其他的世界(蕾蒂姨妈并不了解),他自己就到过其中之一。如此说来,或许真有一片“年轻的土地”,一切皆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也许真有能治好妈妈的病的果子!哦——你能理解,盼望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时是什么心情吗?因为你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也因为那种希望美好得有些奢侈,你甚至就要和希望作对了。这正是迪格雷当时的感觉。然而想扼杀这种希望是徒劳的。或许——真的,真的,有那种可能性。已经发生了那么多奇怪的事了,而且他手里有魔法戒指。每个水潭都通向一个世界。他可以找遍所有的世界。之后——妈妈的病就治好了。那就一切都好了。他把守候女巫的事抛到了脑后。然而,就在他伸手去拿黄戒指的一瞬间,一阵急驰而来的马蹄声打断了他。
“哇!发生了什么?”迪格雷想,“救火车吗?谁家着火了么?天哪,她来了,啊,是她。”
“她”是谁,可想而知。
这是一辆双轮马车。车夫的座位上空着,一只轮子悬在半空中,整辆马车以让人难以置信的平衡飞速转过弯来。车上——不是坐着,而是站着——女巫简蒂丝,那位恰恩的死神。只见她张着大嘴,目光如火一般地跳动着,一头长发像彗星尾巴似的拖在脑后。她毫不留情地鞭打着拉车的马。马的鼻孔涨得通红,像疯了一样冲向前门,在灯柱那里一擦而过,然后,两条后腿直立起来。马车在撞上灯柱的一瞬间上碎掉了。简蒂丝优雅地一跳,恰到好处地跳到了马背上。她跨在马背上坐好,俯下身去,对着马耳说了几句话。这些话显然只会让它狂躁而无法使它安静下来。这匹马瞬间再次抬起前腿,尖厉地嘶叫起来,马蹄、牙齿、眼睛和飞舞的鬃毛都晃作一团。除了最出色的骑手,其他人是难以坐到它的背上的。
迪格雷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又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二辆马车紧随其后,一个穿礼服的胖子和一名警察从车上跳下。随后,载着两名警察的第三辆马车也飞速驶来。随着嘘声与喝彩声,大约二十个人(大多数是僮仆)骑着自行车,一路响着铃赶了上来。最后是一群步行的人,一个个跑得大汗淋漓,但显然十分开心。街边的窗户一扇扇地迅速打开。每幢房子的门前都站着一个看热闹的女佣或男仆。
此时,一位老绅士挣扎着想要从马车的残骸里爬出来,几个人跑过去想帮他,可这个扯腿那个拽胳膊,各顾各的;或许,要是没人帮忙,他早就出来了。迪格雷觉得那位老绅士一定是安德鲁舅舅,但塌下来的高筒礼帽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的,谁都瞧不清楚。
迪格雷冲过去,挤到了人群中。
“就是她!就是这个女人!”一个胖子指着简蒂丝大喊道,“警察先生,你一定得管管啦!她在我的店里偷了价值几百、几千镑的东西。看见她脖子上的那串珍珠项链了吧,是从我这儿偷的。她还打青了我的眼睛。”
“那是因为有人给她撑腰,”一个人对大家说,“我喜欢这样一只发青的眼睛。她干得不赖。哈哈!她可真强壮!”
“先生,你最好在发青的眼睛上放一块好吃的生牛排,那样就更好了。”一个肉店的小伙计说。
“喂,”警察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来说,她……”胖子刚说话就被人打断了,“看住马车里的那个老家伙,全都是他唆使的。”
那位老绅士,显然就是安德鲁舅舅,此时已经站稳了,揉着身上摔肿的地方。
“好吧,告诉我,”警察转向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呼——呼——嘘——”安德鲁舅舅从帽子里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
“别装蒜了,”警察严肃地说道,“这可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摘掉帽子,听见了吗?”
说者容易做者难。安德鲁舅舅徒劳地忙活了一阵,另有两个警察抓住帽边,硬是把帽子拽了下来。
“谢谢,谢谢,”安德鲁舅舅低声说道,“谢谢,天呐,吓死我了。要是有人给我一小杯白兰地……”
“现在,请你回答我,”警察掏出笔记本和一根小铅笔,“那个年轻女人是由你管吗?”
“当心!”几个人异口同声,警察及时向后跳了一步。他差点被那匹马一脚踢死。接着,简蒂丝掉转马头,朝着人群,马的后腿已经踏上了人行道。她手里舞弄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用力地朝套索砍去,试图把马和马车的残骸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