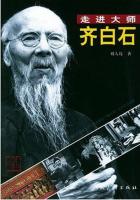一个15岁的衣衫褴褛的大男孩,不用读书也不用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就孤独的在乡间游荡。他的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时刻藏着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是一个身着戎装的外国军官;另一张是这个军官胸前挂着漂亮的外国勋章与一个漂亮女人的合影。
没有人的时候,男孩会摸出照片,爱不释手地看个够,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藏好。即使睡觉都贴身放着,不离不弃,十几年如一日……
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信宜的一幅家常场景。男孩的名字叫李汝礼,李孝式的堂弟。照片上的军官和女人,是李孝式和妻子关小舫。
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土改以及阶级斗争的风暴,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的和平岁月,2010年秋天的一天,笔者为了丰富这部传记的历史和生活资料,在市侨联江起林主席的帮助下辗转采访到李孝式一家在家乡信宜的亲人,已经退休的小学校长李汝礼老先生,不止一次地,这样向笔者描绘他年少时的迷惘和期待……
在相对偏远的信宜,远在异国他乡的李孝式,第一个被划为“华侨工商业资本家兼地主”。他还在襁褓中就随父亲迁往广州时,父亲李季濂和母亲甘固真留下的田地房屋通通被没收,抗日战争时期受过他资助的八叔李如泉(李汝礼的父亲)一家也被抄家,被没收其实靠自己家人耕种的田地。李孝式的弟弟李孝威,1948年平津战役的时候在投诚的途中被误伤致死,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不满4岁的儿子李立德。孤儿寡母被家乡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吓坏了,在李孝式被划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当天,连夜投奔广州的亲戚。年幼的李立德因途中受到惊吓,留下了精神不正常的后遗症——历史的风波平息之后,常年居住在信宜镇隆的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却是“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63号”。李立德的母亲梁耀龙写信向马来亚的哥哥李孝式求助,李孝式也写信到广州到信宜请求相关部门送生活难以自理的母子来马来亚……所有的往来信件都如同石沉大海,救济的汇款又常被拖欠经年……
隔海相望的亲人,求助和援助的手硬是眼睁睁的被隔断了……
“一个人出身于哪个阶级根本是身不由己的。一个人要是生于富贵之家也是身不由己的。一个人要是在生意上交上好运并且赚了大钱也是身不由己的……”跟东姑聊完李氏家族的光荣历史之后,李孝式充满遗憾地这样总结着。
是的,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李孝式也不能。他的每一笔财富都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辛苦得来,因为出生于地主家庭而被打上“剥削”的印记。而且还连带根本不曾亲近过的亲人们都受到牵累。
还有什么比这更冤屈的呢?历史的命运如此,还有什么比这更无奈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被分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国最靠得住的朋友苏联,却是二战时唯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家。历史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李孝式以及整个与他有关系的李氏家族,被命运抛弃到了彼此守望却不能相助的孤岛,曾经热爱向往甚至以命相许的家乡,变得如此的遥远,拒他于千山万水之外。
战争已经结束了好多年,他生命里两个都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国家,因为“阵营”不同仍然彼此排斥着,两地的亲人们被无形却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阻隔着……
李汝礼说,当年他时刻带着的那两张照片,是他无意中从他父亲李如泉的书架上发现的,预备有一天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带着照片偷渡去找在外国做大官的堂哥李孝式,照片就是凭证——自己是李孝式从未见过的家乡亲人。一个浪漫而又无奈的梦想和打算。只是,李汝礼这辈子都还没有去过马来亚。好在,阴霾总会过去,历史终于翻过了惨痛的一页。
后来李汝礼一直在家乡的小学任教,并担任了一所小学的校长。退休后过着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那个衣衫褴褛的、孤独地游荡在乡间的少年李汝礼心心念念想着怎么偷渡的时候,李孝式正在那片即将与自己发生血肉相连关系的土地上,马不停蹄地做着独立之路的演讲,为无数的同胞成为那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并拥有主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奔波着……就是在他的种种努力下,一个国家独立了,在那片土地上拼搏奋斗几十年的同胞拥有了那个国家的公民权,中华文化在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和传承。而他个人的人生理想,也实现了——他成了国家独立的开国元勋和首任财长,成了举世公认的华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他无法释怀的遗憾就是,故乡和亲人越来越远了。他们被无法超越的历史阻隔着,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这段历史成为真正的历史……
是的,时代的进步,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那种牺牲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利益的最终获取。而历史的对错,是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的。就当这一切都是作为大时代中的不幸的个人,为时代的进步做出的牺牲吧!
1956年雨季的一天,大病初愈的李孝式当着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面,翻出了书桌抽屉里一沓无法抵达的家书,感慨地想。
从伦敦墓地回来后,李孝式第3次病倒了。在他的记忆里,他就病过3次,第一次是多伦离开的时候;第二次是第一次去伦敦参加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寻找多伦却没有找到多伦的时候;第三次就是这次在伦敦郊外的墓地里知道多伦已经去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