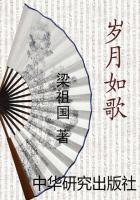11月6日,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开始了。我单位驻点的村是一个大村庄,由三个小村合并而成,选举地点放在村委会,村委会是矗立在国道边的一幢新楼。以前每次经过国道,不曾注意,现在因为11月6日必须在村委会驻足滞留一天,所以在临近选举的日子,过国道时就有意打量了它。楼房的确簇新,墙壁在明媚的秋阳里白得晃眼,不锈钢的大门和玻璃框亮得刺眼,而楼房前的场子还是新掘的泥土,混合了石灰与砖石,一幅时刻整装待发的架势。气派也称得上,虽然只有三层,但四平八稳的模样在丘壑起伏的苍莽里,怎么看也觉得它像一个村委会,而且是一个大村庄的权威机构。
心中暗暗感叹,新农村建设确实实际,路好了,房子显眼好找,为我这样的懒人勾销了不少牢骚和抱怨。想想,这个乡镇在我市最西部,而这个村在此乡镇的最西部。西部已经是一溜往上爬的群山了,当然,我单位驻点的村不是深陷在群山里,而是卡嵌在层层丘陵里。
天下着大雨,哗哗啦啦的,街道路面有了积水。我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大杯水,一同到其它村庄参加选举的另一个单位的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我们到达彼此的联系点,均在八点钟以前,蒙蒙雨中的村庄躺卧在丘陵沟壑里,像抱朴守拙的老人,路边开始是金黄的稻田,慢慢随着路面升高,就是一片片挂满金黄柑橘的丛林了。
下车后,我踟蹰了会,伞上的雨水啪啪作响,我无法抬脚——准备修筑的场子全是一摊乱泥浆,而我穿着皮鞋,随便一抬脚,就是泥巴和雨水的淹没。村委会喇叭此时已经响着高亢而模糊的歌曲。一个黑脸男人在对面喊着什么,又招手致意,要我走前面些,沿着场子边沿的砖坎走。我伸脚走出第一步,第二步就停了下来,黑脸男人踮起双脚,很轻巧走过来,他也穿着皮鞋。然后他回身,我跟在他后面,也踮起脚尖走到村委会里。长长舒了一口气,皮鞋沾满泥巴,幸好,没有水漫溢到鞋里。上二楼,男人关了喇叭,给我倒水。此时,村书记到了,其它工作人员相继到了。接电源、挂标语,抱来选举箱。我站在窗子前,看着对面国道上的车几乎减速,有一两个停下来,是来村委会参加选举的,其它的车马上又加足马力朝山坡爬去。
村民们穿着套鞋来了——这绝对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喇叭里是高昂激情的革命曲子,村民们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中年人老人,但西服和羊毛衫,还有薄呢子外衣,在些许晦暗的雨天显得簇新而庄重。也有和我一样穿着皮鞋来的选民,那当然是年轻一些的村民,我注意到一两个挎着坤包的女子或者媳妇,很漂亮,一个还烫着时尚的波波头,脚蹬土黄色的靴子,我凝望的眼神和她抬头后的眼睛碰在一起,女子给我一个羞赧的微笑。
你是上面的领导?一个矮小的中年人热情地和我招呼,来得挺早嘛,下雨路不好走吧。
这么多问话,我试着从天气回答——选举日竟然下雨,路上倒顺利,就是村委会前的这路……村委会才建起吧……中年人撇嘴,都一年多了,老书记年纪来了,懒得理这小事,等新主任修吧。
已经人声鼎沸了,我干脆站在门口。大门口设有简单的选举主席台,因为选举点分成三个地方,两个在村委会,一个在村委会斜对面的餐馆里,主席台也就只能依靠电源、扩音器来行使主持的任务。老书记已经戴上老花镜,对着话筒使劲喊话:时间已经过去半小时了,选民们请安静下来,选举大会马上开始。无奈,电源不通畅,楼上的听不见,餐馆的更听不见。两个选举点的联络员着急匆匆跑来要小喇叭。老书记吩咐他们——一切按照安排行事。然后,他从容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此时,突然安静了,我看见几个怀揣小板凳在场子上跋涉的老太停了下来,而国道上一个披雨衣的男人刚下摩托车就并拢了双腿。国歌刚停,喧沸声又震得人头昏眼花。
选举正式开始了,选民还在不断地来,穿套鞋的,穿皮鞋的,怀揣板凳的,挎包的,几个嗑瓜子的妇女很悠闲地来到主席台:老汪,你答应修我家前的路没有兑现,就想溜?搞不成的,哈哈,先把路修好,你再下台……哟哟,汪老头子,你通知我们九点钟参加选举,我九点半来村委会,啧啧,你村委会的乱路害我走了半个小时,耽搁我投票,小心我告你剥夺我选举权……
汪书记左一个哈哈又一个哈哈,挣脱嗑瓜子妇女拽着的手,刚端起水杯,几个村民挤到主席台前站好,要求——村子是合并的,两个候选人都不熟悉,做为选民,强烈提议,候选人现在站在主席台,分别给选民就选举这事给选民讲几句话,他们好判断进行选举。汪书记摆手,脖子上的筋一鼓鼓地跳动:我们按照镇里规定选举,不能私下创新。我听到创新,不禁呵呵笑出了声。更可笑的是,一个村民拽住汪书记肩膀,老书记,我们不是土包子了,这算啥子创新?这叫吸人所长……旁边一个妇女插嘴说,就是,人家美国这些天就这样选总统的,也赶上我们这天选举,那个奥……拽老书记肩膀的村民赶紧接口:熬粑粑,是个黑人,他在选民前演说,选民中意才投他票当美国总统。
熬粑粑——我乐开了花,要是奥巴马听到中国老百姓对他的称呼,他肯定是乐极开怀。
汪书记,小冲村快打起来了。一个妇女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咳,××说他家有四个人在外打工,都达到选举规定都有选举权,为什么只发给他三张选票?
你说呢?汪书记似乎很生气女人的传话。你们平常都听什么,委托票最多只能委托两——旁边传来很响亮的擂桌子的咚咚声,我挤在拥挤的人群里,踮起脚尖,看见一个男子正义愤填膺地吼叫,右手拍着桌子:你们想剥夺老百姓的选举权,搞不成!我朝里挤,想对生气的男子解释委托票的规定,但男子一个转身,挤过人群,朝主席台奔去。
你们想搞独断专权,搞不成的,你们说,我家婆娘和两个儿子有没有选举权?男人转身询问围观的人群。人群有声音附和,有的有的,现在是民主时代,只要达到十八岁没有犯法都有的。男人得到鼓舞,很激动地说,就是,你们选举想搞鬼……汤镇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男子后面,拉了他肩膀,说,你误会了,一个人只能接受两张委托票……男人还是激动,那你说,我婆娘和儿子没有选举权?他们不能参加直接选举?汤镇长拉男人手说,莫激动,我们一边说去,不要耽搁大家正事。
又吵起来了,一个老头跑来告诉汪书记,你去看看,调解下,大事情咧。
旁边有不少人吵闹,选举有猫腻,说监票人硬是拉选民写某某的名字。我跟在汪书记后面,还是小冲村,一张桌子发选举票,一张桌子抵在内室的门口,上面放选举箱,内室里三个秘密写票桌子,上面被书写“秘密写票处”的红纸板围拢,村民们集聚在外面拥来挤去,热烈谈论。监票人很委屈,说,我只告诉他们两个人名的字如何写,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怎么说我搞鬼?汪书记脖子上的青筋又一鼓一鼓地跳动,跺脚吼道:哪个,是哪个说监票人要你写某某的?
这真是一个热闹的日子。外面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你,你来给我说清楚,我投一张委托票有错不?
刚回到主席台的汪书记又被拽住了,他摘了老花镜,瞪眼说,没错,你说的没错,你拉我有错。我意外看见汪书记嘴唇上的胡子上下抖动,哈,吹胡子瞪眼睛啦。
你烦啥,我才烦,我代我侄子投票,为啥不给我发委托票?
你侄子有你嫂子代投,你还投啥。
你们刚才不是说一人只能投两张委托票吗?我嫂子代投我哥和大侄子的,我代投我小侄子的,啥不行?
你小侄子委托你,又没有给我们选举委员会汇报,你临时想啥做啥,咋行。
他在深圳打工,凭啥知道你们电话,他咋申请汇报?你个村委会芝麻大的官,官样摆得挺足的,看来,我们逢年过节还要给你们烧三柱香。
乱扯,你儿子好歹吃官饭,你这个老子说啥还得为儿子讲个素质。
你素质高,凭啥不让我侄子选举,他已经二十岁了,有选举权,人活得好好的,他选举证明他合法他是个公民,你们马上发我选举票。
行,你和他联系,要他亲自给我说,他委托你投票,你尽管代表他行使你权利。
你等着,老人按响手里的手机,放耳边后喂喂几声递给了汪书记。
我开玩笑说,汪书记,你村里的选民素质还挺高的,很在乎自己的权利。汪书记没来得及答话,旁边一个年轻的妇女说,那是,选谁关系着咱村的前途,以后咱们日子好不好,好歹得看今天这个票。
一个细高个的老头为媳妇争取选票惹来旁边村民的玩笑——哈哈,儿子不在家了,照护媳妇细心些,这权利要争,汪书记,你这个不解决,可就是挫伤民意,下台了小心挨打。汪书记抹了下额头,又瞪起双眼说,赵老头子的媳妇也是我媳妇,哈哈,我比他还细心,关键是你这老头子办事邋遢,早先你媳妇嫁来就应该把她户口迁来,现在假积极,才伤我的心。
旁边人问,伤你什么心?
伤我媳妇的心比伤我的心更要我难受哦……
汤镇长来了,后面跟着他调解的男人,汤镇长要汪书记把选举法翻出来给生气的男人看,汪书记戴上老花镜,翻出白皮本,朝男人晃了晃——喏,你看好,选举法啊,然后手指沾了口水,一页页朝后翻,翻到有关委托票这一条,靠近男人,大声念读这一条款。男人还是生气,那我婆娘和我儿子都来电话交代了,要选谁当村委会主任,这事是小事吗?你们是选举委员会的,你们给我解决好。
我提议,你可以代你两个儿子投票,你老婆再请委托人啊。汪书记很认真,你还要你老婆同意谁帮忙投委托票,这事你老婆说了算。男人脸红,朝汪书记借手机,说老婆在省城给儿子带孩子,这就电话问她。男人背过身打电话,说,今天选举,我只能代表你和你弟弟投票,你妈还要请人再投。随后,男人把手机递给汪书记,要汪书记接电话,说,我婆娘要你代投选村主任,她保密,只跟你说选谁。
又在飘小雨,淅淅沥沥的,我上二楼三楼转了下,又在外面淋雨站了会,头脑清醒许多,也感觉天气已经很凉了,可以称上冷。门口,几个挎凳子的老人给老书记建议:以后谁想当候选人,就必须先开大会,给我们讲下他在任期间要做的事情,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心里才有个数。汪书记说,你们要建议,得等明天给新主任说,我今天值最后一个班,得稳扎稳打。
陆续有人抱来选举箱,一个衣着鲜艳色彩毛衣的老婆婆从二楼下来,我注意到,她竟然不是穿着套鞋,而是旅游鞋。汪书记大声招呼——万婆子啊,还是这么俏。老婆婆把手搭在耳边,说,汪老头子,你大点声喊嘛,我听不到。
你听不到,巷子还是那样深哦。
哈哈,我是巷子深,你是蚊子跳夜壶。
这很逗的话在选举日不再显得过分,难得这样热闹,难得这样聚集在一起。我瞧着俏老妪,她快成核桃的脸皮依然显山露水地暴露着先前的美丽,合身不俗的穿戴配着灰白的头发在人群里抢人视线。老妪手指夹着汪书记递给她的香烟离开了。走时她丢下一句话:汪老头子真要退位了?不简单,我看你是蚂蚁爬筲箕(事后,我询问他人,得知这个歇后语比喻路子多的很)。
喂,你还是嘴上多积德……老书记坐下来,捧起茶杯,投票几乎接近尾声,三三两两的人群已经在离开。主席台并没有清闲下来。一个妇女气冲冲地跑来问责——我家老人和我们两口子都在家,应该都有选举权,为什么我家老人没有选票?汪书记要求妇女去找小组负责人。妇女说,××说他登记就写了我老人名字,要我来找你的。汪书记很恼火,你等我问,到底有无你老人名字。汪书记在手机里确定,五组的选举名单就在选举委员会人手里,确实没有妇女家老人名字。妇女越发生气;你们捣鬼,我清清楚楚记得,××在我家登记时,还说我老人虽然瘫痪了,但可以委托我选举,就记上了名字。汪书记胡子上下抖动,用手机喊来五组登记的人,××一路跑来,人还未到主席台,就在喊,我登记确实有她家老人名字,后面的事情我就搞不清楚了。老书记胡子又上下抖动,喊,你甭来我这里,你回家把原始的登记表给我找来。××转身就跑,说,我要投票去,等我完事了再回去找。
妇女眼睛红了,说,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但我老人起码还没有死,还活着,就不能一下子勾销他的名字吧。我安慰妇女说,不要紧的,会弄清楚的,都有一个说法,到时看你们组的选票发放情况,如果还多,你完全可以代你老人投选举票。妇女走后,我得知,非常有趣的是,汪书记就此事联系的两个人分别是村主任候选人。
十二点过十分,五个选举箱(该村共有五个小组)全部送到主席台。汤镇长和汪书记商量,抱选举箱上二楼大会议室,准备开箱统计票额唱票。
十二点二十分时,一个胖墩墩的妇女,撑把雨伞进来,大声喊:我还要投票。我上楼找来汤镇长。汪书记一下楼就叫道——你不是刚才投了票吗?还投啥票?
妇女倒不紧不慢,我小叔子两口子才来电话,要求我们代他们一家投票,合理合法,你大惊小怪的。
汤镇长忙说,按照规定,十二点就应该完成投票的,我们已经等了十分钟……汪书记赶紧说,我们按规矩办事嘛,要是选举都完了,天黑时还有人来说要投票,行吗?
妇女抢白了老书记一眼,哟,你说话蛮在情的,你看你弄的路,一滩乱泥,我最少走了十分钟,不被这路耽搁,刚好赶上十二点一十。
汪书记吹胡子瞪眼。汤镇长息事宁人,说,这样,我们肯定是尊重选民的意愿,我请示书记,如果他说能投票你可以投,他说不行,你就不能投票。妇女点头。汤镇长拨响电话请示:“……选举箱还没有开封……好的,一定尊重选民意愿……”
妇女被带到秘密写票处,又把选票折叠好,庄重地用双手投进刚抱下来的选举箱里。妇女吐出一口气说,我小叔子一家走得再远,说到底还是这村里的人。老书记,你别生气,我还真想你当我们书记。
汪书记摆手,你们看我老头子,就想着法子欺负我,没门啦。
唱票统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雨完全住了脚,村委会后面的柑橘林里传来清脆的鸟鸣声,叽叽喳喳的,悦耳、清新。村委会大楼安静了,时光放慢了脚步。我肚子咕咕地强烈地发出抗议声。汪书记给我一盒快餐面,我看没有一个人吃,就把快餐面放在一边。下楼脚步发虚时,我决定泡快餐面吃了。
在下午三点钟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另一个单位叫我回城的,他们选举结果早出来了。我看黑板上的票额统计,两个主任候选人势均力敌,票数非常接近。我回电话,说,如果票额不过半数,可能要重选。重选多麻烦啊,别单位的车只好先回城了。
终于,票数唱完了,扣人心弦的新主任职位尘埃落定——一个候选人以996票当选,票额差不多刚过了半数,好险!此时刚好16时30分。旁边有村民相互嘟哝,这个选举蛮有意思,还蛮真实的。
我在祝贺当选人时,竟然发现,新当选的主任是早上踏过乱泥迎接我的黑脸男人。我下楼离开,新主任说,是我早上迎接你来的,还是我送你走。仍然是他在前面踮脚在乱泥里带路,我踮脚跟着他走出场子。
我想,再经过这里时,看见的应该是齐整、宽敞而平坦的场子,说不定,场子里还有绿树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