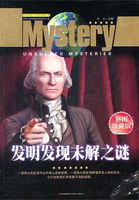人口的迁徙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但在人类社会初期,它较多地与自然因素相关。史称中国古代的夏后氏,曾有十迁,可能多因环境所逼。而大禹时的迁徙,则显然与水患有关。殷商时期,举族迁徙也很频繁。有人考证,商代前后大的迁徙有16次。其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为了避免河患,有的说是为了避免来自西北方少数族的侵扰。比较贴近史实的说法,是商代尚处于刀耕火种的“游农”阶段。因为耕作粗放,不知道保护土壤肥力,所以必须不断地更换地块,迁来迁去。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在成汤以前,迁徙次数较多,迁徙到新地后居留的时间较短;成汤以后,迁徙的次数减少,迁到新地后居留的时间较长。特别是盘庚迁殷后,在一地居留的时间更长。这似乎表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逐渐提高,人们已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土地肥力,由早期频繁的“游农”向定居农业过渡。
殷商以后,中国社会已迈入农业定居时代。户口迁徙在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春秋战国时,一些思想家认为,如果让百姓从事农耕,就会厚重一些,厚重就会少私义,少私义,公法就能立,事业就能专一。百姓从事农耕,家产就能多一些,家产多就会顾忌迁徙,顾忌迁徙,就是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也不会有其他想法。相反,如果百姓舍本(即不从事农耕)而事末(即从事工商等业),就难以号令他,不能号令他,国家退不能守,进不铜牛车能攻。再者,百姓舍本事末,他的家产就简约一些,家产简约,就易于迁徙。百姓迁徙不定,一旦国家有难,人人都想跑走,没有安居之心,国家就危险了。
春秋战国时出现的这种“尚农重迁”思想,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发展。《汉书》的作者班固,把这一思想概括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八字。意思是,治理国家之道,是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这是根本。此后历代户口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可以说超不出这八字箴言。
与“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思想相应的,是历代都有一些尽量使民地著务本而不迁徙的办法。《周礼·地官·载师》规定:凡是房屋周围不栽树木的,要罚他代缴一里之中25家的税布;凡田地未耕作的,要出三个丁壮劳力的粟米;凡没有职事可干的,要罚他出按家庭征收的赋税。也就是说,没有恒居之心,耕作不努力,要受经济处罚;不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没有固定职业而游荡之人,也要额外加税,以示劝惩。
秦汉时有“禁民二业”的政策。所谓“禁民二业”,就是士、农、工、商,只能死守一业,不能改业,也不能兼业。而“禁民二业”的主旨,是促民归农。如秦国就一再强调用各种手段促使人们“作壹”,即一心一意务农。商鞅还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朝廷不许人们自由迁徙,那些愚昧无知而又不安心农业的人就没处吃饭,从而必定务农。愚昧贪婪的人专心务农,农民就必然安宁。农民安宁而愚昧,荒地必然开垦,国家也就富裕了。
在“禁民二业”的同时,是竭力招诱“亡命”之人归田,以扩大农耕队伍。汉代有“舍匿法”,即对在各地游窜,在诸侯家中说长道短者,以及收留这些人者,都要给轻重不等的处罚。王莽当政时,一度还依照周朝之制,对浮游无事之人加征“夫布”之税。
从唐宋一直到明清,基本上恪守秦汉以来“尚农重迁”的治国思想,主调是四民各守本业,不得擅自改业,擅自迁徙。并用各种手段,促使人们归农、务农,安土重迁,死守一地。
与“尚农固本”相应的是“抑末”,即对工商等业的种种禁限和抑制。秦汉特别是汉代以后,逐渐将本、末与农、工、商对等起来,并用各种办法抑制、打击工商之家,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如商贾有市籍,工匠有匠籍,一入市籍和匠籍,地位就低人一等;法律规定工商业者及其子孙不能入仕为官;工商之家的赋税要重于农民之家。明代甚至规定,农民之家可以穿绢纱,工商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如果有一人为商贾者,也不许穿绢纱。凡此种种,目的就是通过“抑末”,促使人们归本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