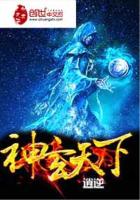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早上八点多钟,对于我来说已经是破天荒了),连早饭都没吃,就用一个小水桶装上十几只河蚌,直奔J市最好的一家医院——S省立医院。
我提着水桶从走廊里走过的时候,立即引来许多人侧目,并掩上了鼻子。
桶内的河蚌虽然已经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不像刚捕上来时那样臭气熏天,但依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异味道,就是盖着盖子,也能从缝隙中散发出来。
我厚着脸皮微笑着,大大咧咧的从他们身边走过,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呢,就算他们把我当成神经病,我也毫不在乎。
医院的大夫都刚刚上班,冯亦农教授也是。当我推开门走近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换着白大褂,一见我拎着一只水桶不伦不类的走进来,就笑着打趣:“小度,你搞什么鬼,我们这里是给人看病的地方,不是水桶修理铺!”
人们对一个城市的留恋,并不是指对这个城市的建筑如何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其间的人们怀有的深厚感情,更功利一点讲,是那里已经有了这个人可以惬意生活的人脉网。冯亦农就是我的人脉关系网中重要的一条,有了他的帮助,我可以和J市所有医院的医生建立起联系,因为他不光是一位医道高超的主治大夫,还是这座城市医学协会的副会长,兼任某高等学府的医学教授,所以他在J市医学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我将水桶蹲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屁股坐下来,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向他抱怨道:“你说你住那么高干嘛?害得我一口气跑上来,累得要命。”
冯亦农虽然也有五十多岁了,但生性豪爽,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跟他交上朋友。他一听我这话,立即就乐了:“嗨,还没见你这样的,我又没请你来……再说那不是有电梯吗?”
“你们看电梯的那老太太忒死板,死活不让我上,我就差给她跪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