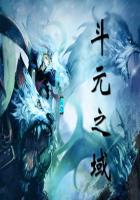弹着mandolin,低低地唱着,靠在墓碑上:
我的生命有一个秘密,一个青春的恋。
可是我恋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恋,我也只得沉默。
天天在她身边,我是幸福的,可是依旧是孤独的;她不会知道一颗痛苦的孩子的心,我也只得沉默。
她听着这充满着“她”的歌时,她会说:“她是谁呢?”
直到年华度尽在尘土,我不会向她明说我的恋,我是只得沉默!
我低下了脑袋,默默地。玲姑娘坐在前面:
“瞧哪,像忧郁诗人莱诺的手杖哪,你的脸!”
“告诉你吧,我的秘密……”可是我永远不会告诉她真话的。
“我想起了母亲呢!”
便又默着了。我们是时常静静地坐着的。我不愿意她讲话,瞧了她会说话的嘴我是痛苦的。有了嘴不能说自家儿的秘密,不是痛苦的哑子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不明说;我又不是不会说话的人。可是把这么在天真的年龄上的纯洁的姑娘当作恋的对像,真是犯罪的行为呢。她是应该玛利亚似地供奉着的,用殉教者的热诚,每晚上为她的康健祈祷着。再说,她讲多了话就喘气,这对于她的康健有妨碍。我情愿让她默着。她默着时,她的发,她的闭着的嘴,她的精致的鞋跟会说着比说话时更有意思的悄语,一种新鲜的,得用第六感觉去谛听的言语。
那天回去的路上,尘土里有一朵残了的紫丁香。给人家践过的。她拾了起来裹在白手帕里边,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家里有许多这么的小紫花呢,古董似的藏着,有三年前的,干得像纸花似的。多咱到我家里来瞧瞧吧。我有妈的照片和我小时候到现在的照片;还有贵重的糖果,青色的书房。”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把那天的日记抄在下面:
五月二十八日
我不想到爹那儿去,也不想上母亲那儿去。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姐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我拒绝了。他们说我近来变了。是的,我变了,我喜欢孤独。我时常独自个儿在校外走着,思量着。我时常有失眠的晚上,可是谁知道我怎么会变的?谁知道我在恋着一位孤寂的姑娘!母亲知道的,可是她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自家儿也知道,可是我告诉谁呢?
今儿玲姑娘在家里伴父亲。我成天地坐在一条小河旁的树影下,哑巴似的,什么事也不做,戴了顶阔边草帽。夏天慢慢儿的走来了,从那边田野里,从布谷鸟的叫声里。河边的草像半年没修发的人的胡髭。田岸上走着光了上半身的老实的农夫。天上没一丁点云。大路上,趁假日到郊外来骑马的人们,他们的白帆布马裤在马背上闪烁着;我是寂寞的。
晚上,我把春天的衣服放到箱子里,不预备再穿了。
明儿是玲的生日,我要到她家里去。送她些什么礼呢?我要送她一册戴望舒先生的诗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颗痛苦着的心。
今晚上我会失眠的。
六
洒水车嘶嘶地在沥青路上走过,戴白帽的天主教徒喃喃地讲着她们的故国,橱窗里摆着小巧的日本的遮阳伞,丝睡衣。不知那儿已经有蝉声了。
墙上牵满着藤叶,窗子前种着棵芭蕉,悉悉地响着。屋子前面有个小园,沿街是一溜法国风的矮栅。走进了矮栅,从那条甬道上走到屋子前的石阶去,只见门忽然开了,她亭亭地站在那儿笑着,很少见的顽皮的笑。等我走近了,一把月季花的子抛在我脸上,那些翡翠似的子全在我脸上爆了。“早从窗口那儿瞧见了你哪。”
“这是我送你的小小的礼物。”
“多谢你。这比他们送我的那些糖啦,珠宝啦可爱多啦。”
“我知道那些你爱好的东西。”恳切地瞧着她。
可是她不会明白我的眼光的。我跟了她进去,默着。陈设得很简单的一间书房,三面都有窗。一只桃花木的写字台靠窗放着,那边儿角上是一只书架,李清照的词,凡尔兰的诗集。
“你懂法文的吗?”
“从前我父亲在法国大使馆任上时,带着我一同去的。”
她把我送她的那本《我底记忆》放到书架上。屋子中间放着只沙发榻,一个天鹅绒的坐垫,前面一只圆几,上面放了两本贴照簿,还有只小沙发。那边靠窗一只独脚长几,上面一只长颈花瓶,一束紫丁香。她把我送她的紫丁香也插在那儿。
“那束丁香是爹送我的。它们枯了的时候,我要用紫色的绸把它们包起来,和母亲织的绒衫在一块儿。”
她站在那儿,望着那花。太阳从白窗纱里透过来,抚摸着紫丁香的花朵和她的头发,温柔地。窗纱上有芭蕉的影子。闲静浸透了这书房。我的灵魂,思想,全流向她了,和太阳的触手一同地抚摸着那丁香,她的头发。
“为什么单看重那两束丁香呢?”
她回过身来,用那蒙着雾似的眼光望我,过了一回才说道:
“你不懂的。”我懂的!这雾似的眼光,这一刹那,这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上永远是新鲜的。我的灵魂会消灭,我的身子会朽腐,这记忆永远是新鲜的。
窗外一个戴白帆布遮阳帽的影子一闪,她猛的跳起来,跑了出去。我便瞧一下壁上的陈设。只挂着一架银灰的画框,是Monet的田舍画,苍郁的夏日的色采和简朴的线条。
“爸,你替我到客厅里去对付那伙儿客人吧。不,你先来瞧瞧他,就是我时常提到的那个孩子。他的母亲是妈的邻舍呢!你瞧瞧,他也送了我一束紫丁香……”她小鸟似的躲在一个中年人的肩膀下面进来了。有这么个女儿的父亲是幸福的。这位幸福的父亲的肘下还夹着半打鱼肝油,这使我想起实验室里石膏砌的骨骼标本,和背着大鳘鱼的丹麦人。他父亲脸上还剩留着少年时的风韵。他的身子是强壮的。怎么会生了瘦弱的女儿呢?瞧了在他胁下娇小的玲姑娘,我忧郁着。他把褂子和遮阳帽交给了她,掏出手帕来擦一擦脑门上的汗,没讲几句话,便带了他那体贴女儿的脸一同出去了。
“会客室里还有客人吗?”
“讨厌的贺客。”
“为什么不请他们过来呢?”
“这间书房是我的,我不愿意让他们过来闹。”
“我不相干。你伴他们谈去吧。疏淡了他们不大有礼貌的。”
“我不是答应了你一块儿看照片的吗?”
便坐在那沙发榻上翻着那本贴照簿。从照上我认识了她的母亲,嘴角和瘦削的脸和她是很像的。她拿了一大盒礼糖来跟我一块儿吃着。贴照簿里边有一张她的照片,是前年在香港拍的:坐在一丛紫丁香前面:那熟悉的笑,熟悉的视线,脸比现在丰腴,底下写着一行小字:“Say it with flowers.”
“谁给你拍的?”
“爸……”这么说着便往外跑。“我去弄Tea你吃。”
那张照片,在光和影上,都够得上说是上品,而她那种梦似的风姿在别的照片中是找不到的。我尽瞧着那张照,一面却:“为什么她单让我一个人走进她的书房来呢?为什么她说我不懂的?不懂的……不懂的……什么意思哪,那么地瞧着我?向她说吧,说我爱她……啊!啊!可是问她要了这张照吧!我要把这张照片配了银灰色的框子,挂在书房里,和母亲的照一同地,也在旁边放了只长脚几,插上了紫丁香,每晚上跪在前面,为她祈福。”——那么地沉思着。
她拿了银盘子进来,给我倒了一杯牛奶红茶,还有一个香蕉饼,两片面包。
“这是我做的。在香港我老做椰子饼和荔子饼给父亲吃。”
她站到圆桌旁瞧我吃,孩气地。
“你自家儿呢?”
“我刚才吃了糖不能再吃了,健康的人是幸福的;我是只有吃鱼肝油的福分。广东有许多荔子园,那么多的荔子,黑珠似的挂在枝上,那透明的荔肉!”
“你今天很快乐哪!可不是吗?”
“因为我下星期要到香港了,跟着父亲。”
“什么?”我把嘴里的香蕉饼也忘了。
“怎么啦?还要回来的。”
刚才还馋嘴地吃着的香蕉饼,和喝着牛奶红茶全吃不下了,跟她说呢,还是不跟她说?神经组织顿时崩溃了下来,——没有脊椎,没有神经,没有心脏的人了哪!
“多咱走哪?”
“后天。应该来送我的。”
“准来送你的。可是明儿我们再一同去看看母亲吧?”
“我本来预备去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吃哪?”
我瞧着她,默着——说还是不说?
“不吃吗?讨厌的。是我自家儿做的香蕉饼哪!你不吃吗?”蹙着眉尖,轻轻地顿着脚,笑着,催促着。
像反刍动物似地,我把香蕉饼吃了下去,又吐了出来,再嚼着,好久才吃完了。她坐到钢琴前面弹着,Kiss me good night,notgood bye,感伤的调子懒懒地在紫丁香上回旋着,在窗后面躲着。
天慢慢儿地暗了下来,黄昏的微光从窗子那儿偷偷地进来,爬满了一屋子。她的背影是模糊的,她的头发是暗暗的。等她弹完了那调子,阖上了琴盖,我就戴上了帽子走了。她送我到栅门边,说道:
“我今儿是快乐的!”
“我也是快乐的!再会吧。”
“再会吧!”扬一扬胳臂,送来了一个微笑。
我也笑着。走到路上,回过脑袋来,她还站在门边向我扬着胳臂。前面的一串街灯是小姐们晚礼服的钻边。忽然我发现自家儿眼上也挂着灯,珠子似的,闪耀着,落下去了;在我手里的母亲照片中的脸模糊了。
“为什么不向她说呢?”后悔着。
回过身去瞧,那书房临街的窗口那儿有了浅绿的灯光,直照到窗外窥视着的藤上,而那依依地,寂寞地响着的是钢琴的幽咽的调子,嘹亮的声音。
七
第二天,只在墓场里巡行了一回,在母亲的墓上坐着。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阴郁的脸色,问我为什么。“告诉她吧?”那么地想着。终究还是说了一句:
“怀念着母亲呢!”
天气太热,她的纱衫已经给汗珠轻薄地浸透了背上,里面的衬衣自傲地卖弄着风情。她还要整理行装,我便催着她回去了。
送行的时候连再会也没说,那船便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可是她眼珠子说着的话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码头上,瞧着那只船。她和她的父亲站在船栏后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湿风对于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为她祝福。
她走了没几天,我的父亲为了商业的关系上天津去,得住几年,我也跟着转学到北平了。临走时给了她一封信,写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听着沙漠里的驼铃,年华的蛩音。这儿有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种风,这儿是没有的。从香港她寄了封信来,说下月便到上海来;她说香港给海滨浴场,音乐会,夜总会,露天舞场占满了,每天只靠着窗栏逗鹦鹉玩。第二封信来时,她已经在上海啦;她说,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了放在首饰箱里,鹦鹉也带了来就挂在放花瓶的那只独脚几旁,也学会了太息地说:
“母亲啊!”
她又说还是常上公墓那儿去的,在墓前现在是只有菊花啦。可是北平只有枯叶呢,再过几天,刮黄沙的日子快来咧。等着信的时间是长的,读信的时间是短的——我恨中国航空公司,为什么不开平沪班哪?列车和总统号在空间运动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脉搏相应的。
从褪了金黄色的太阳光里,从郊外的猎角声里,秋天来了。我咳嗽着。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喜乐,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过几天,我又要每晚上发热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惯常的事。
多咱我们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亲也许在那儿怀念你哪!
玲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厉害,发了五天热,脸上泛着桃色。父亲忧虑着。赶明儿得进医院了。每年冬季总是在蝴蝶似的看护妇,寒热表,硝酸臭味里边过的,想不到今年这么早就进去了。
希望你天天写信来,在医院里,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凶着点儿。母亲那儿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来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怀念着在墓前坐着谈母亲的日子啊!
又:医生禁止我写信,以后恐怕不能再写了。
玲十一月十四日
来了这封信后,便只有我天天地写信给她,来信是没了。每写一封信,我总“告诉她吧?”——那么地思忖着。末了,便写了封很长的信给她,告诉她我恋着她,可是这封信却从邮局里退回来啦,那火漆还很完固的。信封上写着:“此人已出院。”
“怎么啦?怎么啦?好了吗?还是……还是……”便想起那鱼肝油,白色的疗养院,冷冷的公墓,她母亲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树,紫丁香……可是那墓场的冷感的风啊……冷感的风……冷感的风啊!
赶忙写了封信到她家里去,连呼吸的闲暇也没有地等着。覆信究竟来了,看到信封上的苍老的笔迹,我觉得心脏跳了出来,人是往下沉,往下沉。信是这么写着的:
年轻人,你迟了。她是十二月二十八葬到她母亲墓旁的。
临死的时候儿,她留下来几件东西给你。到上海来时来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领你去拜访她的新墓。
欧阳旭。
“迟了!迟了!母亲啊,你为什么生一个胆怯的儿子呢?”没有眼泪,没有太息,也没有悔恨,我只是低下了脑袋,静静地,静静地坐着。
一年以后,我跟父亲到了上海,那时正是四月。我换上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哪,那些年轻的脸。我叩了门,出来开门的是她的爹,这一年他脸上多了许多皱纹,老多了。他带着我到玲姑娘的书房里。窗前那只独脚几还在那儿,花瓶也还在那儿。什么都和去年一样,没什么变动。他叫我坐一会,跑去拿了用绸包着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边的贴照簿给我。
“她的遗产是两束枯了的紫丁香,两本她自家儿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认识这两件东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记起了口袋里还有她去年给我的从地上捡来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块儿走了。路上买了一束新鲜的丁香。
郊外,南方来的风,吹着暮春的气息;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田野是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是不会说话,只会微笑的。
走进墓场的大门,管墓的高兴地笑着,说道:
“欧阳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经安上了。”
见了我,便:——“好久不见了!”
“是的。”
走过母亲的墓,我没停下来。在那边儿,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上有一块新的墓碑:
“爱女欧阳玲之墓”
我不会忘记的,那梦似的笑,蒙着雾似的眼光,不十分健康的肤色,还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迟了。
他脱下了帽子,我也脱下了帽子。
一九三二,三,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