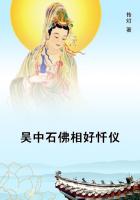“也成,把你和孩子的户口起出来,拿你自个儿手里,不分你地。当时叫我们两个妇女去做手术,人家那个就没去。”
“就把她跟孩子的户口起了?”
“起了,没地,也不着家了,带着孩子四处走。还是人家好!那还有个生儿子的指望。”簸着粮食,守着房子,竟羡慕那四处走的!
“干脆,我给你偷一个儿子去吧。”
“哪儿去偷?”她吓了一跳。
“大街上,看准了,抱起一个就跑。你敢养吗?”
“敢!你敢偷我就敢养!”
“你敢养我这就敢偷!”
说了,俩人又咯咯笑。
她忙里忙外,我睡我必睡的午觉。一觉醒来,饭菜摆了一桌子,地下、院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吃了饭,抹抹嘴,太阳就偏西了。该走了。在农村,走亲戚就是吃顿饭。凤姐送我,不忘提着去摘棉花的口袋。
她婆婆、她嫂子都从自家的院赶出来送,拉着手,叫一声“妹”,再叫一程“儿”。糊里糊涂,照着凤姐掰着嘴教的,叫她婆婆“姨”。悄悄问,她算我什么姨?
“俺婆婆和你婶子的娘家妈是一个人儿。”
还没绕过来。
“大妹子,再来……”,“儿,慢走……”
在城里也没个亲戚,也没个哥和姐,一个人独来独往;有什么些个没整明白的亲戚,叫着,应着,心里还怪热乎乎的。
走到村口那儿,凤姐叫我看看她那块比谁家都长得好的棉花地。景全骑着车追上来,见了,又非要给我指道,把我送到大路上。
路是小的,弯的,没三个辛庄也够我乱的。
“景全,现在转业回来能混上个果园场长也不易呀。”
“啥!人家工人把树都承包了,咱一个月挣那六七十块钱的国家干部,成了‘贫下中农’啦。”
“咦,你不是坦克兵吗?会开车吧?”
“当然会!”
“那,你还不如也承包个拖拉机,汽车什么的。再不如,也跟咱四妹凤英她丈夫似的,去开人家承包的车,那也来钱着呢……”
“咱可不干那。咱不敢。”
不知怎的,我觉着我叔的姑爷景全,真是我们家的人,跟我有种一致的秉性……
“妹子——”路是弯的,凤姐远在棉花地里招手:“明儿,我回娘家送你。”
“别!”我骑在车上大声喊,“就是知道你忙得四脚朝天才跑来看你呢!”
“忙死,你一辈子来几回呀?”
“那行,穿得漂亮点儿!我要给你们照相呢。”
“哟,咱这么胖,还不照到相外边去啦……”
叔家的人平日里也难得吃上这样的“大锅饭”呢。
分了家的,嫁出去的,能来的全来了。小桌坐不下,小凳也不够使,挤着,蹲着、站着。“哼,都沾我妹的光呢!”凤姐脆声叫。还真的呢,老家还是老例,来客,女的不上桌,这回,叔家的女的,不管婶还是嫂、姐、妹,全都和男的一块儿上桌吃饭,造一回反!会喝不会喝,一人一碗酒,甜的;自然,大人、孩子,一人手里攥一个煎饼。
大嫂的儿子偷偷把鱼丢给桌子底下的狗吃,二弟的儿子大壮呢,把不爱吃的肥肉片举着叫:“燕儿!燕儿!……”
“别惊那燕儿,别惊那燕儿。”婶子一边说积善的人家燕才肯建窝,一边呢,就把鱼呀,鸡呀,往我碗里堆,“唉,明儿早起吃饭,又剩我一个人了……”
“哎呀!”我大叫起来。我突然想起来,要走了,还没喝上那碗酸辣汤呢!竟给忘了!
“今儿有集吗?”
“有,天天有。”
“集上有酸辣汤吗?”
“有,到处有,干啥?”
“想去喝一碗酸辣汤呢。”
“不早说,这都什么时候,走到集上,集都散了。要不给你现做一碗?”
“会做?!”
“会,简单,谁都会。”
“嗯,算了,算了,我瞎说呢,肚子都吃撑了,什么也喝不下了。”
真不好意思再叫家人忙,可又惦着舍不下。
“……嗯,那酸辣汤是什么味呀?”
“酸辣汤味儿呗。”
“你跟俺大爷都挺怪,如今啥好吃的东西没有,要吃那酸辣汤!”
“那东西,还真是好吃呢……”大家纷纷说。
心里又惦着酸辣汤,肚子又确实撑得没地方,于是就想,反正就是酸辣汤味儿,假装已经喝了吧。比方,刚下火车,坐在车站外边的小摊上吃了点啥,抹抹嘴去了,到最后一问,原来那就是酸辣汤呀!编一个喝酸辣汤比喝嘴里不更有想象的乐子吗?可不管怎么说,瞎编一段也好,真喝上一回也好,反正喝不出爸嘴里那味儿……
小伟从厂子里赶回来,站着,吃着煎饼,含含糊糊说谁把村里的电承包了。
“真的吗?!”我问。
“可不是真的咋的!我进村的时候,瞧见人家把那个坏变压器拆了,正往拖拉机上装呢,说是送临城修,修好了就送电。瞧人家这致富路子,想得还挺聪明的。包电!”
“真是,咋又叫他给想着了!”二弟眼巴巴地赞叹。
“嗳,听说,李小文儿前两天回来了。”大嫂突然说。
“是吗?”这么巧!”我等会儿看看他去。”
“你看他做啥?”大家都笑。
“就是想看看嘛。”
真的,我真不知干吗想去看看这个人。
“李小文儿走了。”二弟说,“他从来不在家久呆。那是他女儿的家了。听说人家李小文儿现在在外边混得可好呢。在好几个地方都开了小铺……”二弟又是一副眼巴巴的样儿。
叔不议论,守着他的太师椅喝酒。哪怕够不着地桌上的菜也不离那窝儿。我带来的汾酒,一瓶已经见了底,他又伸手去摸第二瓶,开了盖,倒在从来也不兴洗刷一下的小酒盅里,喝水似地喝。土褐色的脸透出红来,脑门子上有汗。
我叔就是我叔。
一辈子干活,一天不歇,什么活儿都干。不论什么潮流,叫干什么,就能学会干什么,他不偷、不抢,公家便宜不占,他就是本分的农民。连他的女儿也不出他的大批。解放时是个中农,现在呢,是个中溜儿,难道,中农真有个中农的性格?
本分是我叔的美德,也是他今后的难得大发家的障碍吧?我想,可像他这样的农民,要比那赵广玉,李小文多得多……也许,是我这城里人,把致富的事听得太易了……
景全说:“那汾酒是名酒呢”。叔听了,忙把酒瓶盖盖上,用手砸死:“留着,留着,等来了客再喝,就说是我侄女带来的。”
我有点儿心疼,我就愿让我我叔自个儿喝!
……
吃了饭,照相。妇女们都紧忙着换衣服,婶又梳一回她那扁扁的、光溜溜的纂儿。打扮齐了,站出来一看,我连声嚷嚷:“不行!不行!我这是彩色卷儿呢,这样子都浪费啦!”平日里穿得花花绿绿,挺时兴的,到要照相的时候,个个全是蓝制服!
谁也不肯去换衣服,都希望别人穿花的,自己穿得板板正正、严严肃肃。照相,总是个正事。于是,我说:“我这个相机呀,不一般的呢,照完了,立刻就出人,穿得越漂亮,笑得越自然,越好看,不信,你们马上看!”
说着,把小孩子们拉到一堆儿。孩子们穿得花,站一块儿,我手里一按,“哗”,从相机后面出来一张胶片。
“你这是什么行子?”“这上边什么都没有呀?”……
“别急,别急。”一次成像的胶片出相也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故意把胶片在身上擦了擦,然后,拿出来:“看,注意看,看见一点儿影儿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人影儿渐渐清晰起来,五个五彩的小孩儿!
全家人立刻热闹起来,你争我抢地看。
“快换衣服,太阳就要下山啦!”
姐、嫂都跟妹妹借花衣服,婶呢,又换了一件衣服,还是蓝的。小弟穿他染料厂的劳动布工作服,领口是敞着呢,还是扣上,老人和年轻人意见不一致。凤鸾穿得花,还背上个塑料小书包,穿上双高跟鞋,我不敢打击她,不告诉她那鞋后跟照不上。景全死活不肯往一块儿站:“我笑不好,憋了镜头……”“那好,你来按!”“快快,站好,笑!”
有影儿了,出色了,清晰了。
一张全家福。
我坐在小板凳上。有点累。想,要赶夜车呢。可能没有座位,可能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白鸡“泼拉拉”飞到枣树上,在房顶那么高的树枝上站着。二弟推出他那辆车,在打量,转身,又进屋,拿出块小孩毯子捆在后架上。
“姐,你咋啦,想家了吧?”小传问。
“没有,歇会儿。”
“就是想吧?”小伟说,“那么好的家咋会不想,像咱这样儿的破家,才不用想呢。”
“小伟,那是谁呀?!凤鸾大叫,“是谁去上海学技术,没去一个月就想娘,想煎饼,想得直哭,直哭。那是谁呀?”
一家人送我出门。
“给你爸捎好儿。”
“儿,再来呀。”
“妹,慢走。”
“姐……”
一些临分手的老话。
我回头应着,看见黄昏中的门口。夕阳从门洞那边透过来,洒亮了半个门洞,抹金了一溜草的檐,点透玲玲珑珑的榆树尖;这半边全在长长的影子里,门板,地面,榆树干和老黄牛……
心突然受不住了,赶紧走到最前头,把所有的话收在耳中,只管脸朝前一个劲儿走,一个劲儿点头。习惯了的,冷静的那半个心问自己:怎么了?究竟为什么?出了什么事?难道,从这里上路,真是去流浪?难道前边那么远,不知有什么在等你?
不知为什么。
只是管不住流泪,哭得好伤心,想站下,把所有的泪都流个干净,真想!还是只管往前走。
走到巷头,擦着眼回下头,一家人默默地跟着我走。拐过弯,走到村口,再回头,全家都站在那儿。天暗了,能从蓝的、白的、花的衣服上辨出人,看不清脸。
走到村外,再回头,看不见脸,看不清人,蓝的、白、花的,隐隐约约,一动不动。
这里不是我的家。
这里在变着,连那个门口,那头老牛,那棵榆树也要消失,终要变成另外的样子,然而,我确确实实地知道,那黄昏时分的老家门口将永远在什么地方牵系着我。
坐在二弟的车后边,抱着东西,颠着,走过初夜的庄稼地、灯光闪烁的工厂和缓缓起伏的山。
孤山孤山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督;
娘娘都督都没出,出了一窝箍漏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