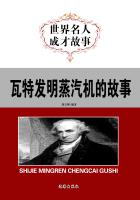到目前为止,俞鉴的演艺生涯(通称艺龄)在我国戏剧女武生中是持续最久的。从四五岁在旧戏班串演童生开始,直到六十二岁“收山”(六十九岁时,她还演过一出折子戏片段),俞鉴的艺龄长达半个多世纪。
与俞鉴相濡以沫五十载的老伴儿,同是从事京剧艺术的苏玉飞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总结了一条经验——一般戏剧女演员都是“红在婚前,倒在婚后”,但俞鉴是个例外,她不但婚前“红”了,婚后也没有“倒”。
听完二老的故事,笔者即兴总结出“三对”,说俞阿姨这辈子做对了三件事——参军参对了,入党入对了,嫁人嫁对了。
老两口听后,深情相对,默默无语,眼中似有晶莹物,但没有流淌下来。曾经沧海,他们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而今已度过金婚之年,仍恩爱如初。
笔者又乘兴追加一句——“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并说不妨作为本章的标题。苏老立刻把这句话写在家中电话机旁的记事本上,看样子颇为首肯。
女人究竟该嫁什么样的男人,坊间流行的主要观点:一是嫁自己爱的,一是嫁爱自己的。依笔者之见,与其嫁“自己爱的”或是“爱自己的”,倒不如嫁个“心疼自己”的。换句话说,对一个女性而言,只有从“心”里“疼”你的那个人,才是你应该嫁的——病榻前送饭、递药的人,远比病愈后送玫瑰花的人来得实在,来得可靠。
苏玉飞便是“心疼”俞鉴的那个人。
苏玉飞是遵义人,1948年参军,工武生,曾在湖南益阳“新舞台”学戏,师从盖玉亭。常扮的角色有《四杰村》中的濮天雕等,后来还创作过剧本。俞鉴参军时,他是团里的通讯员。
刚参军那会儿,俞鉴一不高兴就坐在排练的桌子上,板着脸,撅着嘴,谁也不搭理。
一见她这样,苏玉飞立刻来到她身边,关切地问:“俞鉴同志,又不高兴了?是不是又挨批评了?批评两句怕什么,这是帮助你认识问题、提高思想,把你那‘角儿’脾气改过来。”
那段时间,“逃跑未遂事件”刚过去不久,俞鉴隔三差五挨“批”,这对她原本波动的情绪来说,犹如雪上加霜。领导总是批评她有“角儿”思想、名利思想,“你当上解放军就要为兵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你想的老是角儿、名利呀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种话她压根儿不爱听,听了就生闷气。奇怪的是,只有苏玉飞的话她听得进去。她觉得这位同志说话态度比较柔和,也比较中听,他总是用老同志的口吻关心她;不像分队长,动辄拿“就是要克一克你这‘角儿’脾气”这样的话来压她,太生硬了,她实在接受不了。
她开始注意他了。
在团里的年轻同志中,苏玉飞是最爱学习的一个。下部队演出,其他年轻人又说笑、又打闹,他一个人钻到一边又看书、又记笔记;他写诗、写文章,在战友中享有“诗人”之誉;他在联欢会上跳一段秧歌舞,显得还挺活泼;他爱打抱不平,遇事爱动脑筋;他很少盲从,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
一个人身上集中了这么多优点。俞鉴想:我以后找对象就找这样的年轻人。
她羡慕他有文化。小时候父亲让她上学,她想学戏;满师后她想上学,母亲又不允——她太仰慕有文化的人了。
他也在注意她。
在苏玉飞眼中,俞鉴倔强、率真、开朗、朴实,对人对事从不藏着掖着,更不以金钱、地位、衣貌取人。她好胜的天性、直率的性情、心口如一的品格,这一切都让他喜欢。就连她那凡事爱“较真儿”的小性子,急鼻句鼻句的“臭脾气”,在他眼里也算得上“可爱”。
一次,在拥挤的汽车上,俞鉴正巧站在苏玉飞身边,便主动和他打招呼。又一次,全团同志一起去看苏联电影,她带了一把雨伞,回来的路上下起了雨,她撑开伞,招呼苏玉飞:“你别淋着,跟我打一把伞……”
从注意到好感,从欣赏到爱慕,这一切来得那样自然,那样顺理成章。令人陶醉的爱情就这样悄然而至,不知不觉来到两个年轻人心间。
部队到大成岛演出,离家很近,母亲带着妹妹到驻地来看俞鉴。苏玉飞知道她家境困难,默默掏出自己攒的五块钱,说给她母亲作回家的路费。
俞鉴不要,苏玉飞说:“就当是借给你的,以后有钱再还我就是了。”
苏玉飞也是苦孩子出身,他想,组织上提倡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像俞鉴这样一个演员,在旧社会里受了十年练功之苦,参军后家里没有了生活来源,我怎么能不帮她呢?苏玉飞不沾烟酒,除了爱吃点儿糖,平时没什么开销,他是心甘情愿地帮助她。没想到他却为这件事受了批评——部队当时不许谈恋爱,给女同志“送钱”的举动有“恋爱”之嫌。
后来,苏玉飞看到陈沂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说,部队京剧团将一律转业地方。苏玉飞找到俞鉴商量,说他想改行,到文工团去搞舞蹈。俞鉴表示支持,她觉得苏玉飞身板太瘦弱,在京剧上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到了文工团,说不定还能干出点儿名堂来。
不久,苏玉飞果然调到了军区文工团,但他每个周末必回京剧团一趟。他心里揣着个小秘密——惦着她呢。团里的同志见了他问:“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想你们,回来看看你们。”只有俞鉴心里明白,他是来看她的。
文工团在西湖边柳浪闻莺的一座三层小楼里,苏玉飞每天早晨都在楼下练功。一天,他看见一个人从楼上下来,对他说:“我已看你练了三天功,你的架势不像搞舞蹈的。”
苏玉飞老实承认自己原来是搞京剧的。那人问他为什么改行,他说看了陈沂的文章后,觉得京剧没前途,都是些蟒袍玉带的旧东西。那人批评他的想法不对,是民族虚无主义;又问他是不是青年团员,向他打听京剧团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志是总政实验京剧团导演刘元彤,这次是特为调京剧团进京来杭的。
两天后,刘元彤特地来找苏玉飞,说:“你身架、功底都不错,不干京剧可惜了,将来还回京剧团吧。如果调你去北京,你愿不愿意去?”苏玉飞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刘元彤记住了苏玉飞,也在无意间成就了他和俞鉴的姻缘。
这就说到了俞鉴那次“偷偷去杭州”的事。当年在上海做完整容手术,医生让她一星期后再到医院拆线。她想,我干吗不利用这段时间到杭州去看苏玉飞呢?
说走就走。俞鉴来到火车站,上了一列去杭州的列车——她没有通知苏玉飞,那时电话仅限于地方领导和军内首长,极少有私人电话,且是人工接转的交换机,她没有办法通知他。
那个年代,沪、杭之间乘火车单程需要四小时。这天下午六点俞鉴到了杭州,这座城市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那样熟悉。想起当年在车站的宣传画上看孩子跳绳、为哪吒找“相”的情节,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俞鉴在车站旁边的馄饨店里吃了碗馄饨,然后先到新华电影院去看望一位叫何健的老同志。这是她的“迂回战术”——曲线探情郎。她不能直接去找苏玉飞,那样别人知道了会说闲话。
从何健处出来,俞鉴才往文工团去,到了那里天已黑了。她不敢走前门,便来到文工团后门,说找苏玉飞,值班大爷说,苏玉飞到杭州人民大会堂演出去了。
俞鉴急忙赶到大会堂,绕着围墙,一圈一圈地转悠,一边等戏散场。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看见苏玉飞急匆匆地向她跑来。
原来苏玉飞演完戏回到文工团,听门房大爷说有个女同志找他,苏玉飞知道是她,他知道她是急性子——一定会到剧场外边等他;也知道她是“死心眼儿”,见不到他,一定会在一个地方“傻等”。
“你怎么来了?这么突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苏玉飞见俞鉴身穿布拉吉,戴着墨镜,背着黄挎包,吃惊地问。
俞鉴满心欢喜,向他说明原委,又说:“我是偷着来看你的。”
“你胆子太大了!从上海一个人跑到这儿!现在这么乱,你就不怕让坏人拐跑!”难怪苏玉飞会担心,那时的女孩子很少单独出门。
俩人又商量了一下苏玉飞去不去北京的事,一致的意见是暂时不去。第二天一早,俞鉴就离开杭州,回到了上海。
刘元彤回京后,通过南京军区发了调令,调苏玉飞和另一位拉京胡的同志去北京工作。调令上说,北京要成立一个京剧团,缺少武生演员骨干,但没有说明是俞鉴这个团。
这次调动没有成功,浙江军区职工科一位负责同志说,苏玉飞刚到歌舞团,过一段再说。几个月后,南京军区再次下达了调令。
俞鉴回到北京,正赶上部队扫盲,开展文化学习。她认了不少字,还学会了写信,半个月和苏玉飞互相通一次信。那时她和旦角演员高玉秋住一间宿舍,晚上熄灯后,她还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亮,偷偷地给苏玉飞写信。高玉秋纳闷地问:“俞鉴,你学文化怎么这么积极啊?”她哪里知道,俞鉴是在给苏玉飞写情书。
苏玉飞在信中告诉俞鉴,总政已两次调他去北京,目前他仍在全力“抗上”。俞鉴赶紧回信,让他千万别来——她还是觉得他不适合从事京剧。
如此来回“拉”了几次“锯”,苏玉飞写信说他“扛”不住了。要是再不走,连团长都要为这事背处分了。
1952年8月,苏玉飞终于奉调来京,大家也慢慢知道了他俩的恋爱关系。恋情公开后,俞鉴私自去杭州探“情郎”的事情自然败露了,有人跟她开玩笑说:“你跑到杭州哪儿是去看老同志啊?你是看苏玉飞去了!”还有人说:“苏玉飞对你不合适,这人很滑头,将来弄不好要甩掉你的。”
领导也找她谈话,劝她不要急于成家,“乌兰诺娃为了跳舞,三十岁才结婚。你很有前途,我们不希望这么早就让婚姻绊住你的腿……”
她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晚结婚可以,但是我不放弃他,跟他跟定了!”
领导说服不了俞鉴,又找苏玉飞谈话:“现在俞鉴的演出任务很重,你们俩的级别都不够谈恋爱的资格。”部队规定营职才能谈恋爱,他俩当时都是排级。
苏玉飞的回答是:“别的我不管,国家有新婚姻法,不管军队还是地方,都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再说我和她现在只是朋友,还没到你想象的那种程度。我保证绝不影响她的工作,支持她多演出,多作贡献。至于我们的关系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将来的发展……”
苏玉飞不愧是部队里的“秀才”,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无懈可击。领导只好表态说:“那好吧,只要不影响工作,我就不干涉你们。”
1956年11月,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马拉松,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这一年,苏玉飞二十五岁,俞鉴已整整二十八岁了。
结了婚就意味着开始“过日子”。他俩建立恋爱关系之初,苏玉飞首先想到的是俞鉴从小学戏,吃了很大的苦,受了很多罪,很不容易。他心中默想,如果将来两人能成为夫妻,自己一定要好好爱护她,决不能影响她的艺术。如今成了一家子,苏玉飞终于等来了名正言顺地“心疼”俞鉴的机会。
在家庭生活中,苏玉飞对妻子处处体谅、处处包容。俞鉴从小学戏、演戏,既没有做过家务,也没有这个兴趣,所有的家务活儿,母亲在世时全靠母亲,母亲去世后由苏玉飞一手承担。
在俞鉴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是凡事让着她。丈夫脾气好,自己脾气急,可他从不计较她的态度。拿一件很小的事情来说,家里刷完房子挂装饰品,活儿都是苏玉飞干,但只要俞鉴觉得哪一件东西挂得不是地方,她觉得不满意,就要换地方。苏玉飞任劳任怨,说换哪儿就换哪儿。
团里分成两个队到外地演出,他在一队,她在二队,一别几个月。完成任务回到家,俞鉴想:戏里的青衣、旦角都要伺候男人,我虽是演武生的,也得学一学,尽一尽妻子的本分。于是她端来一盆热水,说:“苏玉飞,你洗洗脸,我给你擦擦身子。”这是婚后她第一次主动照顾丈夫。
苏玉飞受宠若惊:“你下次不要给我打水,这些活儿你都别给我干,我自己来。”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不仅如此,他还要照顾妻子和这个家。平时,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从不让妻子动手。
如果说一般的“心疼”在恩爱夫妻之间不难做到,那么另一种“心疼”就需要境界了。俩人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最让俞鉴感动的是在过夫妻生活这件事上,丈夫最体贴她。到了晚年,她感慨地说,假如丈夫在这方面不够节制、对她不够体贴,那她的事业早就完了,必然会“倒在婚后”,更不会有后来延续一生的辉煌。
作为妻子,在这一点上俞鉴非常感激丈夫,她甚至觉得自己做得很不近人情。年轻时,俩人一接触就有孩子,当时又没有很好的避孕手段。她演出任务繁重,体力消耗很大,经常以累为由,拒绝丈夫这方面的要求。今天回首往事,俞鉴才意识到,为了事业,自己牺牲了许多做妻子的义务,在这方面她一直觉得有愧于丈夫。而他呢,始终说不出口,始终自觉地克制着自己的欲望。
相继有了三个孩子后,出于对俞鉴的爱护,马玉槐同志曾建议苏玉飞做绝育手术。他答应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说实话,对于这件事,苏玉飞内心是有顾虑的。他是武生演员,看到团里有的男同志做绝育手术后影响了身体,他担心自己从此不能再上舞台;再者,假如自己真的做了绝育手术,万一发生“婚变”怎么办?倒不是担心妻子会变心,对俞鉴的人品和秉性,苏玉飞自信了解颇深;但他是个心细如发的男人,女人的心是那样捉摸不定,现实中有的家庭看上去过得好好的,不是说分手就分手了吗?他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但这念头只是在他脑海中闪了一下,他同样说不出口。
俞鉴仿佛看穿了丈夫的心思,说:“还是我做吧。”她到医院上了绝育环,但身体不适应,流血不止,最终还是她做了绝育手术。
她脾气急,他性子慢,俩人的性格正好互补,平时发生点小摩擦,他也总是让着她。
三十年前她闹过一次“离婚”。起因是一天晚上苏玉飞下乡演出回来,她正和孩子吃零食,扔得满地都是果皮、果核。那天家里本来充满喜气,为迎接丈夫回家,俞鉴特地安排包了饺子,还对孩子说:“给你爸留着,让他回来吃。”
苏玉飞推开门,一看家里又脏又乱,皱着眉头发起了牢骚:“地这么脏,你们怎么搞的?”
一句话把俞鉴的火气激了上来。那时她正值更年期,极易烦躁,苏玉飞这一埋怨,急脾气的俞鉴心里更烦,她气呼呼地说:“你哪是嫌家里脏?是嫌我脏啊!你才出去几天就嫌家里脏,我以前去北京开会,在外面吃的、住的都比家里强,我回来怎么从来不嫌家里脏?行,咱们离婚吧!你写离婚书,我签字,孩子都归我!”
当时苏玉飞是团里的业务科长,当晚有位同事来找他谈工作,走到门口,正好听见俞鉴在屋里发脾气,就没敢敲门。
接下来,俞鉴每天催丈夫写“离婚协议书”。
“我们有大的原则问题吗?都出什么问题了?没有原则问题,我写什么离婚书?我就是说了一句嫌家里乱了,我犯了什么错?”苏玉飞心平气和,一点儿不生她的气。
“甭管有大的、没大的,我怎么从来没嫌过家里乱?我就是想不通!”她不理这个碴儿,一次次跟他犯“浑”。连着逼了他三天,他一直拖着不写,慢慢跟她讲道理,她的气也慢慢消了。
1977年,俞鉴的母亲患了结肠癌,手术前,医生让家属签字,俞鉴和妹妹签完字,非要苏玉飞也签。苏玉飞说:“你们俩签了就行,我又不是直系亲属,就不签了吧?”
“你不签字咱就离婚!妈妈在咱家做了这么多事,三个孩子都是她老人家带大的,你得有点良心啊!”
俞鉴的“死心眼儿”又发作了。她执拗地认为,苏玉飞只有在手术单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才是诚心诚意地抢救母亲——女婿如半子,在她心中,早已把苏玉飞当作母亲的儿子了。
在俞鉴的“逼迫”下,苏玉飞又一次妥协了。
母亲从小寸步不离地守着俞鉴,后来也一直跟俞鉴一家一起生活。虽然脾气不好,但老人家像苏玉飞这个女婿一样——从心里疼女儿。为了不影响俞鉴的事业,来宁夏前,母亲把京平带回老家,孩子两岁时祖孙俩才一起来到银川。自打母亲来后,买菜、做饭、洗衣、带孩子……家中一应杂务都由老人一手承担。
母亲这位个性极强的丈母娘,偏偏遇上苏玉飞这个性格内向的女婿——不爱主动接触人,也轻易叫不出“妈”这个字。
一次母亲跟俞鉴叨叨说,苏玉飞不爱叫人,没礼貌。俞鉴便向苏玉飞转达:“我妈对你有意见,嫌你出来进去的不爱叫人。”
苏玉飞立马表态:“叫妈,那有什么?你看着吧,我会叫的!”果然,从此他起床一声“妈”,出门一声“妈”,下班回来又是一声“妈”……把老太太叫烦了,用宁波话抢白他:“叫、叫、叫,叫啥系!”
平时,母亲经常暗中观察苏玉飞对俞鉴是不是真心爱护,观察得相当细致。最后,老太太下结论说:“别看苏玉飞架子大,清高,对老婆子还不错,跟小花脸儿似的。”随后就给苏玉飞起了个外号“小花脸儿”(京剧行当中的文丑)。
母亲去世后,安葬在新昌老家。有一年清明节,俞鉴夫妇和妹妹一起回老家给母亲扫墓。姐妹俩在墓前烧了纸钱,点燃一炷心香。轮到苏玉飞了,只见他站在岳母墓前,双手捧香,神色肃然地说:“妈,我代表全家老小来看您来了……”
俞鉴看看他,与妹妹目光对接,乐了——他那严肃的样子,让她想起一出戏——《十三妹》中的小生安公子。安公子是个书呆子,戏中有句念白,老家院对安公子说:“见人要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俞鉴觉得苏玉飞此时的神情与彼时的安公子,简直如一个模子托出来的,让她憋不住直想笑。她想,回老家一来是为母亲扫墓,二来可以到处看看家乡的变化,这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哭哭啼啼多没劲哪!可一看苏玉飞那直棍儿直立的样子,她和妹妹不由不笑。
苏玉飞用余光扫见姐妹俩笑他,正色道:“你们乐什么!你们哪儿是来扫墓,你们这是玩儿来了!”又道:“还是我跟外婆感情深。你们,有我深吗?”他那煞有介事的神情,让姐妹俩笑得越发直不起腰。
在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夫妻俩相敬如宾,凡事心平气和地商量,很少有过激和不洁的语言。
晚年中风后,苏玉飞对俞鉴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前几年俞鉴病重,憋不住小便,老是觉得内裤湿漉漉的。苏玉飞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不声不响,找出家里的软布和旧毛巾,缝了几个垫子,两头缝上固定的带子,给妻子垫在内裤上,铺平弄好。俞鉴深受感动,说这是一般男人根本做不到的,自己的艺术生命,也正是在这点点滴滴的关爱中得以延长的。
在艺术上,苏玉飞对俞鉴的帮助就更不用说了。俩人从恋爱起就谈得来。俞鉴佩服丈夫的理论水平,她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苦于文化水平低,理论跟不上。丈夫帮她总结、整理出武生行当的经验和几十年的演出实践,俞鉴的两篇论文《我怎样学武生》《浅谈京剧武生艺术》,都是在丈夫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
口渴时端一杯茶水,焦躁时递几瓣剥好的橘子……年近耄耆,苏玉飞对俞鉴仍是这样体贴入微,一如既往。五十年了,生活上他从不要她为他付出,对她的体贴、关爱始终如春雨一般,润物无声。
光阴似水。如今,年轻时的浪漫爱情和青春激情在岁月的浸淫下,早已化作相依为命的亲情和无以回报的恩情,浓似酒、淡如菊。在老两口的影响下,三个儿女也都团结友爱,兄妹情深。
有了苏玉飞这位身兼丈夫、父亲、祖父、外祖父多重身份的榜样,儿孙们自然明了他们的母亲、奶奶兼外婆——俞鉴在家中的地位。
一次家人开玩笑,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咱家谁是老大?”小外孙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奶奶是老大!”
全家人都为这天真无邪的童稚妙语开怀大笑,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