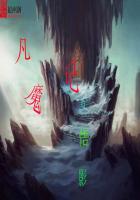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家的被神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面对由于建国后历次运动造成的文坛动荡而导致的文学创作一片荒芜景象,一旦出现了一些向文学回归的作家作品,批评家们就迫不及待地予以命名、无限拔高地予以褒扬,导致了部分作家作品的被神化。不客气地说,这些作家作品的被神化是文革后惯性思维的一种必然。中国人喜欢走极端的思维习惯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销声匿迹,当满目疮痍的文学园地在新时期文坛突然涌现出了这么多迥异于红色经典的作家作品时,批评权威们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他们给这些作品命名了伤痕、寻根、新写实等等煞有其事的名字,把这些作家作品放进一个个筐子里面,以便于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写出引导潮流的当代文学史。这种神化思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后期,先锋文学出现以后,也命定在所难逃地被神化、经典化。
在这个神化产生的过程中,余华是比较突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判断若放在十年以前,恐怕有不少余华迷会毫不客气地指责笔者武断,但现在,当余华把自己历经十年磨出的“利剑”《兄弟》抛出来以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余华作为先锋文学的突出代表这一点上确实被一些庸俗批评家神化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余华的被神化不完全是批评家的愚蠢所致,更重要的是余华作品的模糊性和虚伪性,遮蔽了这些人本来就月朦胧影朦胧的眼睛。以至于把余华神化为先锋文学的最高成就取得者,俨然成为先锋文学的“超男”,直到被神化到最有希望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现在,余华的《兄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批评家的悲哀,也看到了被神化的余华的悲哀。
就余华的创作来看,他的所谓先锋,只不过是受西方小说影响而仅仅在创作形式上显露出来而已,在思想上,他与当时的寻根、伤痕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把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的话,简直就是模仿大人行为的小儿科了。重新解读余华的作品尤其是刚出炉的《兄弟》,我们不得不很无奈地面对这样一个无情事实:余华写作功底很不扎实,他的写作资源很匮乏。尽管余华有着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叙述力,但这些掩盖不了余华这两个致命缺陷。余华的作品之所以一味地充满那么多的暴力和血腥,他写作的语言之所以枯燥无味,都和他的写作基本功不过关和写作资源匮乏有关。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余华,对一个作家下断语要联系他的生活实际。
众所周知,余华是由牙医改行写小说的。在这里,笔者并没有强调非科班出身就不能写作的意思,有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是半路出家的。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言,转行原本不该对余华的小说写作构成什么问题,只是在他从行医到写小说,太早太快地身不由己地陷在了来自外部的热闹与喧哗之中,甚至于没有时间好好地练一练基本功,没有来得及先过一下“匠”关。吊诡的是,文坛也没有给余华一个踏实写作的机会,不但牵强附会地解读余华的作品,还无节制地赞扬其写作的先锋性,包括对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过度拔高评价,把余华其实并不成熟的写作置于喧哗与热闹之中。
余华写作资源的匮乏主要表现在他写作兴奋点的单一,对文革的深刻记忆几乎成为余华叙事的一大法宝,他几乎将自己的所有作品都置于文革的大背景之下。实事求是地说,就余华的写作特点而言,他的所谓零度写作和暴力嗜好的确适合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性的丑陋与残暴没有任何一个阶段达到比文革更充分的暴露程度,任何变态、扭曲,只要放到文革的背景当中,都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余华对文革的认识,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不是停留于红旗、口号、纪念章、游行队伍、毛主席诗词这些表面化记忆(代表作品如《活着》),就是简单地将人性划分为单纯的善恶(代表作品如《兄弟》),余华没有将对文革的反思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哪怕一点的人文关怀。余华写作所追求的一直都是单纯的阅读效果和感官冲击,他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力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在让小说好看的同时也必然会降低作品的批判力度。
余华写作资源匮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小说作品精神内核的单调乏味,在余华的作品中,一直有一个少年的形象,这个少年形象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一直伴随着余华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这个少年形象和余华的三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那个自我疗伤的少年,《活着》中苟且偷生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忍辱负重的许三观遥相呼应,坚守着恒定不变的鸵鸟式的逃跑姿态。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感觉到的多是阴冷、愤怒、冷漠,余华将愤怒化成了冰水,在作品中流成了死寂一般的冰川,阅读余华的作品,你只感觉到冷,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也随着他的作品变得冷漠,最后感受到的是人生的荒谬。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余华十年磨的“剑”——《兄弟》,看看这部作品是否体现出了余华对自我的超越。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在《兄弟》中,余华不但没有对自己实现超越,还不可思议地表现出了大踏步地倒退。出于对余华的敬重,《兄弟(上)》刚出来的那一段时间,笔者面对批评余华这部作品的汹涌澎湃,还想着怎么样为其进行辩解,自我安慰说等等下部吧,上部写得不好或许是余华有意为之的一种写作策略,故意把上部与下部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取得意想不到的对比效果。那就看看下部再说吧,也许精彩都集中在下部了呢?哪里知道等到看了《兄弟》(下),倒真是意想不到,意想不到下部竟然会比上部还差,而且差得十万八千里!
不久前,余华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谈到国内作家的写作,说大家都在多快好省地写书,出书,每年都出书,每年都畅销,起印数越来越高,10万、20万、30万,作家的身价一个比一个高,出版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你就是看不到几本真正值得期待的书。余华的这段话不知道是否有所指(据说被“赞扬家”誉为和余华一样的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的莫言,只用了43天的时间就写了55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平均下来一天要写一万多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余华自己的写作确实也没有逃脱这个指责,余华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兄弟》甫一推出,就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批评讨伐。批评的火力集中在余华无聊描写的过度泛滥(如一开始的偷窥女人屁股)和作品的支离破碎(上部和下部的巨大差别)上,有人说中国社会从来不会存在《兄弟》中所描写的景象,中国人性饥渴的表现从来都不会如此浅显。甚至有评论者认为:即使把《兄弟》当作色情小说都不够格,它没有美感、不提供诱惑,连最色情的人看了都引不起色情念头。如此说来,《兄弟》竟连地摊文学也不如吗?真不知道是余华的悲哀还是文学的悲哀。
《兄弟》语言也不被评论者所认同,“那是怎样的文字呢?没有文采,一点都没有,像白开水,索然无味,给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带来的只是懊恼,没有丝毫阅读快感”。更糟糕的是,余华对于批评界对自己的批评并不服气,他为自己辩解说“再伟大的作品也有缺陷”,“如果能找到一千个(错误)例子我就服气”,这哪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作家的风范?要知道读者是将余华当作作家里面的人尖儿呵护着的!“赞扬家”们是把余华当作最有希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的!
有一个例子,在这里也许能很好地说明读者对余华的期待:余华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场面十分热烈。书城的读者大多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如数家珍,面对余华的新作《兄弟》,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他们说,相信余华不会令他们失望。有位高中生一下子买了30几本《兄弟》,说是要送给他的朋友和兄弟们。这个事例一方面表明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余华的崇拜是多么盲目,另一方面也告诉了余华,写作要悠着点,不要对不住自己忠实的粉丝。
余华写出《兄弟》这样蹩脚的作品的确对不起重视他作品的读者,也让那些“赞扬家”们突然之间无所适从:余华怎么会写出如此拙劣之作?《兄弟》的拙劣终于让他们不能沉默,李敬泽、谢有顺、张颐武、陈晓明、蒋泥等纷纷起而讨之。
余华声称,《兄弟》要从“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对此,李敬泽评价说余华把过去40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简化成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余华终究还是暴露出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软肋,他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的作家。由于选择了不恰当的位置和路径,余华降低了他的志向、误用了他的才能,这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他一样会失败,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余华曾经洋洋自得于自己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写小说当然离不开细节,有了大量绵密的细节才能使人物性格立体化。然而在《兄弟》中,多的是如蒋泥所说的虚假的细节或者是细节的虚假,这些虚假的细节和怪异的缺少内在统一性的人物,将《兄弟》推上了三类小说的“宝座”。
细节的不可靠(已经有人在怀疑余华在一开始写到的厕所构造,什么样的厕所能够让李光头他们如此清晰地偷窥到五个女人的屁股?)是余华《兄弟》的一大硬伤,明明是60年代的中国语境,小说中却出现的“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1990年代才出现的词语。如此四面漏风的文本,怎么能完成“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的“光荣”任务?如此低劣的写作,怎么能成为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小说精品?倒是《兄弟》的畅销,在这里找到了注脚。
《兄弟》毕竟是余华十多年来在纯文学领域的名气转移到大众读者市场的产物,是跟随前卫作家转化成商业流行风向标的一种变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兄弟》的畅销非常自然,不是奇迹,大家对余华的期待太久了,哪怕他拿出的是一堆臭狗屎,人们也会蜂拥而至。遗憾的是,余华在吸引了大量的盲目大众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专业读者,正是这些专业读者,感觉到了《兄弟》对他们的愚弄,由此对其产生巨大的失望。
专业读者对《兄弟》的不满,还表现在对这本书的特殊出版运作的态度上。一部长篇小说分两次推出的恶劣行径是余华从先锋姿态大踏步走上平庸道路的又一表现。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排除出版方的介入或者直接运作,这年头,一切作品都得听从市场的安排,余华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余华《兄弟》的媚俗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算是为了巨额的市场利润,为了那不菲的版税,余华似乎也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操作出版的理由(也许余华早就准备好了迎接文坛的批评,他既然有勇气这样做,就得有勇气接受读者的批评)。有人将这种出版行为讥诮为文学以外的“行为艺术”,是在用文学以外的手段操纵读者方面。余华的《兄弟》算是走了一招“好棋”,尽管这是愚蠢自己和愚弄读者的“好棋”,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余华(和出版方)的刁钻。更有评论者认为,《兄弟》的这种出版形式,比它的内容更令人摇头。一部长篇小说被人为地——非不可抗力地——腰斩为两半分次出版,只是为了赶上书展而忽略读者的利益,这种行径多少有些恶劣。
这让笔者想起了刚出道时的余华,如果说那时候他是无意识地投时代之机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而今,余华分两次出版的《兄弟》则完全是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做”出来的“先锋”姿态,先锋作家余华也由此华丽转身成为了畅销书作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文学期刊界的权威刊物《收获》竟然也凑了个非同寻常的热闹,将《兄弟》部分章节作为长篇小说予以发表,等于是来了个中途搭卖,这也引起部分读者反感。
更为遗憾的是,作为与余华同样有才气而且成就曾经斐然的其他先锋作家,其作品也呈现出不断退化走上庸俗的迹象。比如莫言。他前期的写作特别是“红高粱系列”取得了很高成就,也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坚实地位。到了后来,莫言的小说越写越邪乎。尤其是长篇小说《檀香刑》存在着严重缺陷,其描写的爱情故事不可信、反人性,其屠杀场面、细节、气氛渲染上任性夸张及其流露出的与小说人物高度一致的品玩心态,其缺乏道德与心灵上的拷问、对杀人话题津津乐道等等都是有害于作品艺术性的。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言,这部小说表达的是怪异的、病态的、消极的快感,而不是温暖的、具有人性深度的人道主义情感;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檀香刑》中的人物也是莫言任性的想象和怪异的情感的牺牲品:他把人物变成了扭曲的影子,变成了一个苍白的符号。
凑巧的是,余华的《兄弟》也具备了这些特点,而且在对丑的、恶的、残忍的事情、人物的夸张而膨胀、集中又强化的虚假描述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到了《生死疲劳》,莫言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大笔挥就50余万字大著,无怪乎马悦然先生对他有这样的告诫: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到《生死疲劳》,它们有的是花哨的形式和结构,唯独缺少人道情怀、人性品位、现代性意识和深刻的思想境界。
余华也好,莫言也罢,其写作都是经验型的,感性充盈而思想、文化储备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在艺术上作进一步的提升。而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或者说将来有可能真正成长为文学大师的小说家,必须有自己的写作理念和思想,没有思想的文学大师是不存在。相较于莫言,余华没有像他那样早在《红高粱》、《檀香刑》等作品里就已呈现出自己的影子,余华早期的作品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轻易地看出他的致命缺陷早就存在,他缺少的是深厚的现代人文精神。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原谅余华们从先锋大踏步向庸俗“前进”的姿态了。不是他们不努力,是他们本来就缺少继续前进的资质。
由此看来,先锋文学作家的分道扬镳各走各路不是一件偶然性的事情,如果说90年代余华还能够混迹在先锋文学这面大旗下的话(在这面大旗下,有才气的作家和不懂写作的作家同样得到庇护,这面大旗具有强大的护短功能,一切变态失真、不合逻辑、无可信性、谁都看不懂的文学作品,都能在这面大旗下找到存在的合法性),现在他已经没有理由和必要继续呆在这个阵营里面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凡是反传统的不合常规的都是先锋派的时代了,后退二十年,余华只能是一个庸俗的畅销书作家。
余华的先锋写作从一开始就带有太多的投机性与虚伪性:他故作一种写作情感的疏离,其实是为了制造惊世骇俗的效果,拉近作品与时代流行精神的距离,刻意制造出高深莫测的探索谜题,其实是为了轻易地实现深刻,融入当下盛行的华语氛围。也许会有人反驳,不管怎样,余华的作品具有批判性,这一点不能否认吧。是的,如果没有看到余华在美国回答罗格斯大学读者提问的话,我们是可以相信他对时代的真诚批判的。但现在,我们没有相信余华的理由了。
据评论家蒋泥披露,当罗格斯大学的读者问余华:你的很多作品对中国现实批判得如此深刻,当局为什么还能容忍呢?余华回答:“中国当局、中国媒体也在逐渐变得更开明。前十来年电视报纸采访我,我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了胡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反正是不敢刊登的;到1995~1996年我发现不能那样放肆了,因为我说的“反动话”他们也敢照登!到现在更不得了了,我没说的他们也敢登!政府?政府才不管呢,政府没人读报纸看这些东西啊。”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余华具有自觉地对社会的批判性纯属误会,通过他的回答,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余华就像他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塑造的那个少年一样,是一个鸵鸟式的作家。
应该注意到,不仅是余华,当年的许多先锋作家们在新世纪以后,大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一种急躁心态,有许多在做着没有多少意义的挣扎。2004年,格非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并获得了2004年度华语传媒大奖的“杰出成就奖”;而马原则选择在为年轻一代作家命名的仪式中(2004年,马原命名五位80后作家为“实力派五虎将”并作序推介)来实现自己的重新登场;余华则以半截子新作《兄弟(上)》于2005年现身上海书展,再度引发吹捧。部分先锋作家的再度出山,虽然姿态说不上多么优美,但毕竟又闹腾出了自己的动静。如果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当年先锋作家而今的生存境况的话,会发现他们中有许多已经从文学的前台走上了幕后(如格非、马原到了高等学府教书)。这说明当年先锋文学作家整体风光已经不在。
我怀疑余华也许一直把先锋作家这个称号当作一个套子,他早就想把它扔掉了。当年的先锋,在余华这里,仅仅剩下花哨、变异的形式、结构,而没有了内容和精神底子。也许余华在一开始就被误读了,也许他根本就不应该归于先锋作家之列,余华作品所展示出来的暴力、丑恶、血腥、野蛮……只是符合了文革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也迎合了不明就里的一些老外们的审丑口味。余华的虚构作品只停留在对欲望、物质和狭隘的个人体验层面上,缺少对现实、对人类痛苦的关注,缺乏对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和价值信仰的关注。
正如恩斯特·布洛赫在《论文学作品反映当代的问题》一文中所说:
“……许多看上去倾听现实脉搏的人,只接触到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没有感触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流行的见解,所以在读者中造成他们写了时代小说的假象。他们也许能供人消遣,但一定是短命的……”布洛赫的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概括余华等先锋作家的写作。
余华的先锋写作带有很多的投机性和虚伪性,恰恰是这种投机和虚伪让作为先锋文学的余华收到了歪打正着的效果,也因此被相当多擅长于惊人之语的文坛“赞扬家”们奉为经典,不断地予以神化,而余华自己也在这种不断被神化当中越发地投机和虚伪,致力于血腥和暴力的营造,使自己的写作成为一种下意识习惯性的行为,没有信仰和追求,更没有人文关怀,只有自我膨胀的复制。
《兄弟》的出版加速了余华神化的破灭,余华由此转入一种新的成长状态,余华也因此面临着重塑自己的可能。与同为先锋作家大旗下的其他作家相比,余华有自己先天的优势,但他缺少真正的艺术追求与信仰,缺少杰出作家所应有的博爱精神,这才是导致他作品走上庸俗化的根本原因。
周冰心在《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发表文章,就余华油滑的人生观、投机的写作观、狭隘的世界观、浮泛的历史观、虚伪的道德观、病态的东方观、消极的人文观作了考察,并就他作品中不同程度存在的载道、代言、全球、忏悔、当代、忧患、人文、悲剧、中国、民本、自由、知识分子、挑战、省察意识缺失进行批判。周冰心指出,余华等先锋作家之所以在叙事、艺术、思考上都落入“惯性化、惰性化、消极化”写作,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普遍缺乏独立、自由表述的勇气,对民族内心灾难的省察意识,缺少对当代苦难经验的回望、民族意识、虔诚的宗教忏悔思维、强烈的代言人身份、深刻思考中国人普遍面对的经验场和肉体“驯化”过程的荒诞性等。这些作家一等到个人苦水经验倒尽,作为“作家”的“象征资本”也已聚累完毕,政府自会将他们都包养在大城市,给与锦衣玉食,给与一定职位,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阶层,自身再也没有更高境界的精神提升和叙述追求,当然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小说。如果余华也走上这样一条被体制“招安”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担心他还有没有重塑自我的可能。而现在,我们看到,从《在细雨中的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直到现在的《兄弟》,余华正在从一个先锋小说家逐步蜕变成一个通俗小说家。也许,就目前的中国文化环境,我们过高过早地要求余华有一个华丽的转身——进而重塑一个真正先锋的余华——依然还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笔者注意到,随着余华《兄弟》以特殊方式隆重推出,最近批评余华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这些批评大都表露出对余华的过度失望,而这种过度失望恰恰是建立在对余华的过度爱护基础之上的。即便是淬火出炉的备受争议的《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一书,我认为其用意也是好的。当然,对余华的批评,过于温吞水与过于猛烈偏激都是不可取的,但从良药苦口的角度考虑,对余华的稍微严厉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这些爱极而恨的文字能够促使余华猛醒,我想这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
我们期待着余华的再一次重塑,这种期待是忐忑不安的期待,因为我们不知道余华究竟还“余”下多少精“华”,但愿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