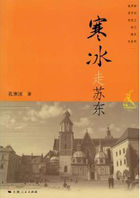一、百济遣使入唐概况
百济从武德三年(620)第一次入唐朝贡到永徽三年(652)灭亡前最后一次遣使,32年间共有27批次。和高丽使者入唐情况类似,绝大多数入唐使者的姓名不见于史载。但通过对这些使者入唐情况的分析,能以新视角来了解唐朝、百济以及当时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
二、百济王室成员充任入唐使者的原因
列具姓名的入唐使者——王侄、王子、太子——都是百济王室成员。百济王室成员充任入唐使者,与半岛三国之间的关系走向密切相关。
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三国,为了扩张各自的领土,很早就攻战不休。到了隋朝,在隋炀帝准备征讨高丽时,百济王积极响应,并派使者入隋请军期。然而当隋军真正攻打高丽的时候,百济却“严兵于境,声言助隋,实持两端”。不仅如此,百济还伺机派小规模兵力侵扰新罗。唐朝初年,百济对新罗的动武更加频繁。贞观元年(627)七月,百济王准备大举进攻新罗,收复被新罗侵占的领土。新罗王向唐告急,百济才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八月,百济王派出王侄扶余福信入唐朝贡。
百济向唐朝派出王室成员这样高级别的使者,表明对此次出使非常重视。其原因当和前月准备大举进攻新罗,后来得知新罗向唐朝告急而罢兵有关。百济意识到唐朝有可能对此事进行干预,故派出王侄为使者,为自己辩护。果然,唐太宗对百济和新罗进行了调解,敕书百济王:“王世为君长,抚有东蕃……忠款之至,职贡相寻,尚想嘉猷,甚以欣慰。朕祗承宠命,君临区宇,思弘正道,爱育黎元……新罗王金真平,朕之蕃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对王侄福信、高句丽、新罗使人具敕通和,咸许辑睦。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
此时唐太宗刚登上宝位不久,宫廷内部的问题还没解决完,对于蕃国之间的矛盾纷争也就采取中立政策,务求息事宁人。使者扶余福信即使想要为本国申诉,恐怕也没有机会让唐太宗真正听进去并为其解决问题。
贞观十一年(637),扶余隆入唐朝贡。他以王室成员的身份前往。百济遣扶余隆入唐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百济与唐之间有大海相隔,两国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所以百济不像高丽那样顾忌重重。派王室成员入唐,不但不担心被唐朝扣留,反而能够让唐增加对其的信任和好感。二是扶余隆乃扶余义慈之嫡子,当时的百济王扶余璋之嫡孙。按其身份,将来必将接任百济国的王位。在年少之时派遣其出使大唐,可以增加其阅历,更使百济给唐朝留下忠诚的印象,从而拉近与唐朝的关系。
有资料认为,公元637年入唐的扶余隆为百济太子,误。因为此时扶余义慈还没有当百济王,他才是百济太子,扶余隆为太子之子。公元641年,百济王扶余璋去世之后,义慈接任宝位,三年后,也就是公元644年才册封扶余隆为太子。又据记载:公元660年,唐讨伐百济时,义慈王和太子孝逃到北方边境地区,这似乎表明当时的太子已不再是扶余隆。然而,是否扶余隆的太子位置被扶余孝取代了呢?对于换太子这样重大的事情,史书上却没有任何记载,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另据《新唐书》载,唐军攻入百济时,“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百济太子为扶余隆而不是扶余孝。而且据《新唐书·百济传》所载,当时的另一个王子为“小王孝演”,即扶余孝演,非扶余孝。《旧唐书·百济传》也记载,当时的“太子隆、小王孝演”被唐军俘获入唐。可见,《三国史记》把扶余孝记为太子是错误的。
公元644年,百济册封扶余隆为太子。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百济太子扶余康信朝唐,则此扶余康信当即扶余隆。遣太子朝贡显示出百济对唐朝的重视,其背景应当还有以下原因:一是扶余隆在没有当太子之前,已经有作为朝贡使者的经历,对于朝贡事务比较熟悉,唐朝对他也不会陌生,而且这次是以百济太子的身份前往,更能引起大唐对百济以及扶余隆本人的好感。二是此时的唐朝正在准备大举征讨高丽,太宗皇帝即将御驾亲征,这对百济来说是个不小的震撼。唐征高丽的原因之一就是高丽侵凌新罗,而百济和高丽又常常联合攻打新罗,百济对唐朝的出兵不能不有所顾虑。但百济在与新罗战争频频的同时,善于及时向唐朝朝贡以表示恭敬,也就是说,百济这种外交策略在保护自己免受大唐制裁的同时,还能够尽量地侵略新罗,扩张地盘。这和隋炀帝征讨高丽时百济虽积极表态,但“严兵于境,声言助隋,实持两端”的做法实质上是相同的。一方面结好高丽,一方面又讨好唐朝,这是小国百济求生存并图发展的手段。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春正月,百济最后一次入唐朝贡。此后,百济一面与倭国通好,一面和高丽、靺鞨联合,占领新罗的大片领土,在政治上同唐朝的意志越来越远。同时百济王扶余义慈也荒淫无度,不纳忠言,终致唐朝和新罗毁灭性的打击。小国百济在数百年间审时度势,所以才能够在大国间的夹缝中保全并发展自己,当它一旦忽视了所面临的严峻现实,特别是与高丽联手欲灭掉新罗而开罪唐朝时,就完全背离了其一直秉承的持国方略,滑向了危险的边缘。而其统治者生活糜烂、政治腐败的现象,也与其先祖兢兢业业的持国态度相悖,不能不说与其灭亡也有必然联系。这或许就是“适者生存”规律在国家关系中得以体现的一个反面例子吧。
史载麟德二年(665)十月,唐高宗封禅泰山,刘仁轨率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唐高宗对此情况极为满意。而此时百济早已灭亡,所以参加此次封禅的百济酋长应是以象征性的爵称参加的。原百济王扶余义慈被俘入长安后“数日而卒”,参加封禅的百济酋长应是前百济太子扶余隆。早在龙朔二年(662),以战俘身份入唐的扶余隆被授予熊津都督官职,遣回本国统辖遗民,原百济旧地成为唐的一个羁縻府。麟德二年(665)八月,唐朝派专使督令新罗和扶余隆举行盟誓,企图让这两家夙敌和睦相处。主盟者在盟誓之后返唐。凭着与新罗多年的交往经验,扶余隆坚信,没有唐朝军队镇管,新罗必不遵守誓约,定会想方设法置自己于死地。所以史书说扶余隆“惧新罗,寻归京师”。扶余隆跑回唐都长安,适逢唐高宗的封禅泰山大典,封禅结束后就借势留在唐朝,不再回国。此后百济旧地不再有原百济王室成员维持统治,新罗更加大肆侵夺百济旧地。事实最终证明扶余隆对新罗的判断是正确的,新罗后来果然吞并了百济旧地,并与唐朝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不仅意味着唐朝安排的新罗、百济盟誓完全失败,也标志着唐朝对新罗的支持政策以此终止,同时表明唐朝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对新罗的政策,导致其陷于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