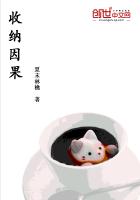(第一节)军阀统治下的京族
进入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各自为政,互不相属,为了扩充力量,对辖区内的百姓极尽盘剥之能事。防城各族自治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老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陈济棠家族的陈维周、陈济南、陈伟南、李培农(陈维周的女婿)等人,就是该县统治阶层中的实权者。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县政府的军、政、财权,勾结并扶持京族地区的官吏和京族的地主,对京族百姓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如地方官吏、民族败类陈汉光,于1947年至1948年间,多次窜到越南芒街乞求法帝国主义“支援”,从那里领取枪支弹药回来,在江平等地袭击游击队。伪江平联防主任、地主黄玉书,于解放前夕在江平京族地区组织反动的自卫队,与我地方游击队相对抗。1948年12月又指挥其保安团中队长邓从基,借捉共产党为名(当时已有游击队在山心等地活动),在山心岛上捉去京族青壮年共30多人进行威逼吊打,勒索钱财。国民党政府在京族地区还把山心岛的京族刘杰三安作县参议员,刘扬瑞安作国民党江平区分部书记,利用他们来达到控制京族的目的。
在行政管辖上,国民党政府在京族地区推行与汉族无异的保甲制度,但在具体实施上却带有强烈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意识,它把世代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的京、汉两族人民分割开来,实行“分而治之”,把山心的京族单独划为一保,而把与山心相邻的东西两头的佳邦、贵明的汉族又划为一保;把万尾岛中间村的京族和巫头岛的京族单独划为一保,(巫头为正保,万尾为副保),而把万尾岛的东头村和西头村的汉族又另划一保。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便从中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更为恶毒的是,对京族人民派的苛捐杂税特别重,“分配”的征兵征夫名额特别多,以此制造京、汉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佳邦的汉族地主龙振明和贵明的汉族地主陈振芝等人,乘机散布流言蜚语,多方威胁和恫吓,扬言要把京族“小孩拉去看牛,妇女拉去做老婆,男人杀光丢下海去”等等,致使这里的京族人民白天不敢露面,晚间则逃进海榄山去躲避。
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和土匪是“两位一体”的,正如万尾岛京族人民所说:“国民党的官就是匪,匪就是官。”如1948年12月,村长、保队副李世珍,勾结惯匪陈树廉洗劫万尾岛中间村京族人民的财产,把全村的牛、猪、鸡、鸭、衣物、被帐、鱼网、犁耙、粮食等,全部抢劫一空。并抓去京族吴世隆等人,从中进行敲诈勒索,扬言说不拿钱去赎就要把他杀掉。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巫头岛的京族人民洗劫一空等等。此外,国民党政府对海盗的行为熟视无睹,甚至放纵他们抢劫。所以,京族人民出海捕鱼时,经常遭抢劫,每年被抢去的渔网、鲜鱼,不计其数。例如1921年3月,万尾岛的何金发、武大哥等四人在海上捕鱼时被海盗抢去鲨鱼网一张,价值千元以上;1933年3月,万尾岛有一张百多丈长的大网,撒下海不久,就被海盗抢走。1945年万尾岛梁达茂等四人,在一次捕鱼中,再次被海盗抢走一张大网和五百多斤鲜鱼等等。海盗的猖狂抢劫,加深了京族渔民的苦难。
经济上,国民党政府对京族劳动人民的敲诈和掠夺,真是无孔不入。据不完全统计,在京族地区的苛捐杂税就有十多种。如:
(1)田粮赋税:每年每亩要交稻谷2斗;
(2)海税:凡出海捕鱼的渔民,一张大网一年要纳十元光洋,一张鲎网一年要交四元光洋,否则就封船封竹排,不准出海捕鱼。
(3)盐税:盐田收得100斤生盐,就要抽税一元光洋;
(4)猪税:凡养一头猪,要纳税一元光洋;
(5)屠宰税:宰一头百斤以上的猪,要纳税2。5元光洋;
(6)牛税:买卖牛只时,大牛要交五元光洋,小牛要交三元光洋;
(7)市场税:京族渔民挑鱼到江平虚镇出售时,每百斤要交纳市场税三斤鲜鱼;
(8)过秤税:凡是经过官方过秤的东西,每一百斤要纳税一勺(鲎壳制的,每勺约五斤),不足百斤的,要纳税半勺(二至三斤);
(9)竹木税:买卖一百元光洋的竹木,要纳税二元光洋;
(10)门牌税:每家每年交税一角;
(11)“身份证”税:每人每年交五元“西贡币”领取“身份证”,若遗矢申请补发时,要交手续费20元;
(12)自卫班米:规定每家每月要交一定数量的大米作为自卫班的粮饷;若有国民党的军队驻村或过境,则要加倍另交粮饷;
(13)联防米:江平于1947年设立伪“联防队”之后,每家每月要交纳联防米三至四斤。
征兵抽丁,更是京族人民的沉重灾难。最初三丁抽一,进而二丁抽一,到最后连单丁独子也无法幸免。1946年至1948年间,伪江平联防队多次进入巫头岛抓人当兵,其中最多的有三次达数十人。据调查材料统计,京族地区曾经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京族青年被抓去当过兵。征兵的人进村抓不到青年,就抓老人,连瞎眼的老太婆也不放过,借以勒索钱财或逼使逃征的青年回来当兵,赎回他们的父母。
在征兵过程中,各级大小官吏和保长等人,趁机敲诈勒索,弄得许多贫苦的京族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向国民党政府“申请”,领取“免征书”;贫苦的京族人民借债“申请”,被勒索多次,最终还是领不到“免征书”而被抓去当兵。如在1946年,万尾岛的武德贵先后被抽壮丁三次,被保长勒索了二百五十元“西贡币”,最后把仅有的一亩旱田也变卖掉。1947年,万尾岛的梁达成,先后“申请”了三次,花去一千八百元“西贡币”,最后还是被抓去当兵。万尾岛的李世丰因被征兵四次,被保长勒索了三千六百元“西贡币”,不仅变卖了十二亩坡地,而且还把女儿李亚留卖给地主为奴。结果被逼得上吊自杀,其妻子逃亡外地行乞,最后落得家破人亡。
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当地土绅对京族的渔民和农民的剥削也是十分深重的,除了缴纳各种高额的地租和渔箔租之外,还要为他们服各种无偿劳役,“租空地”(就是渔民给地主预交了渔箔租,要等到几年之后,才能实际使用)也是常见的现象。
总而言之,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京族劳动人民平日吃的是红薯、芋头、薯藤叶,荒月里只能以白榄果(俗名榄钱)、海菜、芭蕉头充饥。冬天没有被子盖,只有靠烤火度夜,穿的是破网和千缝百补的破衣、烂麻包,住的是里外透风漏雨的破茅寮。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京族的劳动人民,被迫卖儿卖女的三十七户,逃荒的一百一十六户,被拉夫抓丁的一百二十五人,无辜坐牢的七十五人……世世代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京族已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渔业经济时期,其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较为复杂。
经济结构方面,在京族三岛计有渔业生产、农业生产、盐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四种主要模式;阶级关系方面,农业上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渔业方面有兼营渔业的地主、富裕渔民、一般渔民、贫苦渔民、渔工等。此外,还有一些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主要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他们通过出租土地、渔箔、渔网及雇佣工人的方式进行剥削,而广大贫苦的京族人民只有依靠租用他们的生产资料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在其他社会机制方面,京族的婚姻由父母包办,同时将自己的婚姻生活寄托于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合八字”之上,往往造成许多婚姻上和家庭中的悲剧。由于京族严格禁止同姓通婚,而历史上的通婚方式又为族内通婚,因此,京族各村各姓氏相互之间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在居住上则表现为同姓集中聚居在一起。在医疗卫生方面,基本上无现代医疗技术可言,治病往往是通过宗教、巫术、迷信的手段加以处理,常常因此而延误医治,导致病情的加重或是病人死亡。教育方面,万尾、山心各有一所保立小学堂,但真正能接受学堂教育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只能接受家庭中传统的技艺及谋生手段的教育。除了仅有的每年农历八月初十的“哈节”外.很少有精神文化方面的生活。
历史上,京族三岛各村诸姓均未出现族长,只是同姓中辈分较高年长者拥有一定的威信,受到同姓族人的尊重,在关于分家财产继承等方面起到主持人或见证人的作用。各姓也没有形成共同财产,只是在历史上有过通过捐赠方式向哈亭和学堂提供的全村各姓共享的公田,如在《山心哈亭碑记》中有刘有庆、刘振彬向哈亭施田及《江平山心学校纪念碑记》中有刘族上户向学校“敬送”坡地作为学校操场的记载。
历史上形成的村中白事、哈节按“乡饮簿”①(京族男子年满18岁者可以进入哈亭参加哈节的聚餐,并将名字登记入薄,该薄俗称为“乡饮薄”)名册顺序轮流分摊任务和各家到哈亭求神许愿、还愿、祭拜同村先逝祖先,此习俗至今仍存。清明祭祖,除山心村刘姓到“大庄山”进行统一祭拜外,主要以各家单独到埋葬自家过世亲人的坟地扫墓的形式为主。(调查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