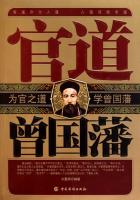禅宗或称"禅那",是梵语的音译,是止、观、禅那修行中的一种。菩萨的修行很有意思,有止、观、禅那几种修一种的,有修两种的,还有三种齐修的,又按修行的顺序不同而有分别,倒十分类似今天为白领量身订制的培训套餐。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秉承魏晋玄学传统,力倡良知的天机活泼,任运而为,蔑视权威,张扬自我。"五家禅"指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临济宗在"五家禅"中最具特色,在禅的思想方面和风格方面都不落俗套,讲究创新。该宗不仅在我国流传了一千多年,对唐宋及其以后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还对日本禅宗的开创和发展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禅宗大师中的确有呵佛骂祖、烧佛经、劈佛像的"狂禅"僧,但是这并不是一味的张狂,后人学其形而忘其神,就是禅宗被误解没落的一个原因了。"狂禅"的前提是已经开悟,证得空性。如果未开悟,未证空性,则罪过无量。"狂禅"的目的是为使学禅人破执著,不是为狂而狂,不是卖弄,不是自命不凡。"狂禅"的使用频率往往只是一次,并非总是这样,破执目的达到后,他们照样尊敬佛经、礼拜佛像。
一般来说,禅宗比较为人所知的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曹洞宗中的"默照禅"很少人学习。"默"指沉默专心坐禅,"照"是以智慧观照原本清净的灵知心性。临济宗中的"话头禅"及"公案禅"比较为大众所知,但容易被误解而只修习意义。
本质而言,"禅"的修行是纯粹的,以十分平常之生活,悟得大彻大悟之道,这点说来,没有强调"不立文字",也没有说"妙语生花"。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与道教在一定时期有抵触,但就哲学的层次而言,两者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以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禅师强调内心的自由,这和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思想是贴合的。道教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在禅的名义中占有多数,但不适合作为道教的一个分支,只能冠以外来的"禅宗"之名。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对禅宗的追捧,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点。
中国的禅宗是中国化的,日本的禅同样是日本化的。并不能简单地把日本遣唐使以及唐代的文化交流作为日本禅宗的开始。《今昔物语》的作者源隆兴说:"汉才虽微妙,但若无一点和魂者,可以说此心幼稚如死也。"日本对中西文化的融合上一直是自主的。日本获得外来文明的途径,中国只是其中的一条。佛教传入日本时间较早,与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教处于对立的地位,并没产生如道教和佛教的那种融合。时至今日,日本的神道教徒占信徒的大部分,也可见他们对于原有宗教和哲学的坚持。遣唐使的出现,可谓唐朝文化输出到日本的一个高潮,唐朝因"李姓天下"而推崇道教的始祖李耳,道家文化的传入可能才是日本禅宗兴盛的主因。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既好斗又谦和,不畏死而热爱生活。这种特质与日本的地域条件分不开,狭隘与生存的压力产生了焦虑,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做到佛教所言"四大皆空",也做不到道教的"无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使其性格坚忍,另一方面又追求与自然的协调。"菊与刀"的背后,日本所追求的"道"不同于中国的"道",乃是一种"极致之道",对美和死亡的追求都是如此。
在日本流行的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曹洞主知见稳实,临济尚机锋峻烈;曹洞贵婉转,临济尚直截。临济宗主要和幕府上层武士关系密切,而曹洞宗则注重在地方上的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这是所谓"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说法。禅宗的讷言和巧言正是这两者的体现。禅宗以寡欲为宗旨,与武士们提倡的廉洁操守也很相似。禅宗把佛教的教理与日常生活结合,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简单易行的方法,容易产生普及的效果。
但日本武士道的德,以忠孝、勇武、慈悲、礼让、勤俭为主,其中大部可能来自儒家。至于茶道等追求生活体验的态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极致之道",道家的思想占得多些。茶道的始祖陆羽的好友皎然称:"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陆羽的茶道本身是和道教的养生成仙之学紧密联系的。至于佛教的慈悲与隐忍,可能并不适合一个把生存之道放于首位的民族。追求"极致之道"的结果是能产生精致的文化,但终究离不了焦虑和迷茫。这是哲学体系无奈的缺失所致。
禅之初如春发之芽,是萌动和鲜活,是"答非所问"的自在。离开这点,禅宗也就失去了其本意。观浅草如茵,学老庄"坐忘",美则美矣,奈何淡了一切心,乃至慈悲心,不足衣食哪来谈玄机。离了平常道,"禅"就不再是禅了。
§§第二部分 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