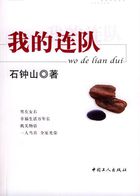云梦江子在窗外透进的昏暗光影里不停地颤抖着,她看清了眼前衣不遮体的一股血腥气的中国姑娘,就是白天在鱼巷子见过的那个酷象自己的渔女,所有疑惑和惊诧都消失了。昏暗中,那中国姑娘压低嗓门小声问:
“你是日本人?”
她嘴里塞着手帕,讲不出话,点点头。
“是你救了我?”声音里带着怀疑。
点点头,又摇摇头。
“噫,你能听懂中国话?”飞镖的利刃离开了一些,仍然是怀疑,“你为什么救我?”
云梦江子嘴里的手帕被轻轻扯掉了,她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
“我是日本军妓,跟你一样恨谷野次郎。我能救你——只要你一切听我安排!”
那影子痴呆了,仿佛她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鬼魂。为什么这家伙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而且会说中国话?难道是死在九泉之下,自己跟自己的魂魄在说话?
强烈的探照灯的光柱,在院子里的林荫中扫过来扫过去。一道白光透进了窗口,云梦江子拖着中国姑娘躲进了临窗的那堵墙的阴影之中。窗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日本警卫在树林里搜索,穿梭般走过来走过去。
云梦江子取下墙角洗脸架上的毛巾,提了半桶水放到中国姑娘面前,咬着她耳朵说:
“你赶快脱了衣裤抹净身子,藏到衣柜里去……”
她照办了。
云梦江子拿拖把拖净地板上的水迹,将她脱下来的破烂塞在铁皮水桶下面,上面压上拖把。她提着水桶和拖把,走出卧房,反手关上门,不慌不忙走进斜对面的卫生间。这时,警卫和闻讯赶来的宪兵,正在楼道那头逐屋搜查。她打开抽水马桶,将破烂的衣服赶快撕成布片,一块一块塞进马桶里,放水冲走。销毁这些“罪证”,费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把铁皮桶里的半桶血水倒进马桶,将拖把一起放在里面冲洗,直洗到见了清水,她才深深喘了口气。
嘭嘭嘭!
楼道里有人很凶地敲门。她急忙将拖把搁在门角里,给铁皮桶注人半桶清水,装做刚上过厕所的模样,再次扭开抽水马桶的水龙头,方才慢慢腾腾地打开门。
两个年轻宪兵端着枪一拥而进,凶神恶煞地瞪着她问:
“在这里干什么?”
她傲慢地回答:
“这还要问吗?”
“为什么不立即开门?”其中一个宪兵咆哮道。
“非常遗憾,这得回家问你母亲,”云梦江子嘲讽地一笑,“你母亲生下你的手脚,难道没生你的脑袋吗?”
那个烈性子宪兵举起了枪托,另一个宪兵拦住他,话语放和缓地问:
“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司令官邸情报秘书云梦江子!”她大声作过回答,提了水桶趾高气扬地朝门外走去。在门外她碰到宪兵队长吉茂。
“江子小姐,”吉茂一对贼溜溜的小眼珠瞪着她,有几分疑惑地问,“怎么半夜三更还没歇息?”
云梦江子犹豫了一下,跨前几步,放下水桶,掏出钥匙扭开卧房的门锁,回头支支吾吾说道:
“我……刚从楼上下来……”
她提了水桶,走进门,拉亮电灯,吉茂和那两个年轻宪兵跟着挤了进来。比狐狸还要狡猾的吉茂,仿佛是闻到陌生气味的猎狗,朝卧房四处扫视了一眼,眯缝着贼眼紧盯着云梦江子,用审查的口气问道:
“江子小姐,听司令说你固执得很,今晚你上楼去了?”
“烦闷的时候上去散散心。”她在榻榻米的坐垫上盘腿坐下。
“刚才发生‘事变’的时候你在楼上?”
“不信吗?你去问楼上!”
“噫,”吉茂的牛皮底靴子在地板上蹭蹭,“地板怎么象刚擦洗过?”
云梦江子心里猛一怔,不由自主扫视了一眼大衣柜,惊得站了起来,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怎么回事?”吉茂走过来,逼视着惊慌失措的江子小姐。
云梦江子瞅了瞅窗外,灵机一动。
“上楼的时候,我忘了关窗户……刚才那场暴风雨打进来,淋湿了地板……下楼以后,我胡乱擦了擦……”
宪兵队长对云梦江子的追问,使那个报复心切的年轻宪兵壮了胆子。他突然抓了洗脸架上那条毛巾,尖声大叫:
“血!队长,你看毛巾上有血!”
云梦江子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软耷耷跌坐在榻榻米上。
吉茂队长接过带血迹的毛巾,送到电灯的光圈下翻过来复过去地瞧了好一阵,自言自语地说:“血,是今晚刚擦过不久的血!”他眨着阴险恶毒的小眼珠,把毛巾送到云梦江子鼻子前面,咄咄逼人地向:
“江子小姐,这又是怎么回事?”
云梦江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的脑子嗡嗡嗡的,只想到衣柜里的中国姑娘,竟什么话都回答不出来。她惊恐万状地勾下了头。
“唔,江子小姐作不出解释,那就对不起了——”吉茂提高了嗓音,象是对江子,又象是对他的手下人说,“有个中国臭女子要谋杀谷野司令,我们是奉命来搜查凶手。请原谅,每个房间都进行了搜查,我们是例行公事。”说完,他朝两个年轻宪兵递了个眼色。
两个年轻宪兵得到上司的命令,立即一手端枪,一手去翻大木箱和衣柜。那个对江子小姐刚才的嘲笑愤愤不平的大胆宪兵,刚走到衣柜跟前,云梦江子猛然醒悟,跳了起来,冲到衣柜前面,用身子拦住柜门大叫道:
“住手!谁敢来动女人的衣柜!”她害怕衣柜里的中国姑娘冲出来拚命,又一语双关地大喊,“不要动!你们躲得远远的,不要动,看看你们谁敢动……”
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个复仇和邀功心切的年轻宪兵,不知天高地厚地将云梦江子一推,拉开了衣柜的柜门。
云梦江子跌倒在地板上,差点就要惊厥过去。她用手撑着地板,抬起头,看到衣裙一件件被刺刀挑了出来,乱甩在地板和榻榻米上。她的心一阵阵紧缩:衣柜只那么大,可怜的中国姑娘还能藏到哪去?她仿佛看到刺刀挑破了姑娘的胸膛。是她把她藏在衣柜里,是她葬送了她的生命呵……只剩衣柜角上最后两条连衣长裙了,她不知哪来那么大一股劲,跳了起来,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企图用身子挡住衣柜的暗角,但是迟了。然而,最后两件衣裙被甩出衣柜,柜子里竟然空空如也,连人影都没有!她惊骇得差点要尖叫了。中国姑娘哪去了呢?难道是不信任她,趁她去卫生间的时候逃出了房子?那样也只有死路一条!所有怨恨,惋惜,同情,化作一股怒火,她一头冲年轻宪兵撞去,嘴里不停地叫骂:
“你这不长人眼的狗,把我的衣服全都弄脏了。凶手在哪里?你把人交给我!……”
被推搡得火冒冒的宪兵,威胁地朝江子扬起了枪托。
不知什么时候,谷野次郎和跟在后面的铃木中尉等几名副官,走进江子小姐卧房来了。谷野次郎阴沉着脸朝前走了两步,以命令的口气冲宪兵队长说道:
“吉茂君,把那年轻人的枪下掉,关三天禁闭!”
吉茂回头看到谷野司令,紧张地答应一声“是”,走过去下了部下的枪,又迟疑不决地回到谷野身边,把带血的毛巾递过去,声音压得极低地说:
“司令,在这里发现有刚擦上去的血……”
谷野接过毛巾看了看,沉吟不语,朝窗口走了两个来回,突然锁着的眉头舒展开来,极温情地瞅着脸上一块红一块白,又惊又怒的云梦江子,安慰地说道:
“江子小姐,你受惊了!”他猛地转过身,逼视着吉茂队长和铃木中尉,严厉而又不失身份地斥责道,“吉茂君,铃木君,你们玩忽职守!是你们粗心大意把个杀人凶手引进司令官邸,你们不引咎罪己,反而怀疑到江子小姐头上!告诉你们,江子小姐是我的人,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在我身边。今后不管警卫还是宪兵,未经我的批准,不许闯进江子小姐的住处,不许对她的行动进行干涉!”
“是!”宪兵队长,铃木中尉和所有副官全都打了个武士道式的立正。
谷野回头冲那个因下了武器而吓得战战兢兢的年轻人,恩威并施地说道:
“谅你年轻初犯,三天禁闭暂免,你帮江子小姐收拾好衣柜,该洗的你去洗洗。”
年轻宪兵如获大赦,很响地答应一声,鞠躬触地,就势跪下去收拾散乱的衣服。云梦江子连忙拦阻说:
“你们走吧!我自己收拾,再说……我太累了,需要安静……”
这时,门外闯进来一个宪兵,大声报告:
“报告队长,凶手杀死了好几条狼狗,越墙逃跑了!”
“啊!”谷野大惊失色,冲宪兵队长和所有跟来的副官吼道,“你们还不快去,快去调集人马追!追!一定要给我把凶手追回来!追不回来统统的要你们的脑袋!……”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蜂拥着出门去了。谷野次郎觉得自已有点失态,朝门口走了几步,又把铃木中尉叫了回来。
“铃木中尉,”他严肃而冷静地说,“你是帮我豢养狼狗的,狼狗被人杀死了好几条,你没有听到狼狗的叫声吗?”
“听到了,报告司令!”铃木打了个立正。
“啊?”谷野惊诧地瞅着他的“心腹”。
“司令您也知道,狼狗仍保持着狼的本性,每到深更半夜就要仰天嗥叫,到了雷鸣电闪刮风下雨的夜晚,嘶叫得更加厉害,院子里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了。”铃木一气说到这里,动了感情,“因为我是司令吩咐喂养狼狗的,心里时时刻刻装着那些宝贝。今晚在雷雨大作的时候,我听到了它们的呼唤,知道它们平平安安,也就落心落意睡着了……”
“谢谢你,铃木中尉,你走吧!”谷野拍拍铃木的肩膀,等他一走,转过身来到江子面前,抚着她圆润的肩膀,甜情蜜意地说:
“江子,你是处女,洁白无瑕的处女——”他扬扬带血的毛巾,又送到仁丹胡嘴边吻了吻,“让这块爱情的‘圣巾’,留在我身边作永恒的纪念吧!往后对中国姑娘我不屑一顾,心里只有你。过去为了报复,我放纵过自己。其实我崇拜的是清心寡欲,爱情专一。好了,”他亲了亲云梦江子,“你累了,收拾一下就歇息吧!要不天就亮了!”
谷野终于走了出去。云梦江子关上门,插上门闩,拉熄电灯,两腿象剔去了骨头似的,一步一挪,扒拢散乱的衣裙塞进衣柜里,倒在榻榻米上,再也支不起身子。她睁着双迷惘的眼睛,望着灰暗的天花板。那个中国姑娘杀死狼狗越墙逃跑了,是真的吗?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路灯探照灯全熄灭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大概宪兵和大部分警卫追击潜逃的谋杀者去了。折腾了半夜的谷野也重新入睡,在楼上新增加了几名贴身警卫吧?她想:那个貌不惊人,跟她一样苗条袅娜的中国姑娘,怎么可能杀死好几条狼狗还能翻墙逃跑呢?要不是有她的同伙架着云梯在墙外接应,那她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能飞檐走壁,力大无穷的侠女……
她正躺在那儿胡思乱想,忽地黑暗中传来一个极细小的女人的声音:
“江子小姐,我能出来一下吗?”
江子倏地坐了起来,她怀疑耳朵产生了幻听,或者真有鬼魂在捣乱。竖起耳朵听了会儿,近前还响起轻轻敲击木板的声音。她的神经紧张得就要炸断似的慌慌张张摸索着衣柜,壁柜。突然,壁柜柜门轻轻推开了,一双女人的手抓住了她的手。她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嗓音发颤地问:
“你是谁?”
“我是被你搭救的姑娘呀……”
“你怎么到了这一边?”
“我在衣柜里找了身衣服穿上,闷得慌,趁你不在,我到壁柜这边看了看,想找个宽敞一点的地方。壁柜里果然又高又宽敞,横着可以睡觉,我就在这边留下了……”
“你呀,真把我急死了!”她紧紧地搂抱住她,欢快的泪水淌到她的脸蛋上。
两人就这么坐在漆黑的壁柜里,悄声交谈着:
“你真好!”一个说。
“你叫什么名字?”另一个问。
“你就叫我乔妹子吧,人家都叫我乔姐。”
“你就是‘飞镖乔姐’?”
“你怎么知道?”
“皇军听到‘飞镖乔姐’的名字,魂都吓掉。我以为‘飞镖乔姐’有三头六臂,原来就是你这模样——哎,你多大年纪?”
“二十三。你呢?”
“十八。”
“那我叫你‘江子妹’。”
“我叫你‘乔姐’——乔姐,你家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家,江湖上就是我的家……”
“那怎么可能呢?”
“我不到三岁,母亲便病死了。跟着父亲走江湖,父亲从来不跟我说有家没家。十五六岁,父亲一死,我就成了随风漂荡的浮萍……”
“你在陆城小镇上有亲戚没有?”“什么陆城?没听说过……”
“多可怜!”她想的是她们之间并无“巧合”。
“你们当军妓的也很苦吧!”
“嗯……”
云梦江子把“飞镖乔姐”留在自己卧房里,是有一定把握的,因为谷野次郎作了保护伞。自从谋杀事件发生后,她以谷野司令的“战时太太”的身份出入司令部,人人心照不宣。除了谷野偶然来她卧房坐坐,谁也不敢涉足这“皇宫禁苑”。她外出可以乘坐司令几乎不用了的那辆旧轿车(谷野新配了一辆崭新的流线形轿车),进出时门岗卫兵不再验她的特殊通行证。就是在城内各军营机关,只要通报她的名字,也受到远非一般军妓可比的尊重(小雪子对她这点羡慕得要死)。凡此种种,都为她保护乔姐提供了方便,乔姐栖身魔窟,一晃就过去了四五天。
乔姐白天躺在壁柜里睡觉,无人打扰;晚上熄灯以后走出来,在屋子里活动活动肢体,跟江子谈谈悄悄话。白天三餐饭,由江子从伙房打回房间。江子还不断采购罐头、牛奶、饼干、水果,两人分吃一份饭菜绰绰有余。难办的是,乔姐身上有多处被狼狗抓伤咬伤,虽未伤筋动骨,但也怕感染化脓带来后患。而日军内部对药物控制极严,特别是三次湘北战役后,日军野战医院伤病员剧增,外敷药膏和内服消炎药物更为紧缺。司令官邸虽有保健军医,药物齐全,但怎样去要外伤药物而不引起怀疑呢?云梦江子苦恼了一天一夜,想出了一条苦肉计。那天吃过早饭,她去伙房送还碗碟,走到伙房外的麻石坎坎上,故意踏上长满青苔的滑腻石头摔了一跤,将手肘擦破了皮;倒下时,又着力将大腿的裤管擦了层泥,碗碟当然摔个粉碎。“伙头军”一看伤了“司令太太”,连忙陪罪,搀扶着去看军医。江子大腿安然无恙,却装得一瘸一拐,口里还哼哼唧唧,军医看了看她的手肘,拿酒精、碘酒药棉消了毒,涂上红汞,还特别讨好地上了消炎膏。军医瞅着她“擦伤”的大腿,考虑到她的身分,面带难色地伸出手,小心翼翼触摸了一下。她故意“哎哟”一声。
“江子小姐。能否请你将裤头退下……”军医犹豫地说。
她脸一红,羞答答地说道。
“这样——合适吗?”
“唔,失礼了,”军医自知失言,立即改口,“让我打电话去野战医院,请他们派名女护士过来吧!”
“不必了!”她“痛”得吸了口凉气,“请你给我一些碘酒、药膏和药棉,还要些内服消炎药。我在学校学过卫生保健。”
“那当然可以。”
她拿着足够的外伤药物,回到卧房里,当即便拉上窗帘,给乔姐敷药吃药。
没过几天,乔姐的伤口便不再疼痛,吃饱睡足,体力也很快恢复了。她老是叨咕着要回她的“部队”去。开始江子不同意,是因为一来乔姐的身体没有复原,二来自从暗杀事件发生,城里城外乃至湖上连续戒严搜索凶手,别说一时难于混出司令官邸,就是混出了魔窟,又怎么闯过皇军占领区的层层岗哨和蛛网般的炮楼呢?不过,老是把乔姐留在这里,江子也有她的难处。她一直没敢把乔姐杀死的并非谷野,而仅仅是谷野的一名保镖的事告诉乔姐。她怕乔姐性急火起,再去冒险。如今谷野加岗加哨,就连晚上她上去,通宵都有保镖在门外守卫。乔姐再去行刺,很难伤着谷野,只会断送自己。她宁愿乔姐早日脱离虎口。昨天把戒严令撤销了,乔姐已归心似箭,江子不得不认真考虑送乔姐脱离险境的事情了。
乔姐要混出司令官邸,她和江子面貌酷似,这是个有利条件。只要把她好好化装打扮,穿上自己平常爱穿的衣服,就能鱼目混珠。可是还要出城,还要混过无数岗哨炮楼……最好给她弄一份特殊通行证或“良民证”,如果用谷野那辆旧轿车把她送出城外,那就更安全可靠。然而,到哪里去找一名绝对可以信任的对中国女子富有同情心的驾驶员呢?她想到了铃木中尉!铃木一郎给谷野开过一年多车子,技术自然精熟。从对铃木良子的思念和日常交谈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正直而又对女人富于同情心的人。她握有良子的“秘密”,生死关头可以逼铃木就范。她难以决断的是:自从她和谷野苟合,铃木明显地疏远了她,躲着她。她弄不清铃木副宫对谷野有几分忠诚,又有几分“貌合神离”……
那晚上,云梦江子和乔姐一席闲谈,乔姐无意中谈到的一个意外情况,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乔姐原来一直认为,那晚上把她从狼狗嘴里救出来的人影,就是江子小姐。江子听了立即警觉地问:
“有人把你从狼狗群里救出来?那些狼狗不全都是你杀死的?”
“不是。是那人赶走剩下的狼狗,还把我抱着送到你房间里……那不是你?!”
“糟了!大院里还有另一个人知道你藏在我这里——这人安的什么心?他又是谁呢……”
云梦江子这晚上通宵未眠,榻榻米上象长满了针刺。她辗转反侧思考着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第一个想到的是铃木中尉,铃木中尉具有一般的、隐而不露的反战意识,对摧残女性——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相当反感。可是,在皇军的司令官邸,他要作出这样的叛逆选择,是难以想象的。除非一种可能——他已见过良子,他已作好了死的准备……想到这里,云梦江子象患疟疾一般打着哆嗦,浑身冒着虚汗。
她只等天亮就去找铃木中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