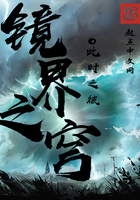这天,梁啸尘一上班就被徐部长叫了去,要他参加一个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组的档案材料和报道工作。接着,他和审计局、检察院等单位的同志们来到县委小会议室,参加了一个动员会。县委程书记脸色铁青,当当地拍着桌子说,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要一查到底!不管牵涉到谁,一律不能手软!宣传部要及时向各位书记通报进度,报社要将案件情况及时在报纸上曝光!梁啸尘听到这里,就感到案件的严重性。他听旁边检察院的人小声地嘟嚷了一句,林政韬。心一下子就扑通了起来。
会议结束,调查组为了保密,在月亮宾馆包了两间房子,开始了工作。查阅有关文件,找证人谈话,折腾了一下午,也没个眉目。调查组在宾馆集体就餐,梁啸尘惦着震瑶她们的事情,朱清丽又一连两天都没有露面,他吃罢饭就匆匆往回赶。
暮蔼又降临了小城,所有的街道、店铺统统沐浴在一片乳白色的淡雾之中。下班的人们,如同从许多条小河泄出来的水流,汇到街上,然后,急冲冲地向前涌去。
“啸尘!”
一声凄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梁啸尘扭头一看,是朱清丽!只见她脸上挂着一层哀怨和愠怒的冰霜,眼睛里噙着泪花。隆冬的寒风,掀动着她黑色的裙摆。梁啸尘感到那两条瘦骨伶仃的裸露在裙裾外面的腿在栗栗发抖。他心灵为之震颤了。急忙跳下车去,叫道:“嫂子!”
朱清丽找了他一圈了。她找到编辑部,一位女记者告诉她,梁总编去了宣传部。她到了宣传部,办公室的人说没见到报社的人来。她估计他可能下班回家去了,不期在这儿碰到了他。
他一见到朱清丽这个样子,就估计是周剑章出了问题,而且肯定是和林家飞。不禁心想,这下林政韬可谓是祸不单行了!不由掠过一阵快感。又想到毕竟事关老朋友,自己怎么可以幸灾乐祸呢!同情心就又占了上风。尤其看到寒风中朱清丽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越发动了恻隐。自己要不是把握住了,说不定柳震瑶就学了朱清丽呢!忙说:“嫂子,你找我有事吗?”
“剑章他……”朱清丽嘴一撇,眼泪夺眶而出,差点就要哭出声来。
梁啸尘赶忙掏出手绢,递给她,说:“别哭,别哭。你还没吃饭吧,走,找个饭馆先吃点饭,再上我单位去。”说着,就去拉她。
朱清丽仍然站着不动,她拿手绢擦着眼泪,刚刚擦去,泪水又不可遏止地涌了出来。下班的人流从他们身边驶过,向他们投来惊异的目光。梁啸尘想老周如今是名人了,哪能让嫂子在大街上出丑啊!就说了声:“先上编辑部吧!”骑上自行车,逆流而上,朝编辑部驶来。朱清丽止住了啜泣,跟着他来到楼前。
屋里没有暖气,很冷。梁啸尘让她在对面沙发上坐了,为她倒上一杯水,说:“我这里只有方便面。我给你泡一袋吧?”
朱清丽说:“你别管了,我这会儿哪有吃饭的心思呀!”说着,肩膀抽搐着,终于哭出声来。
梁啸尘望着她汩汩流出的泪水,想,这剑章也真是的,放着小日子不好好过,偏要搞什么……!可是,他又理解周剑章。他又想起了林家燕。一时踌躇着,不知从何说起。
朱清丽抽泣着说:“剑章和那个浪妮子干那事,让我给逮住了!”
“真的,什么时候?”梁啸尘虽说思想上有所准备,可她话一出口,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和震颤。
“就你们回来那天!哼,不定在一起干过多少回呢!那次,我就发现枕巾少了一块。和他弄那个,他……怎么也起不来……”
“你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了吗?”梁啸尘开始稳定下情绪,不由想起那年在西城见到他们俩亲热的情景。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弄不清楚。大概是从他搬到城里以后……”
“哦……”梁啸尘想起几次在怡心庐见到他的情形,“不管怎么说吧,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那天,我把那个浪×妮子抓了一回,他妈俩人跟我跪着求饶!我想,你是剑章的好朋友,在滨河,他就听你的!你得好好劝劝他,剑章这会儿是色迷心窍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可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推心置腹地找他谈一谈。可是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行。尤其对方……”
“林家飞,林政韬那三妮子!”朱清丽咬牙切齿地说。
“我知道,我是说,尤其对方还是个女孩,这事对你的潜在威胁很大,我是说,她有她的优势……”梁啸尘选择着字眼,尽力说得轻松点。
“哼,看我不拿刀子豁了她个浪×!”朱清丽两只眼睛放射出母狼般的绿光。梁啸尘心中一悸。想到女人其实是得罪不起的,真要把她们逼急了,她们不定要做出什么事情来。他说:“嫂子,你可千万不要蛮干。那样只会促使他们……”
“什么?”
“……走到一块。对不起,我必须这样提醒你!”
“他敢?”
“这不是敢不敢的事情。他要真的喜欢上她了,我是说……你应该有所准备……”
“准备,准备什么?”
“我是说我不一定能成功,但我一定尽力而为!”
“哼,真要把我逼急了,我一刀子捅了他们!”
“嫂子,我劝你还是不要做那傻事!”
“那我就天天跟着,他走到哪儿,我跟到他哪儿,我看他能怎么样……!”
梁啸尘被她感动了。他感到了女人的可怕。他记起柳震瑶说过类似的话。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有些为剑章担心。看着朱清丽那样子,他又想,你这是何苦呢!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你能跟住他的人,又怎能栓住他的心呢?与其这样,何如……如果,周剑章要死心踏地往那条路上走的话,你是拦不住他的。这实在太残酷太难容忍。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好朋友的家就这样解体。可是,他又深深地了解周剑章,因为太深的了解而预感到,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却极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他感觉还不到说这话的时候,现在这样说,就如同提前告诉她谜底,使她丧失了努力的勇气。那简直成了帮助周剑章他们了!就又想着法儿解劝了半天。然后,告诉她,自己明天必须上班。要不,我这会儿去找找他?朱清丽说这会儿就这会儿,咱又不是外人,我也不用客气了!你去吧,我上街里吃点东西,一会儿还回这里等你!
梁啸尘看她那焦急的样子,越发同情起她来。就说,我立刻就去找他!嫂子,你放心!他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我也要把他拽回来!把她拖到你身边!他感觉他必须这样说。虽说这样说了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面对着朱清丽那凄苦无助的样了,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这么说的。
说罢,将钥匙交给她,骑上车子,又回头瞧了一眼门边的朱清丽,一头扎进寒风中。
“当说客来了?”周剑章阴沉着脸,瞥了梁啸尘一眼,冷冷地说。
梁啸尘看他一付置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就说:“你要不欢迎,我立刻就走!”
周剑章仍然坐在被窝里,披着棉衣,头发蓬乱,脸上有几道血痕。他将腿收回来,为梁啸尘腾出一块地方,看着他坐下,双手抱了膝盖,说:“说吧,我倒要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梁啸尘侧着身子,与他对视着,说:“其实要说的,在北京都已经说过了。第一事业不可丢……”
“事业?她还让你搞事业?你看看去,画框上的玻璃全都砸烂了!”
梁啸尘这才想到,刚才进屋时确实见到几幅画框被弄得七扭八歪的,玻璃碎了一地。他尴尬地笑笑:“气头上的事情,可以理解……”
“理解?你不知道她那个狠劲呀!恨不得……”
“还不都是你逼的?”
周剑章拧了拧脖子,不再说话。
梁啸尘接着说:“你让我把话说完。第一事业不可丢;第二家庭不可毁;第三嘛,爱情也得要……”
“嘿嘿。”周剑章一耸肩膀,冷笑一声,“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家庭和爱情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我理解你!但是,你不能否认,你和大嫂之间曾经有过爱情。”看他又要发作,他按了一下他的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记得,当初你刚结婚那会儿,我到你新房去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在方桌上作画,大嫂在旁边给你倒茶递水。当时我想,剑章和大嫂是全镇子上最般配、最幸福的一对呢!我日后若能象他那样,就知足啦!”
周剑章一声长叹:“那是过去……”
“你也承认那曾经是事实。你能说那时没有爱情?”
“可是事物要发展,爱情也会死亡!”
“这我明白。问题是你为什么让它死亡,而不使爱情之树常绿常青呢?”
“你们文人啊,就知道咬文嚼字。你也许还不能理解,你不知道,她是怎么一点一点使爱情死亡的!”
这一句正戳着梁啸尘疮疤,他皱了皱眉头,将痛楚压了下去,看着他说:“还不是大嫂这几年顾工作多些,尤其最近又忙着生意上的事情,对你照顾不周?第三者乘虚而入……”
“你不知道她那个人呀!咳,远的不说,她这会就一门心思地想着赚钱!赚钱!”
“这难道也错了吗!她赚了钱是谁的?”
“我把钱看得没有她那么重,我们的生活目的不同。或者进一步说,当初的结合就是一个错误!”
“你敢说你没爱过她?”
“此一时,彼一时也。”
“说白了,现在你是地位变了,名气大了。可是,你想到没有,你的成功里面,有人家多大成份?”
“跟她有什么关系?她除了来捣乱、盯梢,没起过任何好作用!”
“老兄怎么不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呢?如果没有大嫂在那里撑着,你能安心地搞你的创作吗?”
“这么说吧,如果现在林家燕要和你好,你会怎么样?”
“我,我会立刻拒绝她!”梁啸尘挺起心肠,说。
“恐怕老弟言不由衷吧?”
梁啸尘低下了头。
“要是现在林家燕站在你面前,我看你能不动心?”周剑章又在他滴血的心头捅了一刀。
“……”
“打中七寸了吧?”
“我可能动心。”梁啸尘抬起头来。“事实上她曾经站到过我的面前,就在我回来前不久,我们曾经去了红枫山……。那是唯一的一回,也是最后的一回!人生,有那一回,就足够了呵!”说着,他伸出了手去,握住了周剑章的手,使劲地摇着,眼里闪烁着泪花。周剑章错愕地瞧着他,想不到那么坚强的汉子,提起心爱的女人,也会泪眼婆娑。看来,他爱得比我还要深沉。他被感染了,眼中一阵潮湿,鼻子就酸了。他拍了拍他的胳膊,默默地走到画室,瞧了瞧被砸碎的玻璃,坐到竹椅上,低着头不再说话。
梁啸尘跟出来,提起壶,摇了摇,空的,他走到院中,灌满了水,燃起柴油炉。看了看冷冷的屋子,坐到一旁,说:“你这么多年一个人孤军奋战,长途跋涉,是不容易……”
周剑章想起在这里受的苦楚,眼圈又红了。他想说连壶水都没人给我烧!可是,他没说出口。
梁啸尘想着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就告诉他,父亲已经在城里租到了门市。他们要搬进城里来了。他劝他说将嫂子一块搬到怡心庐来。俩人住在一起,没有干扰了,慢慢就又和好起来。他还想起正在查处的林政韬受贿和挪用公款一案。想了想,感觉没办法跟他说这件事,就住了口。
周剑章说:“你们能折腾就折腾吧,能折腾总比不能折腾好得多!我是个局外人,帮不上忙……”
梁啸尘说:“你怎么是局外人呢?听震瑶说,这次的新款式还是你设计的呢?”
周剑章就笑了,笑得完全象个孩子:“你可能不知道,也不要告诉她们:那是人家设计的……”
“谁?”
“还能有谁?”
“哦……我明白了,她们姐妹是挺有灵性的……”
“你是不知道和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啊……”周剑章连连搓着手。
梁啸尘脑屏上不由又浮起和家燕在一起时的情形,周身一阵痉挛。不知道,不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忽然想,自己被林政韬破坏了美好的爱情,可是,自己为什么还要破坏周剑章和林家飞的爱情呢?想到这里,他不由去瞧着周剑章,瞧着他那张被抓破的疲惫的苍白的脸。他忽然感觉周剑章很可怜,同时又十分地可亲可爱,甚至可敬起来。他感觉周剑章其实很男人,很——伟大!他的执著,他的追求,还有他的敢作敢为,都是他所做不到的啊!他迫不得已,悬崖勒马,其实,他骨子里是非常赞赏周剑章的。他站了起来。他把握不准,再这样谈下去,不知道究竟谁能说服谁。
这时,他想起了傍晚马路上那一声凄厉的呼唤,他的心灵再一次地震颤了一下。他感觉那是一个掉进冰窖的人在向自己求救。自己怎么能将这种义不容辞的救援半途而废呢?
可是,周剑章,他又瞥了他一眼。这个周剑章呀……他也不愿意伤害了他呀。老牛不喝水强按头。他要执拗下去,朱清丽还能幸福吗?想起朱清丽,他又想起了他的角色。她还在办公室等回音呢!自己怎么可以在这里败下阵来,弄个落荒而逃?于是,他挺起心肠,说:“我还是希望你和大嫂好好谈一谈,能够和好起来。你的事业需要一个稳固的家庭,这也是我的切身体会和肺腑之言!其它的事情吗,我也劝你好好斟酌一番。甘蔗没有两头甜。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他终于说明了自己的意思。说完了,他感觉自己的话那么软弱无力。他感觉他不适宜扮演这个说客。又感觉有点对不起朱清丽,又对不起周剑章,还有点对不起自己似的。
周剑章看他那难受的样子,心中十分感动。他知道他是受人之托,不能完成任务,他是十分痛苦的。他也知道了他的心病。猩猩相惜。难为他还能这样劝诫自己。他何尝不是在劝诫他自己呵!就说:“我非常感谢老弟的一番苦心和直言相劝,我会十分慎重地考虑你的意见的。不过……”
梁啸尘不想恋战,就截住了他:“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太对不起大嫂!她不容易,真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你、你让他去依靠谁呀?”
最后几句话,他几乎是噙着泪水说的。说完,赶紧抽身便走。他知道周剑章还会说出什么话来。
刚刚做了说客的梁啸尘无功而返,却不料自己又坐到了被说的位置上。他回到编辑部,已是深夜。令他感到不解的是,铁兵霍然在坐,旁边还有那位军师捻儿。他们正和朱清丽说着什么事情。见他进来,竟然全都客气地站了起来。他猛的掠过一种预感,眼睛瞥了一眼桌子上的烟酒,脸色就耷拉下来。
“干什么?还给我提溜着来啦?你怎么不弄两瓶茅台?”他瞧着铁兵,凌厉的目光逼迫着铁兵低下头去。
捻儿笑道:“这会儿都兴这个了,梁兄……”
“那你得看跟谁!”梁啸尘吼道,“你问问他。”他指着铁兵,“我们是从小光着屁股打扑通长大的!好呀,跟我也来这个?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铁兵低着头,不敢迎视他的目光。
捻儿仍然嘻嘻笑着,冲淡着紧张的气氛:“这是我的主意。我们也没别的意思,兄弟们听说你高升了,前来贺贺喜,喝一场……”
“那还要掂着酒来?”
“这个……”
“实说吧,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把这个掂走啊!”梁啸尘说着坐了下去。
铁兵抬起头来,与他目光碰了一下,急忙闪开。梁啸尘注意到那目光中含有一种祈求和期待,知道他们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来找他。就看了看朱清丽,说:“大嫂,我跟老周说了。看来他暂时还有点情绪。不过,不要急,都这么多年夫妻了,我想他不会走得太远的。”说完,他又感到话语是那么软弱无力。
“你是不知道,他那拧劲儿上来喽……”
“不要紧,我抽空再劝劝他。你呢,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你怎么把他的画砸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他的心尖子!你这不是往外推他吗?这种事千万要冷静。你越不冷静,事情会越糟!我看你也搬到城里来吧,两口子长期分居,准有一方会出点小问题。我想,你们住在一起以后,会逐渐好起来的。记住,千万不要再跟他吵!那对你没好处,你得拖住他!慢慢使他回心转意,我就不送你了。”说完,转向捻儿,嘱咐他送周大嫂回去。
看着捻儿和朱清丽走向夜色之中,梁啸尘回到屋中来,摇摇头说:“这个老周哇,真是,人一出名……”
铁兵已经知道了事情大概,他和捻儿一块劝慰了朱清丽半天。这会儿,见他这样说,心中想,你如今也成了名了,你会不会变呢?又不便直说,就那么瞧着他。
梁啸尘坐下去说:“怎么啦?深更半夜的跑来,你这是干什么嘛?咱们谁跟谁呀?你这不是跟我弄难看吗?”
铁兵鼓足了勇气,盯着他说:“实在是事情重大……”
“有什么嘛?咱兄弟们,多大的事情用得着这样吗?”
“我、我们借了林政韬五万块钱……”
梁啸尘心中咚的一响,林政韬的问题一是受贿,一是挪用公款。谁知他挪用的款项,却是借给这个冤家了!他一时语塞。
“是、是我们被逼急了,去找的他。我们都是乡亲,林政韬那人挺够义气,一下子借给我们了。要不是他,我们的冷库……”
梁啸尘明白了。他想林政韬这是咎由自取。他想起程书记上午那严峻的神色,估计林政韬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可是,他不知道铁兵找他有什么意图。就听铁兵说:“我们想退还那几万块钱,你能不能把那个材料撤出来?”
“什么?”
“我们想,林政韬好心帮助我们,我们不能眼瞅着……”
“他是自作自受!——你不要那样瞧着我!你可能会想,我和林政韬之间有个人恩怨。是的,林政韬确确实实压制过我,但我不会趁此机会落井下石的,我没有那么卑鄙!林政韬触犯了党纪国法,情有可恕,天理难容。怎么处理他,是组织上的事情。我不过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而已,这事我帮不了你。就是能够帮助你,我也不会那么做的。我还要劝你打消那种想法,我估计组织上要向你调查,我希望你要积极配合,如实反映事情真相。任何别的想法,都只会使事情搞得更糟!”
铁兵呆呆地瞧着他,好像他是个兵马俑。
梁啸尘说:“这不是咱兄弟俩之间的事情。”
“可你能帮这个忙!”
“我帮不了你!你可能因这事恨我。以后你会想通的。我不能那么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啊,你当官了嘛,哪里还能瞧得起我们这穷兄弟!”
“当官不当官,跟这事没关系。这是纪律。真的,我只能这样。别的事情都好说。比如,你的冷库发展起来了,我给你写文章做宣传,上哪一级报纸都行!可这事不行,我爱莫能助!”
“一点也不能通融?”
“我真的帮不了你,你应该理解我。”
“那你就看着你兄弟倒霉吧!”
“我劝你赶紧向调查组说清事实,这可以帮助你解脱出来。”
“谢谢你的好意!”铁兵说着站了起来。
梁啸尘提上烟酒,递给他。铁兵像烫住了一般躲闪着,看着他那越来越陌生的铁板一般的面孔,心中叹道,真是人一当官,脸就变了!
梁啸尘痛苦地将他送到门外。他十分珍惜和他的友谊,他不愿意破坏那种手足般的感情。可是,他又不能顺着他们来。他感到自己是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不情愿,但毫无办法。
周末上午,联合调查组召开会议,将调查情况做了汇总,责成梁啸尘写成材料,向县委和程书记汇报;还要在《滨河报道》发表消息,将调查结果及时披露出去,接受群众监督。
吃罢饭,梁啸尘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刚刚写完消息,副总编匆匆赶来,交给他下周的稿件,请他审签。梁啸尘想你来得正好,就将消息让他看了,排在头版显要位置。副总编走后,他就开始审看稿件。签上名,一边心中想着,这期报纸一发出去,林政韬就算是彻底完蛋了!不由掠过一种快感。他燃起一支烟,盯着那条消息,陷入了深思。
他想起了小时候,在狮子楼里这位林大官人的喝斥。那时,他是多么地骄横,不可一世啊!他还想起了在月亮河里和伙伴们一起游泳时,看着这位林大人坐着吉普从桥上拐下来,在同僚的陪同下,到柳荫里垂钓的情形。那时,知了嘶嘶啦啦地叫着,农民们正在田野里劳作,林政韬架着二郎腿,黑亮的皮鞋反射着阳光,旁边的人正为他点上一支烟。林大官人抽了一口,就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地哼起了河南梆子……车上又有人将啤酒和烧鸡掂了过来……他和伙伴们的眼睛都快瞪出血来了!他羡慕他,嫉妒他,憎恨他,又盼望着能够成为一个象他那样的叱咤风云,倍受人们尊崇的人物。但是,他并不期望象他那样作威作福。他懵懵懂懂地感到,林政韬这样恐怕不是上级所期望的,恐怕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倒台,甚至说不定自己还会超越他呢!那时的思维到此为止。
这时,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特定环境,而思维却向前推进了一大截。少时的梦想和期待都神奇地变成了现实。他仿佛正步着林政韬的后尘,一步一步向上攀援,虽说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甚至还有摔下去的危险,但是,恰恰因此而更加具有诱惑力。他已经超越了许多朋友、同学。他想,即使留在部队,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呢!许多正营职军官转业才安排了个一般干事呢!总编这个位置,虽说不是那么显赫,手下也没有那么多人,穷得连部车也没有,可毕竟是总编,是正科级。其地位和权力还是令一些人颇为动心和垂涎的呢!在县城,一个正科级,就差不多是许多优秀儿女终其一生的追求了呢!自己年纪轻轻的,却已经得到了它。虽说目前只是聘任,可只要办完录用手续,去掉前面的那个“聘”字,是完全有可能和能够做得到的。而且,只要努力做下去,更大的辉煌就一定在等待着他。想到这里,一种成就感占据了他的心怀。
“可是。”他暗暗地告诫自己,又燃上了一支烟。一定要记取林政韬的教训。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什么份上,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是怎么得来的,都不能为所欲为,都必须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工作。上升时期如此;以后到了辉煌时期还要如此;就是后期,更要如此啊!
想到这里,他拿起了笔,他第一次感到那枝钢笔是那么沉甸甸的。他再一次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特殊时刻立下的誓言。
天空灰蒙蒙的,室内光线黯淡下来。他燃起第三支烟,在稿纸上写下标题:《关于林政韬受贿挪用公款一案调查情况的汇报》。
有人敲门,敲得很轻。他的眼睛转了一下,想着有谁知道自己在这里。朋友当中只有周剑章。那天,他又找到怡心庐,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夜,看来是很难拉回来了。他这时候来找我,肯定是有重要事情。梁啸尘搁下钢笔,走到门边。
又是一阵敲门声。很急,也加重了声音。要是周剑章,肯定早叫了。他站在门边,心想,会是谁呢?
“梁总编,我是组织部的,请你开一下门。”
“组织部的?莫非是龙晋生?他来干什么?”梁啸尘犹豫了一下,快步走回办公桌前,将材料和文稿装进抽屉。想了想,又拿出一叠稿纸摆在桌上。然后,打开了门。
一位中年男子笑眯眯地站在门外。
“您是……?”
“我进去说话,好吗?”
梁啸尘让他进来,又锁上了门。
“你可能不认识我吧?梁总编。可是,你的大名我可是久闻了啊!我在部里几次跟同事们说,你们都要向梁总编学习……”
“请问,您是……?”
“我叫杨昭明。”来人说着,掏出名片。梁啸尘接了看着,指了指沙发:“哦,杨部长,请坐。”
杨昭明瞥了一眼桌上的稿纸,眉毛一扬:“又要写什么大作呢?你在《西城日报》发表的文章我读过,梁总编思想敏锐,才华横溢,不愧是我们滨河的名人呐!”
梁啸尘抽出一支烟递给他,杨昭明摆摆手,非常热情地说:“你的录用报告我看过了。嘿嘿,我呢,正好分管这一块。我要提请部长办公会尽快研究。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
“那就谢谢你了,杨部长!”
“不过。”杨昭明拧了拧脸,“我在组织部二十多年了,根据以往的经验,上报名额都有富余。就是说,这个……”
梁啸尘明白了,就打断他说:“我一定努力工作,请杨部长多关照!”
“当然,当然!我一定会全力推荐!”杨昭明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近梁啸尘。“听说,林政韬一案已经结束调查了?”
“嗯。”
“听说,除了向程书记汇报,还要在报纸上捅出去?”
梁啸尘没有搭话。对于这位杨部长获悉“情报”的速度和反应他感到吃惊。他努力稳定着情绪。
“你看,这样好吗,梁总编?”杨昭明说,“录用的事,我抓紧办理。上面来考察,我一定大力成全!给程书记的材料呢,你该怎么报就怎么报。我想,这消息嘛,是不是先不要发?”
“为什么?”
“你看,是这样。我和林政韬的关系,估计你也清楚。林政韬呢,过去多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也批评过他。现在,他行动不便,我来代他向你道歉,请你原谅。都是本乡本土的……”
“请你放心,杨部长,我决不会落井下石的!”
“当然,当然,我是信得过你,才来找你。我也搞过材料,咱们文人是不会那样做的。我们正在活动,你只要推迟一下见报的时间,下来的事情,就由我们运作了。而且。”杨昭明说到这里,拍了拍他的肩膀。“保证不会影响你的前程。老程那里,由我为你去解释。”
“我没有考虑什么前程。我在部队的事,大概你也清楚。你想让我撤下那条消息,除非你能说明,那样做是错误的。”
“这个……”杨昭明后退了一步。
“否则,我恐怕难以使你满意。”
杨昭明又趋上前来,又一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亲切地叫道:“小梁,梁总编,我十分钦佩你忠于职守的精神。当然,我更不会让你犯错误。那样,我将于心何忍?我是说,你能不能暂缓发表?”
“暂缓?”
“当然。理由嘛,梁总编是有办法的。何况,今天又是周末。”
“我要是坚持按时发表呢?”
“那……不,你是个聪明的人。我想你不会那样做的。”
“你想错了。杨部长,我也许并不聪明。但是,我必须忠于职守。很对不起,我只能如此。”
“年轻人,做事情都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杨昭明说罢不由冷笑了一声。这声冷笑,使梁啸尘有点毛骨悚然,他的腮边又习惯地鼓起两道褶子。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盯着他说:“杨部长,我信奉这么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说,我连前程都不关心,哪里还会虑及什么后路呢?对不起,我不能给予你这个方便。”
杨昭明狠狠地坐了下去,偏过头,语气里明显地流露着威胁:“梁总编,难道竟是一点儿也不肯通融?”
“没办法,我只能恪尽职守。”
“我想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在部队的教训?”
“正是那个教训,使我必须这样做。”
杨昭明阴毒地一笑:“那好,我要向你学习,也应该恪尽职守。根据群众反映,你的录用走的是县委某领导的门子。部务会上,我打算就这个问题,请大家展开讨论。”
“那是你的职责。而我的职责,要求我马上开始工作。杨部长,你看,夜幕已经下来了?”
“好吧,梁总编,我会严格地履行我的职责的!”杨昭明说完,猛的站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林家燕被从食堂喊了出来。“谁呀,谁找我呢?”她推了推推散到腮边的头发,从值班员手中接过电话。
“家燕吗?我是杨昭明呀。”
“呀,是姑父呀?你这时候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燕子。”杨昭明尽力使语气亲昵和委婉些。他知道这位妻侄女的脾气,也知道他们父女的关系。他努力装出一种平淡的口吻,“你知道你爸的事情了吗?”
“知道了……”
“现在我和你爸正在想办法,估计很快就会出现转机。但是那位梁……总编却要在报纸上捅出去。那样你爸可就没救了……”
“姑父,你就直说,让我做什么吧?”
“燕子,我知道你和小梁的关系。过去呢,在这件事情上,你爸是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可他毕竟是你爸呀!你爸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再说你爸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你说,需要我干什么吧?”
“我们想,让你跟小梁通融一下……”
“怎么通融?”
“让他把那稿子撤下来,我们就有办法。”
“你们找他了吗?”
“你知道,你爸跟他弄成那样;我呢,怎么也不如你……”
“你别说了。我不能那样做。”
“燕子,这可事关你爸的命运呀……”
“我爸是自作自受,我救不了他。”
“燕子……”杨昭明迫不得已,动用了长辈的威严。可是,对于压根就对这位姑父没有好感的林家燕来说,这种威严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杨昭明也感觉这位内侄女不会就范。于是,他就亮出了杀手锏:“燕子,我可提醒你,你爸一完,说不定你也要跟着倒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应该比我清楚。你的位置是怎么来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知道吗?你爸为了你能考上这个播音员,在老县长那里……”
“我爸是怎样活动的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我的业务能力是充满自信的。何况,我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已经完全胜任了这份工作,就是再来一次考试,我也会榜上有名的!”
“那你就看着办吧。”杨昭明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还想告诉你一个信息,那姓梁的转干问题下周就要研究,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主管部长呀!”
“那就凭你的良知吧!你要没别的事我就挂了。”
挂断电话,林家燕信步走到大厅,团团转着圈子。一盏吸顶灯将黯淡的灯光在地板上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她蓦然想起来这里参加考试时的情形。那时,她和爸一起走出了任局长办公室。她看到爸爸毕恭毕敬地对任局长陪着笑脸。虽然她对爸爸这种做法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她还是能够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爸爸确确实实是为了女儿。她也时刻在想着回报爸爸的关爱。而且,正是因为我太看重这种父女亲情,才和啸尘弄到这步田地。就是爸爸,生了我养了我,自以为处处爱护着我,又恰恰是他断送了我和啸尘的姻缘——是他害了我啊!
如今,爸爸触犯了党纪国法,情有可恕,天理难容。自应该受到惩罚。可是爸爸却要……
爸爸,我们父女磕磕碰碰这么多年,但是,最终都还是我依顺了你的意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归根结蒂,还是我太爱你的缘故。我也时刻想着为妹妹们带一个好头。到头来,三儿还是爱上了周剑章,我自己也并没有获得幸福!
就是这样,我依然爱着您,谁让你是我的生身父亲呢!您应该主动找组织交代清楚,争取宽大处理,也好尽快解脱出来。而这样下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也不会帮助你那样做的。何况,就是啸尘为你网开一面,也是无济于事的。
爸爸,生我养我的爸爸呀,如果您以为违悖您的意愿就是不孝的话,那么,这一次,就请您原谅女儿的不孝了!
林家燕想到这里,迈步朝值班室走去。这时,她发现自己是踩着自己的影子向前走的。发现了这个现象,脑子里突然一亮。于是,步伐更加坚定了起来。
梁啸尘回到编辑部,已是华灯初上,他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他知道林政韬、杨昭明他们是不会善罢干休的,他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一到编辑部,就将签好的文稿交给副总编,要他立刻送到印刷厂。
副总编接过文稿,掂了掂,那样地瞥着他,说:“梁总,是不是考虑,缓发一下?”
“缓发,为什么?”
“不看僧面看佛面吧,要是林局长的女儿知道了……?”
梁啸尘的眉毛颤动了一下,脑海里闪过林家燕的面孔。转瞬,他双眉一抬,又将这个影子赶走了,语气变得非常果决:“没事儿,我了解她。你马上去印刷厂,下周一定见报!”
副总编刚走,电话铃响了。
“你好,《滨河报道》编辑部。”
“我是林家燕。”
梁啸尘愣住了,家燕,她,她真的要来下说辞?梁啸尘抬眼向窗外看了看,心中一时没了主意。虽说他了解林家燕对他的一片深情,可毕竟事关她的父亲呵!
“怎么不说话了?”
“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你呀,你可真让我失望!梁啸尘呀梁啸尘,我已经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你了,你怎么还是不了解我?!”
“可是,事关你的父亲……”
“父亲怎么啦?你是不是还想表现一下你的所谓大度和宽容,唱一出《华容道》呢?真是,叫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还想着再摔一跤吗?”
“那你……?”
“我就是担心你为了我而放弃原则,才跟你打这个电话的。啸尘,一个男子汉,在大事大非面前……”
梁啸尘打断了她,告诉她,铁兵、还有杨部长都来找过他,他都顶住了,就是刚才副总编还劝他放林政韬一马,担心我过不了你这一关。听到这里,林家燕插话:“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我告诉他,我了解你。”
“呵……”一股热浪从心底直冲鼻端,她的鼻尖一酸,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她翕动着嘴唇,用颤抖的声音说,“你终于成熟起来了,坚强起来了呵!我的啸尘!”这时,她由衷地体会到一种幸福,一种心心相印的幸福,体内潮动着一种母性的湿润,慰藉和自豪。霎那,这股暖流便席卷了她。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活的颤栗,泪水不由夺眶而出:
“谢谢你,啸尘!这才是我对你最大的希望呵!”
一个璀璨的笑容,绽放在她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