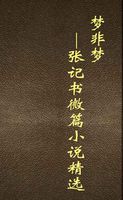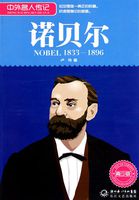她的脸涨红了,她的手又开始活动,不停地抚平她的衣服。这时我向她步步紧逼,不让她有片刻躲闪的机会。
“珀西瓦尔爵士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我说,“也难怪你害怕他。珀西瓦尔爵士是一位煊赫一时的人物——一位从男爵——拥有上好的庄地——出身名门望族——”
这时她突然纵声狂笑,使我感到无比地惊讶。
“可不是嘛!”她用最辛辣而又坚定的口气讥笑地重复我的话。
“一位从男爵——拥有上好的庄地——出身名门望族。说得对,一点儿不错!名门望族——尤其是他母亲那一方面。”
现在再没有时间体味她突然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我只意识到,等我一离开这里,就应当仔细揣摩一下这些话的含意。
“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和你辩论家族问题,”我说,“我对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事一无所知——”
“你对珀西瓦尔爵士本人的事知道得也同样很少。”她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在这一点上,我劝你别说得太有把握了,”我反驳她,“我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我还怀疑更多其他的事。”
“你怀疑什么事?”
“我还是先告诉你我不怀疑的事。我不怀疑他是安妮的父亲。”
她一下子跳起来,逼近我跟前,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怎么敢对我谈到安妮的父亲!你怎么敢说谁是安妮的父亲,谁不是她父亲!”她勃然大怒,声音激动得直颤抖,一脸的肉不停地抽搐。
“你和珀西瓦尔爵士之间的秘密,并不是那个秘密,”我丝毫也不放松,“笼罩着珀西瓦尔爵士整个生活的那个神秘事件,并不是从你女儿的出生开始的,也不会因为你女儿的死亡消失。”
她倒退了一步。“给我离开这儿!”她说,凶狠地指着房门。
“你心里根本就没想到那孩子,而他也没想到她,”我接下去说,决意要逼得她走投无路,“你去赴那些秘密约会,你丈夫发现你和他在教堂法衣室里悄悄谈话,当时你们并不是在偷偷摸摸地谈情说爱。”
我的话一出口,她指着房门的那只手立刻垂下,脸上愤怒的红晕随即消失。我看得出,她身上发生了变化——我看得出,这个冷酷、坚强、大胆、沉着的女人,不管怎样决心故作镇定,也不禁吓得发抖,因为我说出了那最后五个字:教堂法衣室。
有一两分钟,我们站在那里,默默地对视着。接着,我先开口。
“你仍然不相信我吗?”我问。
她一时无法恢复脸上消失了的血色,但是,当她再回答我的话时,她的声音已变得坚定,她又露出那副挑衅的神情。
“我就是不相信你。”她说。
“你仍旧要我离开这儿吗?”
“是的。离开这儿——再也别来了。”
我向门口走过去,等候了一下,然后开了门,再回过头望了望她。
“我也许会得到一些你意料不到的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消息,要让你知道,”我说,“到那时候,我还要上这儿来。”
“我不期待听到任何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消息,除非是——”
她不再往下说了,苍白的脸变得阴沉了,然后,她像猫一般,悄悄地移动轻巧的脚步,偷偷地回到她的椅子跟前。
“除非是他死的消息。”她说着又坐下了,这时冷酷的唇边闪出讥讽的笑,镇定的眼光中隐藏着仇恨。
我打开房门走出去,她向我迅速地瞥了一眼——露出冷酷的笑,她的嘴唇慢慢地张开了——她正在暗中异常阴险地注视我,从头到脚打量我——她整个脸上显出一副无法形容的期待表情。她是不是在暗自盘算我这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大的闯劲儿?感到受了伤害时,能激发出什么样的力量?需要时,又能将自己克制到什么程度?她是不是在考虑:一旦珀西瓦尔爵士和我相遇,以上这些因素会给我多大影响?因为明知道她是在这样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离开时连普通道别的话都没说。双方都不再讲什么,我走出了房间。
我打开外间的门,看见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牧师从广场上回来,又要经过这所房子。我站在门口台阶上等着他走过去,同时转身朝那客厅的窗子里窥视。
凯瑟里克太太在那冷漠地方的寂静中听见牧师的脚步声移近,又去站在窗口等候他。这个女人虽然被我那样激怒,但是她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下,丝毫也没忽略了对自己多年来努力争取到的社会地位的关心。瞧,我离开她还不到一分钟,她又站在那里,故意地等候着,这样,牧师出于一般礼貌,就不得不再一次向她鞠躬。他又抬了抬他的帽子。我看见窗子里面那张冷酷可怕的脸露出温和的神情,现出骄傲得意的光彩;我看见那个戴着阴森黑色帽子的脑袋毕恭毕敬地低下来还礼。当着我的面,这牧师一天里已经向她鞠躬两次!
离开那里时我心里还想,虽然凯瑟里克太太不肯与我合作,但是她无意中却帮助我向前迈进了一步。我刚要拐向广场外面,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关门。
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家门口台阶上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小矮子,不用说,那是凯瑟里克太太寓所靠我这面的隔壁的一家。那人毫不怠慢,早已准备好要去的方向。他急速向我站的拐角这面走来。我认出他就是律师事务所的那个雇员。记得我去黑水园的时候,他曾经先我一步赶到那里;后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参观那府邸时,他又试图寻衅,要和我争吵。
我停留在那里,看他这一次是否准备走近我跟前和我攀谈。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继续急速朝前走,甚至走过我身旁时都没瞅我一眼。他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进而引起了我的好奇,也可以说是引起了我的疑心,我决定继续留心监视他,要知道他这会儿究竟是在干什么。于是,也不顾被他发现,我就跟着他走过去。他始终不回头看,一直引我穿过街道,走向火车站。
那时火车快要开动,两三个迟到的旅客正挤在售票处的小窗口。我走到他们身边,清清楚楚听到律师事务所的雇员要买一张去黑水园站的车票。我断定他确是搭那班火车走后,便离开了车站。
我对刚才耳闻目睹的情况,只能做出一种解释。毫无疑问,我看见那个人离开了凯瑟里克太太隔壁的那一家,他大概是珀西瓦尔爵士派去住在那里的,因为见我这样进行侦察,预料我迟早要到那里去找凯瑟里克太太。刚才他肯定看见我进去了又出来,于是就匆忙搭第一班火车赶往黑水园去报告,因为珀西瓦尔爵士(显然已经知道我所采取的行动)当然要赶往那里去,这样,万一我到了汉普郡,他就可以及时在当地等候着对付我。看来,过不了几天,我很可能就要和他正面交锋了。
不管这些事必然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在珀西瓦尔爵士或其他任何人面前退却,我仍然要继续追求既定的目标。我在伦敦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责任很重,因为必须随时留心自己的行动,以防被人发现罗拉隐藏的地方,可是现在到了汉普郡,我感到轻松多了。在韦尔明亨,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即使我偶尔在什么地方有所疏忽,那立即招来的后果也不过由我本人承受而已。
我离开火车站时,严冬的暮色正开始降临。看来天黑后要在这样人生地疏的附近继续进行侦察,是没有希望取得成功的了。于是,我找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叫了一份客饭,订了一个房间。一切就绪以后,我就写信给玛丽安,说这次旅程平安顺当,颇有成功的希望。我出门的时候,曾经嘱咐她把第一封信(也就是我明天早晨将收到的信)寄到“韦尔明亨邮局”,现在我请她把第二天的信也寄往那里。如果信到时我已离开当地,那将来只需要通知邮局局长,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取到那封信。
时间已经不早了,旅馆餐室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回忆那天下午所做的事,不受任何干扰。就寝之前,我先从头到尾重温了我和凯瑟里克太太那次不寻常的会谈,并利用现在空闲的时间核实那天早些时候匆忙中得出的结论。老韦尔明亨教堂法衣室,成为了我的思路的出发点。我从那儿开始,慢慢地回想我所听到的凯瑟里克太太的全部谈话,以及我所看到的凯瑟里克太太的一举一动。
我第一次听克莱门茨太太提到教堂法衣室的附近一带,就曾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和教区执事的妻子幽会,单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这件事十分离奇,也很令人费解。正是由于我早已有了这一成见,所以我才会不假思索,向凯瑟里克太太提到了教堂法衣室——当时,我谈话的当儿,也只是忽然想到了整个经过的一个特殊的细节而已。我原以为她听了这话最多显出慌乱或表示愤怒,但是,这几个字一说出口,竟然会把她吓得失魂落魄,这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
我很久以前就在猜想,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中隐藏着一件凯瑟里克太太所知道的严重罪行,但此后这一想法被我抛弃了。现在,这女人突然表现得恐怖,使我直接或间接地联想到这罪行和教堂法衣室有关,更令我深信,她不但是这件罪案的见证人,而且肯定是这件罪案的同谋犯。
这件罪案究竟又会是什么性质的呢?不可否定的是,它除了具有其危险的一面,更有其可耻的一面,否则,凯瑟里克太太听我提到珀西瓦尔爵士的地位和权势,就不会那样重复我说的话,也不会那样毫不掩饰地表示轻蔑。这样看来,它既是一件危险的罪案,又是一件可耻的罪案。她参与了这件和教堂法衣室有关的事。
接着,经过进一步思考,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进展。
凯瑟里克太太对珀西瓦尔爵士公然表示轻蔑,那分明还涉及到他母亲的事。她提到珀西瓦尔爵士是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他母亲方面的时候,表示了最恶毒的讥嘲。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看来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因为他母亲出身卑微,或者是因为他母亲名誉上有什么污点,而那件事瞒过了所有的人,只有凯瑟里克太太和珀西瓦尔爵士两人知道。要检验第一种解释的可靠性,我必须查看珀西瓦尔爵士母亲的结婚登记簿,以便确切地知道她娘家的姓氏和家系,这样才能开始做下一步的调查。
另一方面,如果我所假想的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他母亲名誉上的污点又会是什么呢?记得玛丽安曾经对我谈到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父母亲的事,以及他们俩所过的那种孤独得令人犯疑的生活。这时我不禁问自己:他母亲会不会根本就没结过婚呢?在这一问题上,结婚登记簿至少可以为我提供书面证明,确定我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可是,到哪里去查结婚登记簿呢?这时候我记起了自己以前作出的结论,以前我曾这样想到,隐藏罪行的所在地是老韦尔明亨的教堂法衣室;于是我顺着原来的思路去推想,现在我又想到,登记簿也在那个地方。
以上就是我和凯瑟里克太太会谈的结果;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想法。这些想法一致集中到了一点,这一点决定了我明天的行动方向。
那天早晨,乌云密布,天色阴沉,但是没下雨。我把旅行袋留在旅馆里,等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它。我先问清楚了去老韦尔明亨教堂的路,然后才徒步出发。
需要走两里多路,一路上地势逐渐增高。最高的地方矗立着一所教堂,由于经历了悠久岁月的洗礼,它已相当陈旧,两边都筑有厚实笨重的扶壁,前面是一个样子怪难看的方楼塔。法衣室连接在教堂后边,另有通外面的门,看上去也是那么陈旧。在建筑物四周,还可以看到原来村庄的遗迹。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对我说,她丈夫从前就住在那个村庄里,但后来有身份的居民都离开那儿,搬到新建的镇上去了。空了的房子,有的已被拆除,只剩下外面的墙壁;有的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朽败;此外有几所房子里面还住着人,但那些人显然都是很穷苦的。景色很是凄凉,然而,讲到凄凉的程度,即使是这里废墟中最难看的地方,也显得比我刚才离开的新镇更好一些。这里,四处展开了褐色的原野,令人心旷神怡的远景可以供你观赏;这里,树木的叶子虽然已经脱落,但至少使景色显得不太单调,还可以让你向往夏季的浓荫。
我离开教堂的后面,绕过几间已经拆毁的小屋,想要找一个人问问,怎样去教区执事住的地方。而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两个人从一堵墙后边溜出来,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两个人当中较高的一个,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他身体魁梧,满脸横肉,装扮得像猎场看守人;另一个就是我在伦敦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那天跟踪我的两个人之中的一个。当时我特别留神注意这家伙,所以这次肯定不会认错他。
他们俩并不打算和我搭话,都跟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然而他们到这教堂附近来的动机是明显的。正如我所料,珀西瓦尔爵士已经考虑到我要到这里来。他昨晚接到了我去看凯瑟里克太太的报告,预料我要到老韦尔明亨来,所以派这两个人在教堂附近监视我。现在他采取监视我的这种方式,也足够证明我的侦察方向是对的。
我从教堂附近向前走,到了一所有人居住的房屋前面,房子旁边是一片菜园,一个工人正在菜园里干活。他指点我怎样去教区执事的住所,那是一所相距不远的小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了无人烟了的村庄的边上。教区执事在家里,这会儿正在穿他的大衣。这个快乐而和蔼的老人,总是扯着大嗓门儿说话,没完没了,他很瞧不起自己所住的地方(我不久就看出了这一点),同时又因为自己以去过伦敦闻名而沾沾自喜。
“您幸亏来得这么早,先生,”老人听我道出来意后说,“再晚十几分钟,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要去办理一些教区里的事,先生。对于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这可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可是,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腿劲儿仍然不错!一个人只要一不服老的双腿,就还有许多活儿可以干。您也是这样想的吧,先生?”
他边说边从火炉后面得一个钩子上取下了他的钥匙,顺手锁上了小屋子的门。
“没人在家给我看门。”教区执事说这句话时露出毫无家室之累的愉快神情。
“现在我的老伴儿已经躺在那面墓地里了,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家了。这里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您说对吗,先生?可这毕竟是一个大的教区——除了我,这儿的工作谁也应付不了。这只能靠学问,我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而且,还不止一点儿。我能说女王的英语[”国王的英语“或”女王的英语“,指纯正的英语。——译者注](愿上帝保佑女王!)这儿多数人都没有这本领。我想,您是从伦敦来的吧,先生?大约二十五年前,我也去过伦敦。请问,最近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他就这样一路闲扯,终于把我领到了那间教堂法衣室。我四面瞧瞧,看那两个密探是不是还在附近。这时四下里已经不见他们的踪影。他们大概一发现我去找教区执事,就隐藏到了什么地方,以便从容自如地监视我下一步的行动。
教堂法衣室的门是用坚固的老橡木制的,门上钉满了很粗的钉子,教区执事把沉甸甸的大钥匙插进门锁时,他那副神情就像是早已知道要遇到一个困难而又没有把握能克服那困难。
“我现在只好领您从这一面进去,先生,”他说,“因为通教堂的那扇门从法衣室里面反闩上了。不然的话,咱们倒可以从教堂那面进去。像这样闹别扭的锁也真少有。它这么大,简直可以用来锁牢房门;瞧它老是会被咬住,应当换上一把新的。这件事我至少已经向教堂保管员提了五十多次——他老是说:‘这件事让我来办。’可是他至今也没办。唉,这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它不能和伦敦相比,您说对吗,先生?天知道,我们这儿的人都在睡大觉!我们就是不能随着时代前进。”
他用钥匙又是扭又是转,沉重的锁终于屈服,他打开了门。
法衣室要比我单看外面所想象的大一些。那是一间陈旧的屋子,装椽子的天花板很低,室内光线暗淡,显得阴森森的,并散发着一股霉味。屋子两边,靠近隔壁教堂里边尽头的地方排列着一些沉重的木柜,它们都已蛀坏,由于年久而开裂了。在一个柜子的里边角落里,钩子上挂着几件法衣,可以看见它们露出的底部像乱糟糟的一堆帷幔。法衣下边的地板上摆着三个粗木板箱,箱盖半开半掩,成束的稻草从裂口隙缝里向四面髭了出来。
箱子后边的一个角落里堆着积满灰尘的纸张,有的很大,像建筑师的图样那样卷着,有的像是账单和信件,松松地捆成几叠。以前这间屋子,还有旁边的一扇小窗透亮儿,但后来被砖头堵住了,现在改在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这里空气窒闷,透出霉湿味,而由于关闭了通教堂的那扇门,屋子里就更加闷湿了。那扇门也是用厚实的橡木制的,上下都从法衣室里面反闩着。
“照说,我们可以把这地方收拾得整齐一些,您说对吗,先生?”快乐的教区执事说,“可是,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又有什么办法呢?喏,这儿,单瞧瞧这些粗木板箱。它们在这儿等候运往伦敦——已经等候了一年多了,现在仍旧在这儿堆得满地都是,只要是还钉牢着没散开呀,它们会永远堆在这儿。我说给您听这是什么缘故,先生,其实刚才已经讲过,这里不比伦敦呀。我们这儿的人都在睡大觉。天知道,我们就是不能随着时代前进!”
“这些粗木板箱里是一些什么?”我问。
“是一些讲道坛上的木刻,圣坛上的嵌板,风琴坛上的画像,”教区执事说,“还有十二使徒的木刻画像,连鼻子眼睛都不齐全了。它们破破烂烂,都被虫蛀坏了,边儿上都残缺破损了。和陶器一样,一碰就碎,先生,它们即使不比这座教堂更老,至少也是同样地老了。”
“为什么要把它们运往伦敦?是送去修补吗?”
“可不是嘛,先生,是送去修补;至于那些没法修补的,就准备用上好木料复制。可是,我的天呀,经费不够,它们只好留在这儿等候捐款,结果呢,没人捐钱。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先生。为了讨论这件事,六位绅士在新镇上的旅馆里一起设宴。他们发表演说,通过决议,个人签了名,还印发了上千份的宣言书。那是冠冕堂皇的宣言书,先生,上面用红墨水写满了哥特式花体字,说什么,如果不修复教堂,不整理好那些名贵雕刻,那将是一件丢脸的事。您瞧那儿就是一些没发完的宣言书、建筑师的图样、估价单、全部来往信件,大伙儿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争吵起来,现在这些东西都被堆在那粗木箱后面。起初,也收到了一些零星捐款——但是,怎么能指望用那点儿钱把这些东西运到伦敦呢?您瞧,那点儿钱只够用来包装破碎的雕刻、支付印刷和估价费用,此外一个钱也剩不下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情形那样,我们没别的地方可以堆放这些东西——新镇上谁也不肯为我们腾出空房——我们是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嘛——所以,这法衣室里才会这样乱七八糟——谁有空来管它呢?——我倒要请问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