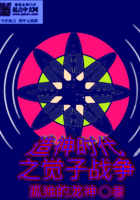Focus:Disability
Narrative Studies
海明威早期的疾病叙事和《此刻我躺下》的抒情维度
[美]米里亚姆·马蒂·克拉克/文周凌敏/译杨晓霖/校
我想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已被普遍公认的观点:海明威早期作品(如《在我们的时代里》和《没有女人的男人》这两个集子里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病态的、受伤的,从《印第安人营地》中临盆待产的难产妇女,到《平凡的故事》中患肺炎死去的斗牛士曼纽尔·加西亚·马尔拉(Manuel Garcia Maera);从经历了胫骨被撕裂、眼睛被打得瘀青、内心被伤害的幼年尼克,到饱受战争煎熬的成年尼克——他不是靠着墙支撑着血流不止的身躯,就是于下午时分在医院治疗他的伤腿,要不就是被所谓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折磨得彻夜无眠。可以说,在海明威的故事里,呈现得更多的是病态的躯体,而不是性态的身体;呈现得更多的是人物遭受痛苦折磨时的态度,而不是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其他实质方面的状态。这里有《杀人者》中被谋杀后倒在床上的奥尔·安德森(Ole Andreson),有《五万大洋》结尾处“彻底破产”的杰克·布瑞曼(Jack Brennan),有《你追我赶》中裹着自制的寿衣、虽晕船反应越来越强烈,但仍与人们交谈着的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有《我的老爸》里脸色苍白、奄奄一息地倒在铁路边的乔·布特勒(Joe Butler)的父亲,还有那些夜夜耽溺流连于酒吧,看上去疲惫憔悴,却还用双手撑着脑袋的男孩们,当然还有备受战争打击而一蹶不振的尼克。治疗疾病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尼克就是在观察父亲为人治病的过程中了解父亲的。治疗疾病如同打猎一样——以大折刀和针头为象征——它意味着力量、责任,意味着必须性情刚硬、从不心慈手软,甚至意味着一种“必要”的残酷。同时,因为父亲是医生,而母亲是个信奉基督精神科学的人(基督精神科学认为祈祷可以治疗疾病,而且是救赎的必要因素——译者注),虽然他们并非处处都“上纲上线”地针锋相对,但是行医治病总是尼克父母之间频频发生家庭内部矛盾的地带,在这里,医药能否说服宗教往往性命攸关。
在创作疾病和伤痛故事的过程中,海明威显示了几个变化。在尼克孩童时代的故事里,尼克一直认为疾病是专门用来惩治种族和社会他者——印第安人的,甚至把印第安人污蔑为患有肺炎、悲观绝望、醉如烂泥的人,把有无这些疾病或刻板形象看成本族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本质区别。直到他经历了隐喻层面上的心碎和情绪低落,再经历了后来在肉体上的真实感受后,尼克才逐渐明白一个道理,疾病和伤痛之魔不是专门用来对付印第安人的,它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在某个瞬间出其不意地夺走他和同族人的生命。海明威的医疗故事也描绘了新出现的现代生物医学技术,通过对比《印第安营地》中尼克的父亲帮助难产妇女分娩婴儿时使用的原始“剖”腹产方式,这些故事强调了新型医疗技术,比如给受伤的曼纽尔·加西亚·马尔拉(Manuel Garcia Maera)(《平凡的故事》中的斗牛士——译者注)做手术时使用的麻醉罩以及在双肺里插入的导管,再比如米兰医院给男孩们做手术时首次使用的康复设备等。
在本文中,我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我认为把尼克的受伤(woundedness)看作是这两部短篇小说集的核心特征实际上是把这些短篇小说当做“疾病叙事”来阅读。在生物伦理学领域,“疾病叙事”的有用性已被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卡斯瑞恩·蒙哥马利(Kathryn Montgomery Hunter)、丽塔·雪伦(Rita Charon)、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戴维·莫里斯(David Morris)等学者完全接受。此外,从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给《海明威》一书作的序和菲利浦·杨(Philip Young)著的《厄内斯特·海明威传》到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麦克·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黛布拉·摩德摩格(Debra Moddelmog)、玛格丽特·森·浦瑞欧拉(Margaret Sempreora)等其他学者对海明威小说中的创伤主题进行的最新探讨来看,可以说,长期以来学界不乏对海明威小说中的创伤主题进行各种对话的学者。现在,我只不过是参与到了这个大讨论中来。然而,与这些早期的探讨不同的是,本文不把研究聚焦在心理分析上,不去分析一种最原始、最根本的创伤,也不去追溯在一系列受伤(woundedness)意象中个人焦虑或文化焦虑的具体根源;我的目的也不在于进行历史描述或传记编写。相反,本研究考虑的问题是,疾病叙事给这些故事带来什么样的结构逻辑,以及疾病叙事如何使文类复杂化——尤其是关于叙事与抒情段落——和它们旨在提出什么样的伦理规则。
另一位与海明威同时期的作家威廉·卡罗斯·威廉斯在其现代主义作品中也突出了对疾病的描述。因此,首先对比一下海明威早期的疾病叙事与威廉·卡罗斯·威廉斯的医学叙事或许很有意义。威廉斯的作品从诸多方面来看无疑都是现代的、认识论上的叙事,它通过医生对病人一环套一环的当面询问这种医患对话方式来寻求治疗和康复的可能性。一方面,医生懂得医疗知识,具有探索精神和人类良知,尽管偶尔也会不厌其烦;另一方面,面对难以解释的神秘疾病和难以治愈的沉疴痼疾,面对医生的沉默或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他所表现出的隐私感或自豪感,面对医生呈现的外表上以及说话方式上的他者形象,病人显得懵懂无知。这种医患沟通从来难以达到完美;病人的故事总让希望从中探得病因或分析病情的医生感到力不从心;尽管医生对疾病诊断和治疗部分源自对病人经历的了解,但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对倾听、直觉和症状的分析。读者要做的正是了解这种形式的知识,或者了解这种知识的局限所在。
与此同时,海明威自身也从受伤的身体开始。如果诊断通过语言来进行,并且是语言的功能之一,那么痛苦和受伤首先必定存在于语言之外,而非语言所能表达。阅读海明威早期作品中的疾病,无论从读者的角度还是从医疗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为了探得病因或在诊断过程中形成关于症状的叙事,而是为了通过观察,回答身体怎样“引发”语言(27),如何走出由疾病引起的叙事触礁(55)而形成故事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引发”(beget)和“叙事触礁”(narrative wreckage)是阿瑟·弗兰克(Arthur Frank)的经典术语。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写道,在弗兰克给疾病下的定义中,创伤超越语言、故事和形式,创伤把三者投到了费尔曼所描述的某种“进程和试验”的状态中。“作为一种事件关系”,费尔曼写道,见证叙事(testimony)“由支离破碎的记忆组成,充斥在这些记忆中的事件尚未进入理解或记忆范畴,不能建构为知识被人完全认知,而是游离在我们的认知参考框架之外”。(5)
乍一看,这样的定义——由未被同化认知的事件关系引起的叙事触礁——似乎与海明威严谨的故事脉络相去甚远,但我认为,如果把它们当做疾病叙事、甚至当做费尔曼和弗兰克描述的那种见证叙事来阅读,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创伤与海明威精炼的行文造句方式相悖,也与其小说简洁明快的风格迥异。海明威在小说中采取了省略的写作手法,增强了故事的源力(raw force),这种源力并非来自“未被言说”——也就是说,并非来自类似威廉姆斯的医生故事中没被说出的症状或未被理解的那些事物——而是来自“无法言说”,即游离于语言和故事之外,非语言和故事所能企及的身体体验。海明威小说中的疾病所体现的纯粹身体性,表现形式的残忍(溺毙性肺炎,粉碎性骨折,畸形的四肢和损毁的容貌等),以及那些甚至集数种疾病于一身的生命个体,都超越了现代主义诗学神话的文化隐喻(诸如“麻醉在床上的病人”这样令人胆寒的抽象诗句或者受伤的渔王在绝望中的冥思),也超越了现代生物医学关于治愈疾病的叙事。无论是在单篇小说里,还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痛苦难以通过医学的诊断和治疗得以痊愈。在《印第安营地》中,亚当斯医生对产妇丈夫的痛苦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而基于现代医学的生物二元论(dualistic)、医疗器械论(machanistic)、还原论(reductive)等治疗模式最终证明对解决病人的痛苦也回天乏术。《在异乡》中,即使最先进的康复治疗机也丝毫不能减轻少校内心深处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不是源自少校受伤的躯体,而是源自失去年轻的妻子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悲痛。当他愤怒地警告尼克当兵就不要结婚的时候,以及当他后来讲述自己丧妻的孤独的时候,如果我们拿他表现出的悲痛之情反衬他“秀”出的那几张伤腿被治愈的照片,我们会感觉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对现代医学对伤痛的无能为力和不能正视这种痛苦的辛辣嘲讽,同时也是对尼克一味迷信医疗器械治疗效果的温和批评。从广义上说,尼克自己的治愈(如果称得上治愈的话),都远非现代医疗技术,乃至希尼的焦土和《大双心河》中的平原上的现代文明本身所能完成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海明威的疾病叙事超越了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方法,超越了小说文类,也超越了单个生命故事,从尼克的伤情到关于创伤、疾病和残废的各种故事,它就像一把铺开的折扇,虽然有些直接叙述尼克自己的生活,有些并不直接发生在尼克本人身上。阿瑟(Arthur)和乔恩·克莱曼(Joan Kleinman)夫妇认为疾病叙事处于主体性和象征秩序之间,这个边缘的位置使得我们能够追溯隐藏在社会关系、社会机构与身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够认识到“身体叙事过程就是在揭示”文化、“文化就包含在身体中”(710-711)。“在他们的叙事中”,他们写到了一群中国病人,这群遭受了“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中国人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从他们身上“把与身体创伤相关的记忆扩展为更广义的创伤故事,在这些故事里糅入了创伤烙印(道德败坏、恐惧、绝望)、对危险和损失的回忆……。身体记忆、传记和社会历史融合到了一起”(714-715)。
海明威的故事似乎都被置于相似的情境中:尼克“晚上遭受迫击炮弹炸伤”的身体遭遇作为所有故事的中心事件,与其早期肉体和心理上所遭受的创伤以及周围暴力世界带来的痛苦一起,通过海明威的其他故事以丰富和深刻的方式外折了出来。如果以这样的方式阅读,那么很明显,《此刻我躺下》代表的就是尼克记忆的变像,这种记忆重新激活了他的父母严阵以待的形象:在伊甸园的尽头,他们不是站在噼啪作响、火舌肆虐的烈火旁,就是徘徊在毒蛇出没的草丛中。痛苦甚至扭曲了他的欲望,以致故事中妻子们的形象变得像迫击炮弹一样危险。甚至那些暗流汹涌、深沟纵横的景物,危机四伏、人人自危的境况,也通过尼克身体创伤的叙事外折方式得以改变。同时,作为文化内折的尼克的痛苦变得可读了,其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深植于内心的婚姻暴力、男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战争的残暴。在故事中,疾病总是未能治愈,虽然疾病在对原罪、弗洛伊德符号学和男性英雄主义的叙述中得以再现,但绝非这些叙事所能完全涵盖;虽然将这些疾病诉诸常规的治疗方式,如祈祷、谈话、或医药治疗,但最终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
在菲利浦·杨整理的短篇小说集《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中,虽然《此刻我躺下》被编排在该集子的中间稍靠后部分,在以复兴、婚姻、父亲、性知识和权利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之前,但在《没有女人的男人》这个小说集中,《此刻我躺下》却作为压轴力作放在了最后,即前两卷小说的最后一篇;关于尼克·亚当斯的故事大多出现在这两个集子里。与成长小说相反,从孩童故事到战争故事,杨按照时间顺序收录的这些小说呈现出和其他小说集不同的叙事效果,杨创作了一种疾病故事,这种疾病叙事渗透、回应和震撼着整个故事集的始终。这样的疾病叙事能够得以展开并保持连贯,不是建立在事件发生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之上(故事时间顺序的混乱就是很好的证明),这里,身体创伤如何进入文化叙事以及文化创伤又怎样表现为身体症状是通过隐喻修辞记录下来的。有时候隐喻修辞由故事的发生环境来决定,比如,在《印第安营地》中,即将分娩的妇女通过紧接其后的斜体字章节与战时妇女们在阿德里安堡城外的推车里分娩的事实联系到了一起。无论这些比喻修辞是否涉及两个事物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遭遇痛苦时的身体姿势都一样,要么仰卧、要么蜷缩、要么倚靠:即将临盆的妇女平躺着在床上,她的丈夫也平躺着;欧·安德森(Ole Andreson)和杰克·布伦南(Jack Brennan)和曼纽尔·加西亚·梅拉(Manuel Garcia Maera)平躺着,要么在与死神对抗,要么在向死神妥协;一个即将被绞死的白人,用床单包裹着头,也平躺在小吊床上;一个印第安人在7月4日那天脸朝沙、背向天地趴在沙里;在乔·布特勒(Joe Butler)的故事中,他看着自己的老父在障碍赛中摔倒,“脸朝上平瘫在草地上,满头是血”(IOT,171-172);炮弹将瑞那第(Rinaldi)和尼克炸飞后,瑞那第被脸朝下地甩向了一堵墙。这一幕幕情景都让尼克想到自己同样也在恐惧中等待着那可怕的死亡——“当炸弹把佛萨尔塔(Fossalta)的战壕炸成碎片时,尼克僵直地平躺在地上,冷汗直冒,祈祷着‘耶稣上帝带我离开这里吧’”(IOT,87)——到最后,如在《此刻我躺下》中描述的那样“在夜晚里目睹一幕幕充满恐惧的景象”。
除此之外,他们遭遇痛苦时可能采取另一种身体姿态:在《战斗者》中,在拳击场上格斗搏命,最后落得身体残废、精神错乱的职业拳击手爱德·弗朗西斯(Prizefighter Ad Francis)双手抱头呆坐着,看着炉火;在《我们的时代》第十五章中,山姆·卡迪那拉(Sam Cardinella)勉强挣扎着支起身体坐起来,以便被处以绞刑;在《我们的时代》第五章中,“罹患伤寒”、在雨中等待着行刑队来执行枪决的内阁大臣,头倚双膝,绝望、无助地坐在一滩水中(IOT,83)。这些前前后后的描述强化了尼克·亚当斯自身的痛苦:“他靠教堂的墙坐着,为了让他远离炮火,他们把他拖到这里”(81),并且引发了尼克对记忆中各种挥之不去的关于其他轰炸、其他战事的战后创伤记忆。
正如故事所承认的那样,尼克本身遭受的痛苦远远小于小说集中他耳闻目睹的其他人的痛苦,也远远不及战火纷飞中他亲眼见到他周围的人所忍受的集体伤痛。但正是这些发生在他人身上的凝重悲怆的故事——虽然在叙事中没有被尼克“亲身经历”,但都被他“一一见证”——有力地渲染了尼克自己的故事——两卷作品中的那个故事。仅这些纯粹的数字就能说明身心体验超出了任何单个叙事或故事框架的限制,一个伤痛故事由许多故事交织而成。这也正如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所揭示的那样,仅凭讲述是不能直接表达一个意义深刻的伤痛故事的。“身心俱伤”需要比喻、重复和沉默等修辞方法来呈现,而这些手法仅仅通过尼克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尼克之外的其他故事有些是发生在战争中,有些是在监狱里,有些是在斗牛场和拳击场里,阅读这些故事时,它们仿佛在告诉读者“它看起来……,好像……,似乎……”。同时,尼克的创伤为世上所有人的痛苦提供了一个隐喻。读者跟随着故事中的尼克加深了对那些身体蜷缩、奄奄一息和身心俱伤的人们的体认,获得这种体认的途径除了尼克的叙事解说之外,还包括《此刻我躺下》这样的特定故事刺激读者所产生的情感诉求。
这种体认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使我回过头来思考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曾提出的问题,亦即我在本文前面提及到的这个问题:抒情文体是怎样在《此刻我躺下》中体现出来的呢?费伦很早之前就提出通过“读者判断”的角色来区分叙事和抒情文体。费伦认为“叙事需要读者判断它的人物;抒情则要求听众不去判断它的说话者”,因为抒情是人物(或说话者)倾吐发泄一系列的态度、思想、情感和选择的再现,这种抒情要求受众不去作判断,而是积极思考并想象将自己置身其中。(“Now”,47)。费伦进一步阐述说,在《此刻我躺下》中,尼克的故事从道德上来看并不易为读者欣然接受,因为强行要求我们去同情尼克,去体会身在他的处境下的情感,无异于让我们去接受某些不道德的价值观,特别是故事里暗含的类比,如战争和婚姻之间的类比,或者可以具体到故事中炸弹与女人之间的类比(“Now”,48)。但是,抒情模式下的尼克,却用他温柔的声音,友善待人和勇往直前的行为诱惑我们不加判断地接受了在叙事模式下原本不为我们认同的观点和类比。
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把抒情文体看作是“进入另一个经验世界的入口”(Hosek and Parker,36),一扇通向“我们习以为常的时空经验”(弗莱语)之外的世界的大门。这样理解抒情或许更有助于回答抒情文体在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里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抒情文体此处要感抒的这个不同寻常的经历是苦痛(suffering)——无论这种苦痛令人多么诚惶诚恐,它都是肉体的苦痛外折到记忆、隐喻和态度上去的过程;同时,也都是外界现实(冲突事件和危险事件)内化为疼痛、恐惧、沉默的亲身经历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抒情文体也就必定对读者有所诉求,除了获得读者的同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加深读者感同身受的程度。如果学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的做法,援引列维纳斯的思想来阐释抒情文体的作用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此刻我躺下》中,抒情文体给尼克的痛苦赋予了一张“面孔”,通过这张融众多诸如此类的道德感情伤痛于一体的“面孔”,我们可以“管窥”世上更深刻更广泛的痛苦。
然而,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迫切需要回答但又常不为人认可的问题:一本书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都能够像列维纳斯“面孔”理论那样赋予其“面孔”的含义吗?无论列维纳斯这个关于阅读伦理观的术语多么让人信服,但是正面遭遇伦理冲突、道德推理或阅读的专注与投入的不可约性都表现出对这种方法的极大抵触。对于莫里斯来说,面对面的遭遇和冲突是伦理困境和冲突的隐喻,而这个隐喻正是疾病叙事所要求的。与罗布和费尔曼一样,对于弗兰克来说,与他者的遭遇和冲突是以“见证”为中介的;在这样的“见证叙事”中,痛苦的经历往往超过任何单个事件的诉说、固定制式的情节或上天注定的人物命运、任何纯粹的认知理解、对意义或回应的所有阐释,甚至如弗兰克所说,超过了任何文体的阐释(203)。罗布写道:“创伤故事的听众不自觉地参与到故事中,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成为创伤事件的主角:读者通过倾听,自身或多或少地体验到了同样的创伤感。这样,故事中创伤受害者和创伤事件一起影响着读者和故事事件之间的关系,读者逐渐和故事中的受害者共同体会着困惑、伤痛、迷茫、恐惧、冲突……。那么,也就是说,听众和受害者一同在与他(或她)的惨痛经历留下的伤痕累累的回忆与刻骨铭心的‘伤疤’进行斗争。”(57)费尔曼认为,“见证叙事”的这种诉求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美学上的、情感上的,而且也是身体上的,它重新唤起受害者肉体上与他人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是非认知层面的。她在书中写道,“见证叙事”的作用“是在事后迟来的见证中,打开读者感悟历史的想象能力,因为这时读者变成了历史见证人——这使得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视力观察(或洞察力)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受和体会发生在他者身上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感受往往只能在身体亲历某个事件时才可以获得”(108)。
但是,与罗布和费尔曼引述的事件以及弗兰克的研究对象——那些实验性、无序性的疾病故事不同的是,海明威的故事不是在一种显著展开的见证修辞推进下进行的,海明威的故事对痛苦的认同——在对勇敢、暴力、性控制和自满的虚饰中,在按时间顺序安排故事所凸显出来的某种艺术性发展叙事中——被迅速抵消了。此外,尽管这些故事具有“见证性”(即它们与那些根本无法讲述或解释的事件之间有联系),但这些故事首先要服从小说的形式和目标。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小说叙事的固定性(immobility)很明显“与概念的固定性截然不同,小说叙事创造生命,为我们的权利和真理赋予现实性,开启辩证思维之门”。(LR,139)。无论海明威的故事看起来多么真实,它们仍然在列维纳斯所定义的人伦关系和启示秩序等概念之外。
然而,当我提出以海明威故事作为中介的面对面交锋或冲撞这些重要问题时,我想阐明一点,那就是这些早期的文本包含了对痛苦本质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无疑受到了列维纳斯思想的启发。我旨在阐述两个密不可分的观点。第一点,列维纳斯坚持当讲述痛苦故事时不可能不使用将来时态,因为这种痛苦经历交织着当前遭受之苦与对未来态势的焦虑恐慌感,谁也不敢说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否会更糟糕,死神是否来敲门。正如同列维纳斯所说:“似乎有什么就要蓄‘事’待发,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比痛苦本身更让人抓狂,愁苦难耐。”(TO,69)第二点,列维纳斯认为痛苦和死亡并不会像海德格尔阐述的那样把人带进一个神清志明、男性阳刚和英雄气概的至高状态,它们代表着黑暗和神秘,它们让人面对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了在《此刻我躺下》中被如泣如诉地道出来的那种(当人面对死亡和痛苦时的——译者注)无能状态。
列维纳斯总结说,受苦不仅处于恐惧和痛苦之中,而且还处在恐惧和痛苦的边缘。就像孩子的祈祷一半来自自己的观察一半来自自己的想象一样,睡眠和痛苦在死亡的边缘分享着同样的位置。这一点尼克深有体会,“很久以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经历,我知道,如果我在黑暗中合上双眼,任它离去,这时我就感觉我的灵魂已经脱离了我的躯体”(MWW,209)。虽然尼克的恐惧源于过去的战争经历,但这种恐惧却集中体现于现在,并暗暗地随着尼克被带向现在与将来的边缘处。尼克说:“自从那天夜里被炸以后,我就感到灵魂离开了躯体,飞走了然后又回来。我想永远不去想它,然而,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无法摆脱这种感觉了。每次在夜里准备入睡时,我必须竭尽全力才能阻止我的灵魂离开躯体。”列维纳斯认为,受痛苦煎熬的人无法从这样的状态中逃脱出来,这种状态也不会自行消退,它也无法给我们任何启示,死亡永远具有不可“知”的神秘性。尼克在战争中饱受痛苦,也目睹了身边很多人的痛苦和死亡,但是他依然活了下来,活在他描述的夏天里,活在故事的现在时里。在《此刻我躺下》中,尼克在一个个不眠的夏夜里,不仅遭受着战争创伤,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关于死亡的真实而无法回避的知识,同时,在无尽的黑暗包围下的他,也遭受着黑暗预示的死亡的那种诡异莫测感的折磨。
极端的痛苦状态不仅会遇到无法体验的问题,还会遇到主体的暂时性悬置问题。死亡及其之后的状态无法通过认知、意志和强制行为来把握。列维纳斯认为,死亡及其之后的状态“不能分析”,它们无法“被理解,只有瞬间剧变”(PL,156)。遭受痛苦的人不能让时光倒流,也无法掌控将来发生的事,只能目睹自己的故事停滞在恐惧时刻。列维纳斯认为,死亡在痛苦历程中的特点是没有光和活力,“它所叙述的事件,主体不是故事的控制者,主体已经不是主体”。相反,“在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中,死亡是神志清明的至高状态,是人体活力的制高点(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不是存在到头,而是向死而在。因此,死亡意味着可能性——译者注)。这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最高可能性’相关的此在(Dasein)假设(面对死亡,Dasein不是被消融在虚无之中,而是‘向终结存在’,进入了可能性的境域——译者注)使得所有其他可能的事物具备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成功把握一个可能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此在脱离了一切限制和依靠。海德格尔的死亡是指一种自由,而对于我来说,遭受痛苦的主体似乎在磨难中达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主体发现自己被束缚、被控制,从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被动状态”(TO,70)。
被动性一方面意味着失去一切,包括控制权、理解力的丧失,以及遭遇死亡时主体性的终结,但对于列维纳斯来说,被动性的另一方面也是责任的本质状态(列维纳斯把存在的意义解释为责任——译者注)。一个人一旦被剥脱了所有主体性,那么,对于他者,这个人就是赤裸的我,我既是守护者又是人质。这种关系先于语言和法律而存在,非自我和利他主义所能解释,因此,这也说明了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包括海明威小说在内的其他所有小说。但是,我仍然认为,把痛苦转化成被动状态和对残酷的暴露视作海明威的重要伦理时刻来阅读是可行的。《此刻我躺下》通过两种明显的方式表现了尼克在痛苦煎熬中男子气概的衰竭和英雄主义的终结。一是尼克对未来、爱情和工作等的冷漠态度。“至于姑娘,我想了几次以后印象就模糊了”,尼克回忆在那些不眠之夜里,“他记不起她们的样子,最后,所有姑娘都变得模糊不清,差不多都是一个样子,我也就不再想她们了”(MWW,222)。尼克对姑娘们的思念只是发生在记忆中,从来没有过色情欲望。故事中,尼克关注的最终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结过婚”。当不可捉摸的死亡越来越靠近尼克时,他在将来时态中几乎什么也没捉摸到;他对约翰讲的话——“我将去一家报社谋份活儿”(219)——是尼克对自己余生的唯一的规划和打算,他捉摸不清这家报社是在芝加哥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只能用“可能”来回答约翰的问题。在尼克遭受创伤后遗症和失眠困扰的夜晚里——对死亡的恐惧使他夜不能寐——他的自我已经在恐惧中变得分崩离析,将来也因死亡变得虚无缥缈;因此,我想起了女人和炸弹之间令人不安的类比。列维纳斯认为,“死亡没有‘现在’或者说死亡从来就不是一种在场”。“在死亡到场时,我就不在了,这不是因为我虚无了,而是因为我不能够把握了。实际上,我的主人地位’、‘我的阳刚之气’、‘我的英雄气概’一旦跟死亡联系在一起,就变得虚无了,一句话,这种意义上的主体不在了。”(TO,72)。
遭遇痛苦和濒临死亡时的这种纯粹被动性,会产生列维纳斯描述的那种婴儿状态的回归:“痛苦达到一种纯粹性状态时”,列维纳斯写到,“痛苦与我们之间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绝对责任就转化为绝对无责任,也就是进入了婴儿状态”。对于列维纳斯来说,这在痛苦过程中就表现为“啜泣”和“颤抖”。表达尼克的自我退缩和自我迷失的第二种重要方式是他在恐惧万分的状态下战栗着念着祈祷词的样子(这与婴儿的啜泣类似)以及担心被炮弹炸飞的阵痛般的焦虑。但是,尼克婴儿状态的回归也通过他召唤过去的回忆,让自己彻夜不眠的这个隐喻手法得以表现——这些回忆带着尼克回到他刚记事的那个年纪所发生的事情、甚至回到他有记忆和会说话之前的真正婴儿状态、回到他出生的小阁楼。这个回归需要追溯并深入到那些充满黑暗和不快的家庭故事中去——母亲、父亲、孩子、暴行——在那里,尼克是一个无助的、被动的旁观者。通过对孩童时代的祈祷文《此刻我躺下》的极度依赖,通过退化到婴儿时期祷告时的沉默发声状态,或通过与约翰的交谈和向(意大利)女孩求爱的言语来发出声音。在对孩童时期的回忆中,尼克也看到人类回归到了婴儿状态,人类从鱼类和蝾螈开始进化;看到了人类回归到了神话和《圣经》中的婴儿状态:母亲、父亲、受蛇诱惑困扰、在熊熊大火中被迫离开伊甸园。尼克自己变成了后来的亚当,当他在回忆万事万物的名称时,他也在重建这个充满战争伤痕的世界。他告诉我们:“因此,有几个夜晚我就背诵起世界上所有飞禽、走兽、鱼虫的名称,接着又开始背诵国家、城市的名字。”(215)。
此刻,通过尼克对心理记忆的苦心重建,我们听到的可能是尼克阳刚之气的复苏,主体对客体——这个世界本身——的把握和适应。重新命名似乎可以逆转被动状态、颠覆婴儿状态的说法、改变英雄主义泯灭的局面,从而通过经历和克服痛苦达到胜利。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列维纳斯所坚信的看法来阅读,认为痛苦经历阻止亚当式的男子气概和自我回归的话,那么尼克每个夜晚所做的努力——像孩子一样百无聊赖地用石块去重砌一座城,或通过拼凑学童时的记忆来重塑这个世界——恰恰不是减弱了他的被动性,而是更加凸显了他的被动性。海明威的故事就在这个边缘上沉痛忧思,以抒情的方式表达着忧思,凸现并抵制死亡面前的被动性。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意志与死亡暴力的交锋是伦理冲突的最深刻根源;无论是死于上帝或敌人的意志,还是死于“剑刃、化学毒物、饥饿和干渴”,“孤独都因此被打破”,和他者的联系也就因此而“敞开”,“至少是被半敞开了”。“我的死亡来自于一瞬间,在这一瞬间里我无论怎样都施展不了我的力量”(TI,235),列维纳斯的这句话似乎不仅适用于《此刻我躺下》中的失眠、颤抖的尼克,而且也适用于海明威后来的小说《一条永远未走的路》中的禁欲、煎熬的尼克。死亡是不能被战胜、被忍受的,“死”也不能融入“生”中去,它的他异性是不能同化的。死亡打破了孤独,改变了意志,以至于意志不再与“自我的需求吻合”,而变成“服务他者的欲望”(TI,236)。列维纳斯认为,痛苦“就发生在与他者的联系变成可能之时”(TO,76)。
再后来,在《无谓的痛苦》一文中,列维纳斯认为,纯粹的痛苦“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痛苦因其将自身置于毫无出路的状态而被宣判为‘无谓’”,但他认为“一种超越却在人际中形成”。通过这个人际伦理的角度,他发现了“他者的痛苦”和“我遭受的痛苦”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者的痛苦’,对于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痛苦祈求着我、呼唤着我;而对于‘我遭受的痛苦’,无论痛苦的历程多么艰难,痛苦生来固有的无用性却可以在成为其他人痛苦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意义,而这正是痛苦所能感受的唯一意义。”他接着说,“在本世纪的种种野蛮行径中(但也正是因为这些野蛮行径),对他者的关注被确立为人际的纽带,甚至被提到了绝对伦理准则这个高度——毋庸置疑的唯一准则”(PL,159)。
有人认为,从痛苦中获得真知灼见宣扬和肯定了海明威小说中“对世界的掌控”(mastery)和“勇敢”(bravado)等意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批评家已经从多方面质疑了这种阐释,比如卡里·伍尔夫(Cary Wolfe)提出用充满“性别越界可能性”的形象来取代“打肿脸充胖子式的男子汉”(223)。然而,列维纳斯对痛苦的阐释的确为我们考虑《此刻我躺下》中尼克的处境提供了新方法,尽管它改变了《此刻我躺下》这篇小说提出的伦理规则。故事中的抒情段落将我们置身于那个边缘,在那里主体能动性不再发挥作用,对一切的把握都变为不可能。这些抒情段落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时刻,这个时刻拒绝任何伦理立场和阐释的努力,既不能被理解,也不能弃之不顾;这些段落使我们成为尼克故事的人质(虽然很短暂)。这样,《此刻我躺下》就打开了半个窗口,通向自我之外的世界,通向他异性、无限性和他者。这个窗口从尼克自己的受伤开始,用故事提供的任何标准来衡量,他的受伤都是无谓的痛苦。这个窗口如此直接而执著地通向他者的痛苦以及人际间的联系,这一事实诠释了包括《此刻我躺下》在内的所有故事具有惊人的伦理力量,虽然这个伦理力量到最后依然困扰着我们的判断。
(原载Narrative,200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Cowley,Malcolm。Introduction to Ernest Hemingway。New York:Viking,1944.
Frank,Arthur。The Wounded Healer。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95.
Frye,Northrop。Approaching the Lyric。Lyric Poetry:Beyond the New Criticism。edited by Chaviva Hosek and Patricia Parker。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85:31-37.
Hemingway,Ernest。Our Time。New York:Scribner’s,1925.
Hemingway,Ernest。Men Without Women。London:Jonathan Cape,1928.
Kleinman,Arthur,and Joan Kleinman。How Bodies Remember:Social Memory and bodily Experiene of Criticism,Resistance,and Delegitimation Follow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1994(25):707-724.
Laub,Dori,and Shoshana Felman。Testimony。New York:Routledge,1992.
Levinas,Emmanuel。The Levinas Reader。Edited by Sean Hand。Oxford:Blackwell,1989.
Levinas,Emmanuel。Time and the Other。Translated by Richard A。Cohen。Pittsburgh:Duquesne Univ。Press,1987.
Levinas,Emmanuel。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y。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Press,1969.
Levinas,Emmanuel。Useless Suffering。The Provocation of Levinas。edited by Robert Bernasconi and David Wood。New York:Routledge,1988:156-167.
Moddelmog,Debra。Reading Desire:In Pursuit of Ernest Hemingway。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99.
Morris,David。Illness and Culture in the Postmodern Age。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8.
Morris,David。Narrative,Ethics,and Pain:Thinking With Stories。Narrative,2001(9):55-77.
Phelan,James。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Press,1996.
Phelan,James。“Now I Lay Me”:Nick’s Strange Monologue,Hemingway’s Powerful Lyric,and the Reader’s Disconcerting Experience。New Essays on Hemingway’s Short Fiction。edited by Paul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8:47-72.
Reynolds,Michael。A Farewell to Arms:Doctors in the House of Love。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mingway。edited by Scott Donald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6:109-127.
Sempreora,Margot。Nick at Night:Nocturnal Metafictions in Three Hemingway Short Stories。The Hemingway Review,2002(22):19-33.
Smith,Paul。Introduction:Hemingway and the Practical Reader。New Essays on Hemingway’s Short Fiction。edited by Paul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8:1-18.
Williams,William Carlos。Doctor Stories。Edited by Robert Cole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4.
Wolfe,Cary。Fathers,Lovers,and Friend Killers:Rearticulating Gender and Race via Species in Hemingway。Boundary,2002(229):223-257.